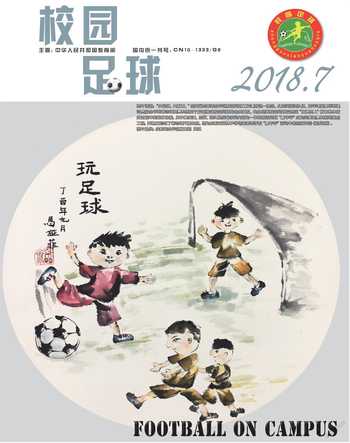構建“四眾兩貫通”長效機制 打造青少年校園足球升級版
范家堂

作為首批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試點區和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滿天星”訓練營,金牛區充分發揮試點區先行先試、改革創新、推進普及的“排頭兵”“試驗田”作用,充分發揮訓練營提升品質、打造品牌、推廣經驗的示范、引領和帶動作用,通過創新教學、訓練、競賽、保障四個體系,實現了中小幼育才機制、班校區競賽體系的全面貫通。
一、匯眾智推動教學體系創新
堅持以教學為基礎,通過創新足球教學體系,推動中小幼教學鏈條全面銜接,持續擴大校園足球普及范圍。一是抓課程建設。落實國家課程,建立區級課程,創新校本課程,以足球進校園、進課堂、進教材、進活動“四進”為抓手,推動建設一體化足球課程,分年齡段編印《校園足球》教材,規范訓練大綱,實現分層、分類教學。二是抓教學改革。加強《校園足球》教材使用,以幼兒園足球興趣化、小學足球多元化、初中足球基礎化、高中足球專項化為抓手,細化教學要求,夯實教學體系。采取“足球教師+足球指導員”的方式,發揮科任教師作為“足球指導員”在學科融合、文化認知、課堂滲透中的作用。
二、匯眾力推動訓練體系創新
堅持以育人為根本,打通“區內區外”“線上線下”“專職兼職”界限,全面構筑家校社共育機制,充分發揮校園足球育人功能。一是打通“區內區外”界限。成功爭取成都國際足球中心落戶金牛區,通過企業參與等方式,建成奧林中心訓練營、五塊石成鐵體育中心和西南交大訓練營。引進10個足球俱樂部與區內47所校園足球特色學校簽訂協議,每周開展不少于3次的足球訓練。同時,擬在法國和阿根廷的成都友好城市建立校園足球海外實訓基地。二是打通“線上線下”界限。借助“互聯網+”思維,建設金牛區青少年校園足球管理系統,打造金牛區獨有的校園足球數據平臺,為區域校園足球發展提供科學的足球人才“選培用推”數據鏈支撐。三是打通“專職兼職”界限。通過現職提升、轉崗培訓、社會聘用等手段,持續優化足球教師隊伍,引進120余名足球教練員。聯合省市足協和高校對學校體育教師、教練員進行全覆蓋培訓,130名體育教師獲足球專項資質證書。每年吸納50余名高校優秀足球專業學生到學校進行日常訓練,向專業球隊、社會和家長招募校園足球志愿者,彌補專職人員不足的問題。
三、匯眾能推動競賽體系創新
堅持以競賽為關鍵,通過以賽促教、以賽促訓,推動班校區競賽體系全面覆蓋,有效提升校園足球競技水平。一是以三級聯賽強基礎。把校園足球聯賽納入中小學體育年度競賽計劃,建立班級、學校、區域三級聯賽制度,建立班級、學校、片區聯賽機制,讓校園足球賽事流行起來,形成“人人都參與、班班有足球、校校有特色”的局面。二是以區級競賽鑄品牌。堅持每年在幼兒園開展足球趣味賽,在中小學開展校園足球普及型聯賽“金教杯”和提高型聯賽“金冠杯”,形成普及型和提高型并舉的競賽模式,滿足中小幼不同年齡、不同水平學生的比賽需求。2015年至2017年,參賽學校從20所增長到53所,增加近2倍,占全區公辦中小學的94.6%;參賽學生數從240人增長到1900余人,增加近7倍。三是以專項賽事促提升。結合區域和學校實際,廣泛組織年級聯賽、趣味賽、挑戰賽及國際邀請賽、友誼賽等專項賽事。同時,鼓勵支持各學校足球運動隊參加各級各類足球競賽。
四、匯眾資推動保障體系創新
堅持以機制為保障,注重協同整合多方資源,著力健全統籌協調機制,切實增強校園足球保障能力。一是強化組織保障。將校園足球納入區委、市委改革臺賬,作為區委書記掛帥的重點項目。區政府牽頭建立部門聯席會議制度,形成“政府主導、部門協同、學校推進、社會參與”四位一體組織機制。全省率先成立區級校足辦。二是強化制度保障。出臺《金牛區青少年校園足球活動行動計劃(2016-2020)》等文件,制訂《金牛區青少年校園足球特色學校評價細則》,建立學校體育運動意外傷害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三是強化資源保障。建立區財政為主體,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經費投入機制。加大足球場地規劃建設力度,目前,全區共有7塊標準化足球場地、30余塊八人制足球場地、150余塊五人制足球場地。有效挖掘公共運動場地、社區活動中心、小區運動場地等資源,探索學校與社會公共體育場所共享機制。
在通過“四眾”模式推進校園足球改革發展的實踐中,金牛區實現了“兩個全面貫通”的良好局面,培育出足球工作的“金牛特色”,形成了足球人才的“金牛品牌”貢獻了足球發展的“金牛力量”。一是中小幼育才機制全面貫通。依托試點區建設,堅持普及與提高并重、升學與成才并舉,建立中小幼“一貫育人”機制,抓好選拔、培育、使用、推薦4個環節,探索校園足球特色學校小、初、高對接招生機制,建立“十五年一體化培養”模式,打通“選培用推”路徑。二是班校區競賽體系全面貫通。依托“滿天星”訓練營建設,金牛區形成了“1+N”推進模式,搭建起高水平訓練和競賽平臺,構建起多層次、全方位的競賽體系,實現班級、學校、區域三級聯賽的全面貫通。金牛區成為省、市青少年校園足球最佳陣容遴選人才輸送大區,53人入選省、市最佳陣容,占比超20%。
下一步,金牛區將按照教育部的部署,持續抓好校園足球試點區和訓練營建設,探索完善青少年校園足球教學、訓練、競賽及保障體系,推動青少年校園足球普及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