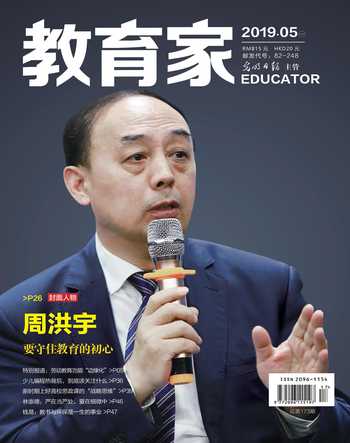勞動教育貴在堅持體腦并舉
虞曉貞

翻閱中小學教學計劃,幾乎每個學段都設置了與勞動或是勞動技術相關的課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需要強調的是,較之過去的學工、學農,如今的勞動教育應該有更豐富的涵義——不再是簡單的“掃一屋”,更多的是堅持體腦并舉和對真實生活的豐富體驗。
為何強調勞動教育
當前,中小學的勞動教育落實途徑主要有四種:勞動技術課、社區服務、校園值日制度、高中社會實踐。其中,勞動技術課和校園值日制度是學校教育的常態存在,而社區服務和高中社會實踐多為階段性或一次性教學任務。以上海市教育委員會每年印發的上海市中小學生學年度課程計劃及其說明為例,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都有社區服務要求,勞動技術課則從小學四年級開始設置。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什么我們還要強調“勞動教育”?我想,首先可能是隨著社會變遷,勞動的內涵也在改變,因此,勞動教育也要應時而變。其次可能是對物質豐盈的社會的依賴,導致了許多對體力勞動的規避,讓我們產生了隱隱的憂慮。第三可能是我們期盼完整的勞動教育,既能讓學生感受大汗淋漓的體力勞動,又能獲得勞動過程帶來的創新成果。
我所感知的勞動教育變遷
在我的中小學時代,“勞動”一直伴隨著成長。上學靠雙腿走路,在學校除了衛生值日、每周大掃除,全班每個同學都有一個勞動崗位。放學回到家,掃地、做飯、洗碗也是十幾歲少年必會的家務。“勞動教育”不是一門顯性科目,而是天天發生的生活。
當我成為中學老師后,學生在校的勞動大抵與從前相似。后來,課表中多了一門“勞技課”。初中階段,男生大多跟著老師修自行車、做木工,女生跟著老師學習縫紉和織絨線;高中階段多是到實驗室做簡單的金工,或學習焊接電路板。于是,撩起袖子打掃衛生、上勞技課、學工學農,構成了中學生“勞動教育”的主體。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中學生,學農時住在農戶家中,每戶接待十名左右的學生,大家睡通鋪,被褥和生活用品都要自帶,生活條件乃至作息都與當地農民一致。那時候,學生還要向農戶學習怎么用鐮刀,割稻子時劃破膠鞋的頻率相當高。學校老師還要自帶一支伙食隊,包括燒飯炒菜用的鍋碗瓢盆,在駐地帶著一群學生為參加學農的師生提供一日三餐。那個年代,高中生的學工也是“真刀實槍”,當時還有不少街道工廠性質的企業,同學們跑到工廠糊紙盒、做燈泡、包香皂,體驗真實的“做工”生活。
如今,變化最大的就是“學農”和“學工”。以高中生學農為例,學習場所從真正的農村挪到了農場或學農基地,住宿形式也從農家通鋪變成了集體宿舍,勞動內容大都是“一班拔草,二班起壟,三班種菜,四班澆水,五班施肥,六班收菜”,剩下的大都和體力勞動不太相關,如觀影、聽講座、參觀現代農業園區、文藝會演、體育競賽等綜合活動。孩子們的學農時光往往夾雜著歡樂與抱怨:集體活動讓他們非常快樂,食宿條件則被他們“吐槽”。
走入當今的校園,可能不會再看到修自行車、做木工這樣的“學工”活動,但卻涌現了更多的社團活動,如做手工、繪畫、3D打印、機器人制作等。這些變化說明,社會在變,勞動的內涵也在變,同樣,勞動教育內容也在應時而變。
學校勞動形式變遷帶來的思索
身為老師,我們一邊懷念曾經師生一體的火熱勞動帶來的身心愉悅,一邊擔憂著學生的生活能力而不再敢去組織這樣的活動。出于安全考慮,學校現在連學生大掃除也很少組織了。學生生活技能的日益弱化,加之家長的寵愛和擔憂,無形中限制了學校組織開展體力勞動的想法。我們曾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每周五下午讓學生進行大掃除,也實行過十幾年的“勞動周”制度,值周班級一周不上文化課,負責校園早中晚進出執勤,還要打掃兩棟宿舍樓、一棟教學樓、一棟實驗樓的公共空間,包括衛生間。后來,由于教學科目增多,學生多元選擇課程的不確定性增大,家長對擦玻璃等勞動內容安全性擔憂,這些勞動活動漸漸停止或消減了。
今日的高中生是否還需要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的勞動經歷?不少人提出,當今社會如此發達,高科技運用如此廣泛,腦力勞動才是未來社會的主流勞動,完全沒有必要讓學生感受那樣的生活,而且現在的農村也不是過去的農村了。這成為人們默認變化的一個強有力的理由。
再一思索,當前的學校還敢讓學生“真刀真槍”地下地收割、派老師帶著學生一起埋鍋燒飯嗎?且不說敢不敢,如今的教師主體已是“80后”“90后”了,他們大多是獨生子女一代,成長在把孩子當作“小太陽”的環境中,不少老師自己連基本的家務活都不會干,學校如何放心讓他們帶著學生去“冒險”?而學校、特別是小學,連學生課間在走廊或是操場上奔跑都感到擔憂,更別說體力勞動了。
再提勞動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教育確實需要應時而變,勞動教育同樣如此,我們要對勞動教育有更全面的價值認識。無論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學校必須圍繞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弘揚勞動精神,讓孩子們體驗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地勞動而展開。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講到,勞動創造了人。人的發展離不開勞動,而勞動的形式有一個從簡單到復雜的過程,勞動的分類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在學校教育中,不能以腦力勞動替代全部的勞動概念,也不應把體力勞動當作唯一的勞動內涵。學校要承擔學生社會化勞動的教育,如公益勞動、體育鍛煉、社會實踐。
同時,家長也應教給孩子最基本的生活技能,比如穿衣做飯、保持自我衛生等。作為老師,希望家長對孩子的勞動盡量少一點干涉,千萬不要拿學習作為阻攔孩子勞動的理由。
同時,勞動教育應根據場所、年齡階段和類別來實施。小學階段的勞動教育應側重訓練,讓學生學會各種動手操作的事務,會利用各種日常工具達成目標。中學階段的勞動教育應側重融合,讓學生通過規范操作實現任務、目標,體驗用雙手獲得成果的喜悅。高中階段的勞動教育應鼓勵創造,引導學生實踐自己的設想,把設計變成實物,從而體會成就感。
完整的勞動教育既有大汗淋漓,也有創新成果
今天許多對體力勞動的規避,既源于對學生安全的擔憂,擔心學生不會使用工具,害怕學生在勞動中受傷;也源于對物質豐盈的社會的依賴,成人的潛意識里覺得某些技能的缺失并不影響生活。
但是,從勞動創造人類的理論出發,我們可以理解為,勞動是人類不斷進化的基本條件,體力勞動是腦力勞動的基礎,簡單勞動是復雜勞動的前提。勞動教育始終要堅持體力和腦力并舉。
我們嘗試以化學和生物課程為基礎,在學校附近的農場開辟了兩塊地。其中一塊地讓學生開墾實驗田種植玉米(強體力勞動),定期維護(耐心和耐力勞動,也是責任心教育)、成熟后收獲(體力勞動,伴隨喜悅的心理體驗),然后將收獲的農產品作為實驗原料,從玉米、秸稈中提取多糖,制備乙醇、可降解塑料等產品,探索秸稈處理的新方法。另一塊地則由學生種植棉花,利用棉花稈表皮造紙,棉花制備脫脂棉,棉籽榨油后制備生物柴油,棉花稈制備活性炭,讓棉花的每個部分都能得到充分利用。
在接觸農田和農作物的過程中,老師們還發現了許多體腦并舉的勞動結合方式。如,四月份,恰逢收獲番茄的時間,前去勞動的同學,一部分把發酵的牛糞混入土壤上肥,一部分按照番茄的大小分裝。上肥的工作比起前一次種植水栽生菜的“味道”完全不同了,到底是土壤栽培有利還是營養液栽培更好?這成為同學們思考的問題之一。回到學校,在老師的引導下,同學們收集了許多飲料瓶,自己在瓶子下部和頸部安裝了兩個水閥,底部的水閥用管子連接在一起,意圖將每個瓶子作為一個栽培器。為了使液體的水位高低可控,老師又帶著大家做了一個小小的“報警器”,把報警器貼在合適的水位線處,一旦水位過低便會發出“嘀嘀嘀”的響聲,提醒操作者補充。而分揀番茄的同學回到學校,也打算在老師的帶領下研究一個小課題,編寫一個程序,做一個按照番茄大小自動分揀的小設備。
這種全過程的完整勞動體驗,濃縮了簡單勞動到復雜勞動的進程。讓學生既能體驗大汗淋漓的體力勞動,又能收獲豐收的喜悅,最后還能付諸科技實驗,實現勞動創新。
寫到這里,剛好看到網上關于某奧運冠軍和先生一起帶著幾歲的兒子去田間插秧的圖片,一時感慨萬千。培養具有高素質且全面發展的人才,帶他們體驗生產勞動第一線是一個必修課,青年學生必須體驗過最樸素的體力勞動,方能體會高科技下腦力勞動的辛苦,才會具備克服自身惰性、勇于攻堅的品質。所謂精神世界,從來都是以物質世界為基礎的,如果沒有大汗淋漓的體力勞動感受,也就很難對腦力勞動的艱辛做好心理準備,或許這是我們覺得生活條件好了,學生卻少了從前那種刻苦學習、不怕挫折的精神的一個原因。
沒有豐富的生活經歷,沒有快樂的勞動體驗(體力勞動也會產生令人興奮的多巴胺),沒有創造的學習過程,沒有獲得的努力付出,我們年輕學生的好奇、樂觀、堅持、抗壓精神將通過什么途徑去培養?而學習本身也就是勞動。
(作者系復旦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
責任編輯:樊效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