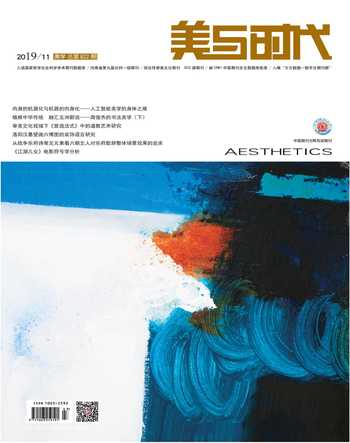諸法歸心
摘? 要:構圖在繪畫寫生與創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呈現的是從藝者觀看世界的角度,作品構圖的處理方式直接影響其創作目的和意圖的表達。油畫風景寫生創作中,構圖表現能力的高下,直接影響其作品質量的高下。油畫風景寫生創作中畫面構圖表現能力經過從無法至有法,再至無法各階段,而各階段之間具有內在關聯。構圖作為創作者傳遞給觀眾的首要形式,除了作品的色彩、造型等具體技巧之外,其方式必然折射出作者獨特的內心世界,即藝術創作諸法歸心。
關鍵詞:風景寫生;構圖能力;超越規矩;諸法歸心
構圖在繪畫寫生與創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呈現的是從藝者觀看世界的角度,作品構圖的處理方式直接影響其創作目的和意圖的表達。“一幅畫、一個設計,構圖不成功就沒有什么意義了,只有有了良好的構圖,各種技巧才有依附的骨干。”[1]構圖表現能力是藝術家在一定的畫面空間安排和處理各要素關系位置、把個別或局部形象組成藝術整體的能力,是為更好地表現作品主題和美感效果構建獨特畫面形式的能力。當下,風景寫生由過去以提高專業能力為目的的小范圍自主活動,轉化成藝術界內聲勢浩大的組團寫生現象。創作水準的提高所涉及的因素林林總總,不過,就提高寫生創作能力而言,如何處理好自己畫面的構圖就成為了首要的課題。為了更好地認識藝術實踐過程中的諸多因素,本文著力于構圖能力不同階段的分析,旨在厘清油畫風景寫生實踐中形式探索的諸種狀態,使從藝者明了獲得創作能力真正提升的內在淵源。
一、達情之需
構圖這一概念最早源于西方美術,它是畫面形式的整體設計。“構圖是造型藝術的形式結構,是全部造型因素與手段的總合。”[2]在中國傳統繪畫中與構圖對應的詞匯是經營位置、章法或布局,展現作品的整體骨骼和框架結構。構圖設計既是繪畫創作中情感表達的起點,也是如此表達以什么視角來實現的終點。所以,構圖設計不只是構思以后落筆的第一步,更是創作過程的整體實施、創作面貌最終呈現的首要因素。
恰當的構圖形式可以充分展現創作者的審美趨向和現場感受,表現作品的主題,提升作品的整體氣質;相反,面對再好的風光景物,如果從藝者沒有為自己的視角找到一個恰當的構圖形式,其創作必然會與其初衷相違,缺乏藝術感染力。
油畫風景寫生不僅能提高實踐者對空間、色彩、造型諸多方面的處理能力,而且它本身也是繪畫創作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關鍵在于,如何將眼中之景內化為心中之景,進而落實于具體的構圖之中。將簡單的寫生訓練升進為對景的直接創作。“一千個讀者眼中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因為不同人的個性心理、成長背景,甚至不同的情緒狀態,閱讀莎士比亞的《王子復仇記》時,當然會收獲各不相類的意境。繪畫寫生何嘗兩樣,面對同樣的風景人物,由于從藝者自身素養、專業能力、審美取向的差別,最終作品的呈現形式自然相異。
二、生發構圖
美國藝術理論家伊恩·羅伯茨在《構圖的藝術》中指出:“印象深刻而又吸引人的構圖不是在你結束繪畫時最后一筆落下的時候才會形成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構圖肯定是在進行繪畫之前的思索階段就已經形成的。”[3]構圖過程果如其所言嗎?鄭板橋早有“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畫語①,讓我們看到中國藝術家如何在意境營造過程中,“心眼”對“肉眼”所見的涵化。其實,此涵化過程正是“心、眼、手”相互觸碰,相互尋求契合的過程,鄭板橋道出了其間差異性之“非”,其“非”自是磨合的前提,也是每每生發新機的開始。在這種差異性的磨合觸碰間,“自然之竹”漸變為“藝術之竹”,其漸進的過程正是主體心靈與自然事物屬性的磨合過程,也是心靈將所欲見之形象傳諸此手,借以達愿的過程。細細追尋起來,這每一個階段都含融著某種相互的抵牾與順隨,找到其間共同的觸點,就找到了藝術表達的形式語言。所以,構圖或許早已緣起于胸中,但它作為一種意愿,恐怕實現起來尚要與眼中之景、手中之景反復切磋琢磨,那么,它就不可能先在于進行繪畫之前的思索階段形成。未動筆之前,“構圖”作為一種意愿內存于心,它是一種觸機,一種觀察世界的個性化視角,將其實現出來尚離不開現實景物的激發,以及從藝者手頭技藝所獲能力的交相碰撞。可見,伊恩·羅伯茨所說的胸中早已形成的構圖,確切地說應該是心里一種朦朧愿景才對,構圖,起于此愿,終于此愿與此景、此手的觸碰契合,將之落實于畫面,其間還有多遠的距離,恐怕也只有具體實踐者甘苦自知了。
這種隨機應變、自然生發的觀念,并不僅僅為板橋居士所獨有,傳統文化中順遂自然、化合陰陽的思想深深影響著中國藝術精神的發展。孫過庭在《書譜》中說:“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4]雖為論書,亦可通于論畫。最終作品會呈現出什么樣子,其實在落筆之初就已經確定了,但這個“定格”之作品,卻并沒有提前呈現,而是因書寫者或繪畫者的內在意愿,因其手頭技能的強弱,在接下來的協調配合過程中引發出作品成型的趨勢。
油畫風景寫生創作中,如何內化現場景物,深思靜構,復以完整的構圖形式展現于畫布之上,豈不與“自然之竹”轉化為“藝術之竹”的升華過程相類?
(一)無法至有法
筆者體會到,在藝術創作過程中,從自然形象到藝術形象的轉換無非人們常說的三個階段,從無法到有法再到無法。繪畫的創作焉能例外?構圖的生成焉能例外?
石濤說:“太古無法,太樸不散,太樸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畫。一畫者,眾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眾法也。”[5]199古人作畫本無方法,但落筆逐意,就在這平面的虛空中界劃出“一畫”,“一畫”既生,復生萬象,其間的自然磨合,成就了藝術的最初之法。“一畫之法,乃自我立。”并非立自石濤,而是立自每一個藝術實踐者。所謂一筆生二筆,二筆生三筆,三筆貫萬筆,正是《道德經》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思想在藝術創作領域的折射。繪畫創作中構圖的生成自然不能例外。
但是對于初學者而言,石濤所說的“無法生有法”,卻并不適用,因為“太古無法”,所以古人落筆隨心,自成其法,而后人卻無緣再真正處于無法的世界。世界早已被前人創造的文明所洗禮,世界已不是嬰兒眼中的世界,我們不可能真正回復到人類的童年時代。后人面對的正是有法的世界。對于求藝者而言,最初的學習必須從自身的無法所適進入到前人創造的有法世界,了解規則,熟習規則,才可能談得上未來拋棄規則,再造新規則。
初學者外出寫生,在真實的自然場景中,往往一籌莫展,不知如何將現場景物整理至畫面,該畫什么,不該畫什么,取舍不清,被動地照搬環境中的實物和色彩,畫面造型、色彩、構圖常是混亂一片。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關鍵就在于其對藝術史上重要畫家的表現形式不熟悉,在自然與個人感受之間尚未找到聯系的紐帶。其實,對于任何從藝者來說,都無非要面對兩個方面一個問題,一方面是藝術傳統,一方面是現實生活,以及如何將傳統與現實生活交融在一起,再經由個人心性的擇取進行個性化的創作。對于初學者而言,模仿大師作品中的表現形式將逐步使其獲得語言的規范性,使其眼中世界逐漸清晰化、秩序化。
構圖形式從畫面的基本結構來看,大體可分為水平構圖、對角線構圖、對稱式構圖、S形構圖、三角形構圖、直角形構圖、三分法構圖,以及按照黃金分割的比例關系進行畫面內容主次分配處理等樣式。然而僅僅了解這些還不夠,關鍵是如何靈活運用。
自然景物各要素之間復雜而緊密,它們相互依托似乎并無主次。研究大師作品,看他們是如何將這些基本結構自然化合在具體的畫面中,同時也能感受到該創作者構圖中所傳達出的其觀察世界的角度,并以此體驗去寫生中加以印證。隨著時間的推移,對諸種構圖形式的熟練掌握使實踐者逐步走向秩序化。這便是從無法至有法的過程。
(二)有法至無法
對秩序、條理的渴望是人的內在需要。沒有人愿意過混亂無章的生活,當然也沒有人愿意接受雜亂無章的繪畫。而對于繪畫的秩序化首先起于對構圖的合理設計。對經典傳統語言形式的熟習,使創作者在寫生中主動根據現場景物的特點和寫生對象的區別,為抒發自己的真實感受和表現作品的主題,遵循構圖的一般規律,在既有的構圖樣式中精心取舍、設計畫面的結構。但是,僅僅依據已獲構圖法則作畫,作品又容易呈現老套式的表達,難以令觀者耳目一新。
法則的獲取不是目的,目的是藝術上的自由創造。如何打破規律、突破固有形式的束縛,傳遞鮮活的情感,完成破繭成蝶式的跳躍?塞尚的經典作品便表達了他對以往視覺經驗的革命性突破。例如其代表作《圣維克多山》,飽滿的構圖在堅實的線型結構中展開,作品顯然突破了構圖形式的常規化結構,三角形、隱性的對角線形、水平線、S線等結構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使得該作從一入眼便給人以豐富的視覺印象。特別是畫面上方伸出的樹枝將天空布滿,左右彎曲的枝條走向與畫面中下部略偏直線分割的空間設計形成鮮明對比,同時又與畫面其他部分的重色形構相呼應,在總體安排中堪稱神來之筆,極具表現力。
可見,靈活應用不同的構圖形式對復雜場景進行主動取舍、精心布局,處理好畫面中各部分之間的關系,從原有的規矩法則中超越出來,是從藝者寫生過程中審美意識的覺醒與升華。這樣的寫生從一開始便超越了一般寫生訓練的性質,而呈現出鮮明的創作傾向。
石濤說:“古今法障不了,由一畫之理不明,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可從心,畫從心則障自遠矣!”[5]203-204當從藝者經過多年的積累,對傳統中的諸種表現形式皆有所得時,即已進入有法的狀態,亦是其入“障”的狀態,因為“此法”終究還是前人之法,以前人之法觀物自是身在“障”中,而褪去此“障”在心不在眼,個體之心消化諸法外相,靜中體悟,超越規矩,看似丟棄了法則,重又回到無序的狀態,實則此時的“無法”正是放松身心感受景物環境,自由調動畫面構圖的狀態。所謂“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為至法”[5]206。這便是藝術創作從有為到無為、從有形到無形、從有法到無法的狀態。“無法”不是真沒有方法,而是放下本已掌握的諸法,直指本心之法。此時油畫風景寫生中現實景物的各個要素不再“始終如一”,其面貌隨“心”而動,創作者將依據心愿構圖,諸元素亦時有變動,搬山挪水,移樹運石皆是司空慣見之事。正是這種改變使寫生作品從構圖到畫面具體物象都有了與現場景物的不同形貌,使畫面擺脫了對自然照搬式的依賴。自然在此刻便成為創作者的資料庫,隨其取用。寫生不再僅僅是繪畫的訓練方式,而升華、蛻變成為從藝者對自然世界獨具觀察視角的個性化解讀,及其自由抒發情感思想的創作形式。
三、諸法歸心
“構圖是繪畫作品中各種藝術語言整體的組織方式,相對構成而言,更多的是根據畫家的創意,把自然的具體的形態和形象,如人、景、物,通過提煉、加工,有計劃地組織、安排在限定的畫幅之中。”[6]在油畫風景寫生過程中,創作者從感受出發,自由提取自然之物構造畫面,各要素的形成和整體結構在自然原始要素基礎上變化、取舍,最終達到寫生創作有感而發、借景抒情的初衷,完成自然形象向藝術形象的升華。這期間究竟以何為準呢?《金剛經》中說:“法尚應舍,何況非法”“非法非非法。”以之為據,從藝術實踐的角度來理解有法與無法,從藝者澄懷以對,調動自身潛能,渾融諸法后的表達卻又不是曾接觸的任何方法,但自成家法就是無法嗎?站在較遠的距離觀察,其實非法何嘗不是諸法之外的又一種方法?因此,即便已經形成自我風格,創作中同樣應該放下自家定式,否則便又進入到自我重復之“障”。古人所謂“滌除玄鑒”“疏瀹身心”就是要求修行者澄凈心靈,忘懷俗世的陳規陋習,舍棄一切既成之法使身心進入到一種空明寧靜、自由舒展的狀態。從審美角度看,這種狀態才是真正創作生成的狀態。
藝術乃心靈活動的跡象化。是心之欲促使藝術作品展現不同的變化。構圖作為創作者傳遞給觀眾的首要形式,除了作品的色彩、造型等具體技巧之外,其方式必然折射出作者獨特的內心世界。相由心生,法依心起,什么藝術創作之法不是心靈找尋表達自身的形式呢?萬法歸心,法由心造,自然是畫隨其心而不是畫隨其景。
好的油畫寫生風景創作不僅能令觀者體驗到萬物之聲,亦能令其與一顆獨立創造的心靈相會,并由此喚起人們對光明、崇高的向往與追求,對美好生活的憧憬與熱愛,這也許正是一切藝術創作的價值與意義吧!
注釋:
①“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于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紙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見鄭板橋.板橋畫論[M].王其和,點校纂注.濟南:山東書畫報出版社,2009:5.
參考文獻:
[1]蔡南生.風景畫構圖與色調[M].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14.
[2]劉寅.繪畫構圖要領[M].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16:1.
[3]羅伯茨.構圖的藝術[M].孫惠卿,劉宏波,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8.
[4]孫過庭.書譜[C]//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畫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130.
[5]韓林德.石濤與“畫語錄”研究[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89.
[6]蔣躍.繪畫構圖學教程[M].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2.
作者簡介:劉明友,碩士,陜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