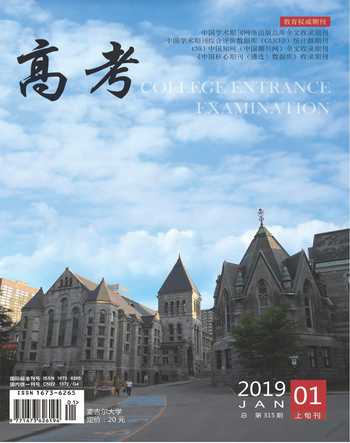《帶家具的出租屋》中男青年的心理分析
郭楠 張斯雨 李沛夏 王彤
摘 要:《帶家具的出租屋》是一篇風格獨特的作品,體現了歐·亨利寫作風格的變異。但前人研究大都關注歐亨利獨特的幽默筆觸,對這部風格悲愴的作品及人物塑造多有忽略。因此,本文將從弗洛伊德的理論入手,分析男主人公的心理變化,從而對這部作品以及歐·亨利的寫作手法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
關鍵詞:《帶家具的出租屋》;弗洛伊德;心理分析
一、引言
歐·亨利是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其小說準確地勾勒出一個個豐滿的人物形象。在小說《帶家具的出租屋》中,他用沉郁頓挫的筆法描繪了出租屋內的悲劇故事。歐·亨利對男青年的心理形象刻畫角度多樣,意味深厚,因此,對其進行心理分析,以便進一步了解作者的寫作手法十分有必要。本文將運用弗洛伊德的分析理論中本我、自我與超我理論對其進行心理分析。按照小說的敘事順序,首先運用自我理論來分析男青年在愛情追求與冷酷的現實環境之中所做出的妥協。其次,運用本我理論分析男青年在聞到花香后重燃的愛情理想。最后,運用超我理論分析男青年在看清社會的冷酷真相后,所展現出的深深的絕望。
二、自我層面:忠于愛情,屈于現實
弗洛伊德認為,人的自我有一個把外界的影響施加給本我的傾向,并努力用現實原則代替在本我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快樂原則。[1]
文章中的男青年是一名徘徊在對愛情的希望和對生活的失望中的悲劇角色。
對愛情的追求是他的本能欲望。他“白天去找劇院經理、代理人、劇校和合唱團打聽;晚上則夾在觀眾之中去尋找”[2]盡管尋找的過程如此艱辛,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因為他這樣煞費苦心地孜孜以求,是要找到讓自己的靈魂存活下去的希望,否則他只能無情地被黑暗的現實吞噬而走向毀滅。[3]
但冷酷的社會讓男青年的“本我”向現實原則妥協。文章開頭處對男青年的動作描寫,暗示了他身體的疲憊和內心的不安。這來源于男青年所處的社會地位。當時的美國,其實是“以千百萬民眾的痛苦為代價,成就了像范德比爾特,卡內基和洛克菲勒這樣的人的成功”[4]男青年作為一名底層階級的小人物,被殘酷的現實壓迫地喘不過氣來,他對愛情的渴望也顯得尤其渺小。這就是為什么文章開頭時,男青年所呈現的是他“自我”層面的心理狀態,也為后文男青年聞到花香,勾起“本我”層面,即純粹的愛情追求埋下伏筆。
三、本我層面:重燃希望瘋狂尋覓
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人有兩種本能:一是生的本能,“生存本能象征著愛和生產的能量。”[5]二是死的本能。“關于死亡本能,它的摧毀與破壞有內向與外向之別,內向的破壞指生物體對自我進行摧殘,外向的破壞指生物體對他人進行摧殘。”[5]
文章中,男青年為尋找心上人做出諸多努力。由于“人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性、本能和快樂。自我不斷尋求對植根于本我中的生理和本能的欲望的滿足,即感官的愉悅。”[6]所以,當他在房間中以為自己聞到了她身上的芬芳時,他的感官得到了愉悅,因此他表現出了強烈的“生的本能”。
在本能的驅使下,他努力追尋這帶給他愉悅的希望,“他把整個房間從一端到另一端篩了一遍”[2]男青年毫不壓抑的愛情追求主宰了他,那絲近乎幻覺的香氣在喚醒他生的本能的同時,也將他推向死的深淵,木樨香的出現為最后的死亡積攢了必要的力量。
在文章后半段,男青年則表現出了“死的本能”。他的希望破碎,愉悅和滿足消失,沖動也由外部轉向內部。
四、超我層面:孤獨幻滅休于濁世
超我是人格結構理論中的第三重人格,也是最高層次。超我是由社會規范、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內化而來,追求完善的境界。[7]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物欲橫流,道德破敗,女房東極力推銷的“特別好的房間”里是死去的情人。金錢至上的扭曲價值觀使人們冷眼看淡生死,與男主人公的愛情追求站在了對立的兩端。
弗洛伊德在人格結構理論創建末期,于超我理論中加入了自我理想的概念[8],男主人公的自我理想就是愛情,可隨著一次次失望,他的理想就如潰敗的倫理道德一般,被殘酷的現實所擊倒,并逐漸走向毀滅。文章后半段中,男主人公踉蹌的步伐是理想幻滅的寫照:女房東歷任房客中沒有木樨草香的主人,他的愛情理想成了幻影,這間房里除了"朽爛的霉味",虛假與破敗,只剩下孤獨。
在超我理論中,嚴厲的超我已經為社會行為制定了常態的模式,如果不遵循這種模式,結果便是用自己作懲罰[9]”當男主人公凝視昏暗煤氣燈,冷靜周詳地著手每個自殺步驟,并“欣然”躺上床接受死亡時,他的理想信念在冷漠中消失殆盡,他清醒過來,看到了現實世界的模樣:破爛的家具,發霉的墻體,人際的冷漠,金錢綁架和欲望裹挾。他純真的愛已然破滅,卻又無法妥協成社會的一部分,冷酷的社會迫使他用死亡躲避拜金主義的侵蝕與失去愛情的事實。他用自己接受了社會的懲罰。
五、結語:
歐·亨利的小說通常因為“無法預料的結局,別出心裁的構思,幽默中又帶著冷酷的語言”[10]聞名于世,然而,這部小說卻顯得尤為不同。在這部作品中,作者用細膩的筆觸渲染出了悲愴蒼涼的意蘊。身處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之下,主人公的內心活動顯得尤為敏感。他的所思所想不僅展現了個人命運的浮沉,更進一步揭示出黑暗的社會背景。在美國從“黃金時代”過渡到“鍍金時代”之時,整個社會彌漫的也是一股悲涼之氣,許多人像男主人公一樣堅守著人類的美好感情,卻在絕望中一步步走向滅亡。可以說,通過展現男主人公的行為與思想,歐·亨利將當時社會的縮影都體現在這部小說里了。
參考文獻
[1]弗洛伊德.一個幻覺的未來[M].上海:華夏出版社,1989.
[2]歐·亨利.歐·亨利短篇小說集[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2009.
[3]高璐.歐·亨利小說中的象征意味—以《帶家具出租的房間》為中心[J].榆林學院學報,2017,(5):84-86.
[4]常耀信.美國文學簡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
[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M].長春:長春出版社,2004.
[6]陶曦.心理分析理論與文化研究[J].國外理論動態,2003,(10):41-45.
[7]何伋,陸英智,成義仁等.神經精神病學辭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8.
[8]林崇德等編.心理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9]張婭.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視角下解讀托尼·莫里森的《家園》[J].安徽文學,2017,(08):45-46.
[10]周玲.以《警察與贊美詩》為例探究歐·亨利的寫作風格[J].長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14,(11):60-61.
作者簡介:郭楠(1998,01-),女,漢族,湖南人,本科三年級在讀,研究方向為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