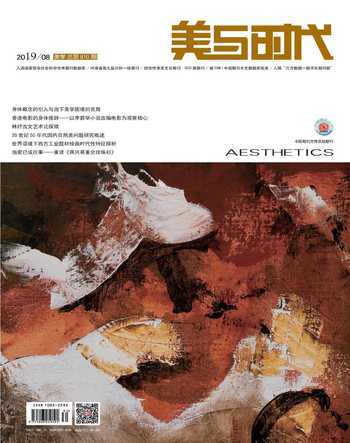梅洛-龐蒂的空間觀念探析
摘? 要:在《知覺現象學》中,梅洛-龐蒂不只是在討論身體問題時介入了空間觀念,還專辟一章來論述他對空間問題的思考。梅洛-龐蒂放棄了先前哲學家持守的空間觀,確立了身體空間,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空間思維模式。他旨在從有關空間的各個角度探尋本己和世界之間的復雜關系,建構起新的空間觀念。
關鍵詞:梅洛-龐蒂;空間;身體空間;時間;深度
在《知覺現象學》中,梅洛-龐蒂不只是在討論身體問題時介入了空間觀念,還專辟一章來論述他對空間問題的思考。有學者認為海德格爾主要從時間角度討論問題,而梅洛-龐蒂則偏重于從空間角度來討論問題,這一說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事實上,就身體問題而言,梅洛-龐蒂認為:“我的身體在我看來不但不只是空間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沒有身體的話,在我看來也就沒有空間”[1]140,明確把空間的存在建立在身體的存在上;在《眼與心》里討論繪畫時,他認為空間是自在的,方位、包圍等要素都是空間的派生現象。而在論述身體的空間方面的問題時梅洛-龐蒂并沒有拋棄時間觀念,“不應該說我們的身體是在空間里,也不應該說我們的身體是在時間里。我們的身體寓于空間和時間中”[1]1185,而物體在空間的存在又是靠前一個時間波和后一個時間波的擠壓而得以可能。此外,據相關統計,在《知覺現象學》和《行為的結構》中時間共出現八十多次,空間一詞出現一百九十多次,表明空間的重要性明顯高于時間。學者楊大春認為梅洛-龐蒂的身體的空間性“開啟了思維的空間模式”,這種空間思維模式拋棄了先前哲學家持守的觀念空間觀和在己空間觀念,確立被后來哲學家所接受的身體空間性,這也說明了空間觀念在梅洛-龐蒂哲學思想建構中的重要性,而理解梅洛-龐蒂的空間觀念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他對重要哲學命題的思考。
梅洛-龐蒂在談論身體本身的空間性時,否定了身體是身體各個器官的并列組合的觀念,身體的空間性實際是一種“處境的空間性”,例如,我坐在在書桌旁,雙手放在書桌上,我的手位置不是通過我的坐姿以及手臂和肩膀的一般身體空間的位置推斷出來的,而是以我的一種絕對能力確定的。這里,梅洛-龐蒂引入“身體圖式”來說明“處境的空間性”,“‘身體圖式’是一種表示我的身體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1]138,這表明我們對身體的感覺不同于對外界事物的感覺,我們能知道我們手握筷子時手的位置和筷子的位置,這不需要經過理性判斷,不需要和肩膀以及手臂來比較確定手的位置,“身體是我們自己的身體”,不需要尋找和思索。可見,身體本身的空間性區別于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空間形式,并有自己獨特的意義。接著,梅洛-龐蒂指出兩者的存在關系:“即使一般空間形式是為我們的身體空間得以存在的必要條件,它也不是為我們的身體空間得以存在的充分條件。”[1]139我們在認識了身體本身的空間性后,就能夠認識日常生活中一般的身體空間,但是和一般身體空間相比,對身體本身的空間性的認識才是最根本和最必要的。
那么,我們到底如何認識空間呢?梅洛-龐蒂首先考察了經驗主義和理智主義對空間的認識,認為兩派所認識的空間性既不是“物體在空間的空間性”[1]316,也非“能空間化空間的空間性”[1]316,而應當區分空間的形式與內容來重新理解空間。如果我們要重新理解空間體驗,就要摒棄先前形成的概念,比如我的左手向上抬起,像“左”“上”等這些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空間概念需要暫時擱置起來,因為“僅僅靠這些場—方位標不足以形成任何一種方向”[1]314,在物體中僅需要兩個點就能確定一個方向,但我們的身體不是在物體中,而是有感覺場存在,觸覺、身體場、視覺場(這些感覺場)是隨著體驗的不斷變化而變化。在這里,梅洛-龐蒂使用了“視網膜映象變正”的例子來說明空間體驗與感覺場變化的關系:在實驗開始后,我們給被試者戴上一個能使視網膜變正的眼鏡,被試者覺得所看到的景象都是顛倒的;到第二天時情況有所變化,被試者感到自己的身體也是顛倒的;到第八天時他感到看到的景象不再顛倒,只是身體處在不正常的位置;直到最后的三到七天,他覺得身體逐漸恢復正常位置;實驗結束時,他感到身體完全處于正常位置。在這個實驗中,一開始被試者的觸覺世界和視覺世界保持一致,一直是正的,但隨著實驗的進行,被試者的視覺世界發生顛倒,視覺世界不再與觸覺世界保持一致。這意味著我們的空間體驗發生變化時,感覺場也會隨之變化,因而物體在世界中的方向發生變化,這樣就導致“世界的定位有無數種,‘上’和‘下’失去了可確定的意義”[1]315,也意味著如果主體找不到一個能容納所有空間規定性的實際出發點,一個絕對的點,那么主體便沒有方向,因而他的存在也就沒有空間。而問題是:重新定向又該從何處開始?顯然,梅洛-龐蒂給出了一條解決途徑:“通過有感知能力的主體的整體活動來完成”[1]317。那么,空間問題又回到了身體本身,“擁有一個身體就擁有變化平面和‘理解’空間的能力”[1]320,這就“把我們帶到主體和空間的有機聯系,主體對作為空間起源的他的世界的這種把握”[1]320。
上面的例子和論述讓我們明白空間本質的東西始終是“被構成”的,我們個體的空間體驗不能給我們提供絕對的方向,只有主體回到對世界的知覺中,對空間的理解才有一定的可能。基于此,我們對“什么存在是有方向的”“為什么存在是空間的”這類的發問已經失去意義,因為在這些問題中,我們的身體沒有參與對空間的體驗。以存在來論證身體空間的能動性,從這個角度看,存在變成了處在。梅洛-龐蒂自己也說“存在就是處在”[1]321,這種試圖把身體空間和世界的構成關聯起來的思路,無疑不同于靜態的位置空間。正因為前期的這種認識,在他后期的著作《眼與心》里,梅洛-龐蒂說“深度、顏色、形狀、運動、輪廓、外貌等都是存在的一些分支”[2]163-164,他直接把空間的維度——深度看成存在的一個分支。到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梅洛-龐蒂的身體空間性事實上也體現出與存在論、現象學的空間思想相互勾連的關系。
和傳統哲學及心理學一樣,梅洛-龐蒂也討論了空間知覺:“我們必須承認空間知覺是一種結構現象,空間知覺只能在知覺場內得到解釋。”[1]356我們前面已經提到主體為找到物體的空間,首先必須確定一個“絕對的這里”,而知覺場才有可能向主體提供一個“絕對的這里”,在這種知覺空間的構建中,梅洛-龐蒂認為身體優先于心靈而存在。梅洛-龐蒂表示對空間的討論不應該停留在空間知覺方面,應該擴展開來繼續進行研究。梅洛-龐蒂在擴展他對空間的研究范圍時,發現在夢中、神話和精神分裂癥患者中也存在“空間”,但在幾番論證后,發覺它們的主體空間性難以想象,這些命題并無意義。
“我們說過,從寬度、高度和深度看,空間的各個部分不是并列的,而是共存的……”[1]350在空間維度方面,梅洛-龐蒂著重討論了深度,他表示:“深度比其他空間維度更直接地要求我們摒棄關于世界的偏見和重新發現世界得以顯現的最初體驗”[1]326,并且他同意貝克萊關于深度是最具有“存在性”的特征的論述。此外,與作為物體之間關系的高度和寬度不同,深度則直接揭示主體與空間的關系。按照傳統的觀點,“深度體驗在于辨認某些已知事實——雙眼的輻合,映象的視大小——并把這些事實放到能解釋它們的客觀關系的背景中”[1]327,這就意味著視大小和輻合是被當作深度的客觀關系中的因素來討論的,梅洛-龐蒂認為我們應該擱置科學知識或幾何學所看到的深度,應當從深度的內部來理解,以此來探明深度是如何揭示主體和空間的關系問題。基于此,梅洛-龐蒂否定了格式塔心理學對視覺大小和輻合得出的結論:視覺大小和輻合是深度的條件和原因。例如,我們在客廳感知到遠處的茶幾、電視和背景墻時,我們并沒有明顯感覺到這些物體在我的視網膜映象和對身體的某種程度的輻合,因而它們無法作為被感知的事實。如果是這樣,深度結構就無法產生。因此,他認為“輻合和視覺大小既不是深度的符號,也不是深度的原因”[1]329,它們“不是作為‘原因’奇跡般地產生深度結構,而是不言明地引起深度結構”[1]330。那么我們在談及物體的深度和大小時,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深度結構的不同?梅洛-龐蒂認為我們在感知到物體的那一刻并沒有把物體與其他物體,或者我們身體的大小或位置作比較,我們對物體深度和大小的感知是相對于我們的知覺的范圍,相對于現象身體對周圍環境的某種把握而言的。這種對深度的分析和對身體本身的空間性的分析如出一轍,都撇去我們一開始就被客觀化的、與體驗分離的思維方式,而是重新發現深度和其他維度背后的隱藏意義。因此,對于深度,我們不能理解為“一個先驗主體的思維,而是被理解為一個置身于世界的主體的可能性”[1]329。
在笛卡爾和貝克萊看來,深度空間是一種理性意義上的抽象空間,這種抽象空間剝離了我們感性的知覺世界,也割裂了我們與世界原始意義的聯系,正因為如此,梅洛-龐蒂認為這不是真正的深度。在《眼與心》中,梅洛-龐蒂尤其肯定繪畫,認為畫家才是真正與世界建立起互動與溝通的藝術家,畫家帶人們穿過事物的表象,深入世界的內在,也正是畫家才讓深度的存在真正展現出來。畫家阿爾伯多·基亞格梅迪說:“我想象塞尚的整個一生都在尋找深度。”[2]152羅伯爾·德洛奈則說:“深度是新的靈感。”[2]152梅洛-龐蒂感嘆:“在文藝復興對深度的‘解決’過去了四個世紀,笛卡爾的理論過去三個世紀之后的今天,深度一直是個新的課題;而且它要人們去尋找它,不是‘一生中只找一次’,而是終生尋找。”[2]152梅洛-龐蒂是塞尚的好友,他們之間常有關于繪畫的書信往來,梅洛-龐蒂也自詡最懂塞尚。他在《眼與心》里寫道:“當塞尚尋找深度的時候,他尋找的就是存在的這種驟然爆炸,而它存在于空間的一切方式當中,也存在于形狀當中。”[2]153塞尚的這種尋找像是“撕開事物的表皮”,探尋事物如其所是的樣子,這與梅洛-龐蒂對深度空間追尋的初衷大抵一致,塞尚在繪畫里尋找深度的途徑似乎為梅洛-龐蒂提供了一把“開啟一切的鑰匙”。在后來的《可見與不可見》中,梅洛-龐蒂發現身體既是感知主體,又是被感知的客體,身體形成一種主客體的混亂,這種主客體混亂交織的感覺使得他不得不回歸到對“肉”的關注,而在對深度的討論上,他有了新的認識轉向,認為深度視覺能產生主客體交織的狀態,深度有必要回歸到世界之肉的起源性。
可以看出,在對空間的重要維度——深度的討論上,梅洛-龐蒂的解釋發生了重要轉向,前期他的深度是在身體與世界的互動溝通中顯現出來的;后期他在對身體本身的本體論思維中做出反思,發現身體主客體交織的特點,因而他的深度開始走向對“肉”的回歸。
梅洛-龐蒂的空間觀念并未完全擱置時間觀念,他承認深度與其他維度的共存關系不只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并且認為“首先是時間的,然后是空間的”[1]350。那么,我們首先必須厘清梅洛-龐蒂對時間的看法,才能理解他如何把對空間的理解依存于時間之上。事實上,在梅洛-龐蒂看來,主體具有時間性,而時間也依存于主體的存在,例如一條河流流經A、B、C三個連續的地點,當A地的流水流動經過B地,再經過C地,B地的流水變成了A地的流水,C地的流水變成了B地的流水,時間恰如河流一樣,現在變成了過去,未來成為了現在,這是我們對時間的傳統看法。梅洛-龐蒂說,只要有一個主體觀看這條河流的流動,情況便大為改觀,比如我乘一艘小船順流而下,已經流逝的河水并非朝向未來,而是流向了過去。這就說明主體一旦從世界中被抽走,剩下的一切都將與主體失去意義,也就失去了時間性特征。“我不是在空間里和時間里,我不思考空間和時間,我屬于空間和時間。”[1]186,我是主體,有一個身體,主體通過身體在世界中活動,而前面已經討論過身體的空間性,在這里我們可以推論出并明確了身體包含時間和空間,“我的身體寓于空間和時間中”[1]185。
到這里,我們毫不反駁梅洛-龐蒂是“空間哲學轉向的第一人”這樣的觀點。梅洛-龐蒂在經驗主義和理智主義的空間之外,開辟出第三種空間。他的第三種空間從身體出發,重新審視客觀空間和身體、存在更隱秘的意義,并擴展他的研究,從空間知覺、空間維度、繪畫等方面層層分析,甚至引入他對時間觀念的認識,以此建構他的空間觀念。
參考文獻:
[1]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M].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2]梅洛-龐蒂.眼與心——梅洛-龐蒂現象學美學文集[C].劉蘊涵,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3]相鳳.法國當代哲學中的空間觀念[J].思想與文化,2017(2):491-502.
作者簡介:牛玉蘭,鄭州大學文學院美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美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