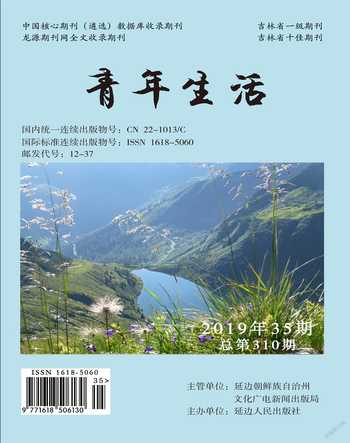義凈所見西行求法僧人籍貫聚集現(xiàn)象探析
張少鋒
唐貞觀年間,玄奘西行求法之事震驚朝野和整個佛教界,玄奘西行求法事件的發(fā)生,實則為應對國內(nèi)佛教發(fā)展困境而為之,是時佛教發(fā)展處于停滯狀態(tài),且相關(guān)教義漏洞百出,一些僧人在如此困境之下將視野轉(zhuǎn)向佛教發(fā)源地,有唐一代國力強盛,陸上絲綢之路得到了進一步的疏通和發(fā)展,海上絲綢之路則隨著海上貿(mào)易的發(fā)展,漸趨興盛。除此之外,安定的國際和國內(nèi)環(huán)境,使得唐初得以休養(yǎng)生息,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國內(nèi)物質(zhì)財富日益豐富,在此種主觀和客觀情況雙重利好境遇下形成了前往印度求法的高潮。
一、僧人籍貫的分布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成書于盛唐時期,為義凈所著。義凈自幼出家,咸亨二年(671年),由海陸出發(fā)前往印度,其在那爛陀修行十余年,因武后稱制,急需“稱述符命”,特招義凈回國,史載“天后敬法重人,親迎于上東門外”。
求法高僧傳中記述了唐貞觀年間至武后四十余年間五十六僧的西行求法事跡。該書成為研究是時中西海上交通,以及沿線國家風土人情的重要交通史料。此書之中對各僧籍貫進行了詳細記述,其中共有唐僧三十四人,這些人中竟有一十九人出自于南方,而荊、益二州又獨占一十一人,占義凈所見西行求法唐僧的近乎三分之一,占南方西行求法人眾半數(shù)以上。何以荊、益二州倍出西行之人,尚需從兩地佛教之發(fā)展談起。
二、唐代荊、益兩州佛教發(fā)展狀況分析
(一)佛教義理之學的興盛
東晉時期南方玄學大興,玄學在南方地區(qū)作為高品之學而在南方士族中廣為流傳。此時“善談名理者,挾其所學,南游江淮。……捍衛(wèi)之間,兩晉之際,俱有學士名僧之南渡。學術(shù)之遷徙,至此為第三次矣。自此以后,南北佛學,風氣益形殊異。南方專精義理……”。唐長孺先生曾經(jīng)指出“江南佛學之發(fā)達及其特點卻與玄學有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南朝之所以重義解,也正是在玄學盛行的氣氛中形成的。盡管隨著佛學研究的深入,佛學義理日益明顯,脫離佛經(jīng)本義的玄學化傾向不再繼續(xù),但南朝佛教之重義不僅出于玄學,而且繼續(xù)受到玄學的影響,并最終在更高的基礎(chǔ)上玄學化”。
南方地區(qū)佛教義理化的發(fā)展對激發(fā)該地僧侶產(chǎn)生西行取法之宏愿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義凈法師書中所載道琳法師西行求法源于“后復概大教東流,時經(jīng)多載,定門鮮入,律典頗朽,遂欲尋流討源,遠游西國。”;潤州玄逵法師,則“邊閑律部,偏務(wù)禪寂。戒行嚴峻,誠罕其流。聽諸大經(jīng),頗究玄義”;會寧法師亦“敬勝理若髻珠,棄榮華如脫履。薄善經(jīng)綸,尤精律典。思存演法,結(jié)念西方”,總而觀之,南方地區(qū)佛教的義理化,致使南方僧人思辨之能力普遍提高,通過對經(jīng)義的詳細研讀,發(fā)現(xiàn)其問題所在,由此便產(chǎn)生了尋求原本之佛經(jīng)的念頭,使得其中的有志之士將目光轉(zhuǎn)向了佛教的發(fā)源地,以期西行獲求真知。
(二)荊州佛教發(fā)展概況
荊州“府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漢之上路,襟帶江、湖,指臂吳、越,亦一都會也”,荊州之地地處交通之要地,亦為南北交流樞紐之地也。荊州佛教在漢魏時期地已經(jīng)開始流傳,直到東晉時期,荊州佛教開始崛起。北方佛教南傳之時,前往荊州及途徑荊州之高僧大德數(shù)量可觀,對荊州佛教之傳播大有裨益。
東晉哀帝時期,釋道安前往襄陽,宣揚佛法,“四方學士競往師之”,由此襄陽地區(qū)佛教大盛,其弟子亦積極向四周弘法,極大地促進了周圍地區(qū)佛教的發(fā)展。兩晉時期荊州佛教的活躍程度已經(jīng)可以和長安等佛教重鎮(zhèn)相媲美,據(jù)《高僧傳》統(tǒng)計,兩晉時期于荊州弘法的“義解”高僧達29人之眾,遠多于長安和健康地區(qū)的18人和12人。至隋及唐初期,荊州地區(qū)因其濃厚的佛教底蘊,吸引著高僧大德紛紛來此講學,亦促進該地佛教的進一步發(fā)展。智顗法師于開皇十三年(593年)前往荊州開壇講經(jīng),是時“道俗延頸,老幼相攜,戒場講座,眾將及萬”,盛況空前。至唐代,玄奘前往荊州講學時盛況亦如同前,“時漢陽王以盛德懿親,作鎮(zhèn)于彼,聞法師至,甚歡,躬申禮謁。發(fā)題之日,王率群僚及道俗一藝之士,咸集榮觀。”
(三)益州佛教發(fā)展概況
佛教傳入益州地區(qū)最早應在東漢晚期至三國時期,至東晉時期,四川地區(qū)的佛教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高僧慧遠弟子慧持“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矚峨嵋,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人蜀”,“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并絡(luò)四方,慕德成侶……時有沙門慧巖、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開巴蜀佛教傳播之風氣。隋末唐初,戰(zhàn)亂頻發(fā),此時江南之地亦受戰(zhàn)亂波及,而四川地區(qū)則因相對安全而吸引著大量人口的遷徙,是所謂“四方多難,總歸綿益”也,其中遷徙之人中不乏僧侶。
蜀地的安定祥和,使得一批高僧大德紛沓而至,在此地講學立說。玄奘法師亦曾居于蜀地數(shù)年以宣揚佛法,“講座之下,常數(shù)百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吳、蜀、荊。楚無不知聞”。釋神迥“擁錫庸蜀,流化岷峨……春秋六十五矣,四眾哀慟,悲其來法來儀,未幾而終,素懷莫展。益州官庶士俗,以同舟列道,爭趨奔于葬所。素幢競野,香煙蔽空;萬計哀號,生動天地”。
蜀地僧人外出求法至唐代已歷數(shù)百年的時間,無論是僧人對外出求法的接受程度,還是其先輩經(jīng)驗的榜樣作用均高于他處。四川為高山環(huán)繞,交通不便,從而導致蜀地佛教的發(fā)展較為閉塞。始自魏晉南北朝時期,“惟蜀中距當時佛教最盛之國都建康太遠,義學水平不高,故蜀中有志之士每嫌‘州鄉(xiāng)術(shù)淺’,下三峽趨建康,從名師進修多年,再西返鄉(xiāng)土,始能盛為講說”。《高僧傳》之中亦載有釋道汪“后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之思索者,亦有釋法琳“常恨蜀中無好宗師,俄而隱公至蜀,琳乃剋己握錐,以日繼夜。及隱公還陜西,復隨從數(shù)載。”之力行者。四川地區(qū)佛教的發(fā)展促進當?shù)厣畟H集團以及佛學事業(yè)的發(fā)揮發(fā)展,此外也促進了佛教在基層的傳播,使得四川地區(qū)佛教擁有著較為廣大的信眾。在其進一步的發(fā)展過程中,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則又激起了川蜀僧人向外求法之心。
三、結(jié)論
西行求法的僧人籍貫以荊、益兩州僧人為多。究其原因,其一,在佛教本身向外傳播的需求。其二,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地區(qū)盛行玄學,佛教為適應當?shù)氐奈幕諊识谀蟼鞯倪^程中逐漸義理化。其三,荊、益二州的佛教發(fā)展基礎(chǔ)較好。總而觀之,因荊、益兩州佛教之發(fā)展使得人們對于佛教適應社會的需要更加迫切,但在此過程中由于本土佛教逐漸陷入僵化,弊端叢生,從而激起了僧眾思源印度之情,以求取真經(jīng),促使佛教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