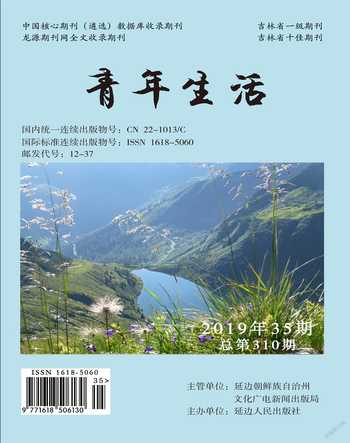《呂梁英雄傳》中的“鄉土中國”
辛搏文
《呂梁英雄傳》是第一部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民族抗日的長篇小說。作品講述了在呂梁山區一個普通的村落—— 康家寨,村民在日寇的燒殺搶掠中逐漸覺醒,在共產黨的帶領下,組織民兵力量同敵人進行殊死斗爭并取得勝利的故事。“鄉土中國”是該作品的敘事背景,其本身也隨著歷史的劇變而改變著,筆者將從鄉土地理、鄉土關系、鄉土道德三個角度來思考這部作品中的“鄉土中國”。
一、鄉土地理
在《呂梁英雄傳》(下文簡稱作品)的一開始,作者展開了呂梁山一角的地圖,“呂梁山的一條支脈,向東延伸……土地肥美,出產豐富真是一個好地方。山下有個大村子,名叫康家寨。東南七里是桃花莊,東北六里是望春崖。三個村正好成了一個鼎腳。……漢家山再往東二十里就是水峪鎮了。”
作者有意為之,在鄉土地理的合理條件下,“四村一鎮”在最初呈現了抗日戰爭中的三種農村模式:
敵占區:漢家山、水峪鎮
侵擾區:康家寨
抵抗區:桃花莊、望春崖
這部作品的人物和情節就限定在作者介紹的這“四村一鎮”的范圍內了。這種活動范圍的描述和限定,寥寥數字,便為整部作品搭建了一種合理的斗爭條件的地理空間,我們在閱讀作品中會發現,鄉土故事在這里發生,共產黨也將出現在這里,民兵們會嚴格依據作者交代的鄉土地理環境,進行機智勇猛的戰斗。隨著情節的推進,康家寨奮起反抗,聯合另外兩個抵抗村,擠走漢家山據點,走向解放水峪鎮的更大的勝利。
土地是農民的飯碗子,更是命根子,在農業社會中,即使面臨著戰爭,只要土地能夠生產,“在人口不流動的社會中,自足自給的鄉土社會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動的……”這是農業社會的根本性特征,不管是在現實中還是作品中,農民始終無法做到拋棄土地,民兵平時生產,抽空練兵習武,戰時便和敵人展開戰斗,并配合主力軍作戰。這既是作者經歷的現實,也是作者筆下這片鄉土上所發生的故事的基礎。
二、鄉土關系
鄉土關系無疑是復雜的,并非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或者是一廂情愿的理想化,在翻天覆地的20世紀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末,橫跨一個半世紀的中國革命是人類歷史個案中最宏大、最復雜的社會變動。這段時間的中國革命包含了政治學理論中所有類型的“革命”—— 千禧年式的農民叛亂(太平天國),無政府式的暴動(義和拳),政變(西安事變和林彪事件),軍事叛變(北洋軍閥時期),國共內戰(1945-1949),自上而下發動的全國性動亂(“文化大革命")。在作品所涵蓋的如此狹小的鄉土空間和短暫幾年的時間里,便涉及了代表千年農業封建國家基礎關系的地主-農民關系、共產黨與國民黨爭奪中國命運領導權的斗爭關系、抗日戰爭中的中日民族敵對關系、民眾內部的投敵與抗日的對立關系等,可謂紛繁錯雜。我們能夠看到作者為還原真實世界所做出的努力,也能看到他們的創作之余的遺憾。
作者并沒有呆板地寫成中華兒女對抗日本人和漢奸走狗的粗糙模式。傳統的地主-農民二元式的鄉土結構是作品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能夠看到漢奸走狗地主樺林霸一家、開明懦弱的地主“二先生”、搖擺不定的地主吳家兄弟、流氓走狗王臭子和康肉肉等、堅決的抗日民眾孟二愣和李有紅等、占大多數的普通民眾……搖擺地主充滿了投敵和抗敵的不確定性,民眾也會因為自家私利做出阻礙抗日的行為,但經過積極的指引是最堅決的抗日力量。這些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分別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也收獲了自己的命運,各類人物的立場與行動,還有情節的發展過程均合理流暢。我們不難發現有兩對矛盾始終貫穿著作品:一是中日民族矛盾,二是地主農民的矛盾。后一對矛盾既是當時的現實體現,又可以理解為共產黨實際工作的需要與文藝路線的體現。
三、鄉土道德
第五回,劉二則夫婦被康家敗等一伙走狗催租逼死,男女老少無不心痛落淚,二先生說“鄰家鄰舍的,總要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劉二則又沒有本家,大家湊點錢埋葬了吧!這可是個積德事情。”當下大家湊了些錢,置辦了兩副棺材安葬,窮人們幫忙送葬,康大嬸還收養了劉家孤兒。
第二十三回,鬼子掃蕩康家寨,逼供村民指出民兵,殘忍殺害村民數人,張忠老漢挺身而出,稱自己知道民兵下落,帶領日軍上山搜捕民兵,在山路上,張忠老漢高喊:“老武同志!石柱子!我姓張的總算對起全村人了……”然后抱著豬頭小隊長跳下懸崖同歸于盡,村民緊急逃跑,幸免于難。
這樣的細節還有很多,我們能看到根植于鄉土之上的中華民族的傳統義利觀,所謂義者,“事之所宜也”,是某種特定的倫理規范和道德原則,是儒家心中至高無上的道義。“義”居于中華傳統美德的首位,舍生取義是傳統中國人追求的最高境界,知恩圖報亦是傳統道德準則,毫無疑問,如果說老武同志有黨的意識形態的引導,那么張忠老漢為代表的具有道德光輝的普通群眾亦用行動踐行了道德追求。
筆者為什么要特地談鄉土道德的問題?一是這種鄉土道德是團結民眾齊心抗日,不怕犧牲的潛在的精神前提;二是鄉土道德和鄉土地理、鄉土秩序息息相關,作者對鄉土民眾的塑造離不開鄉土道德的支撐,歌頌真善美,以起到良好示范的現實功用。這些道德是驅使民眾抗日的內在動力,也是民眾能夠與共產黨人“魚水一家親”的內在準則;三是下文筆者要談到辯證看待鄉土力量成長為英雄的過程中黨的塑造與正義道德驅動的關系……
在激烈變革的20世紀,革命的號角被一個又一個團體或政黨吹響,這片土地上也正發生著深刻而又劇烈的變化,傳統的鄉土結構與鄉土秩序也隨之改變,《呂梁英雄傳》中的“鄉土中國”正是這部作品內在的結構支撐,只有理解作品中的“鄉土呂梁”,才能讀懂這部作品。
參考文獻
[1]馬烽、西戎:《呂梁英雄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第 1頁。
[2]費孝通《鄉土中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頁。
[3]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
[4]馬烽、西戎《呂梁英雄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第23頁。
[5]馬烽、西戎《呂梁英雄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第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