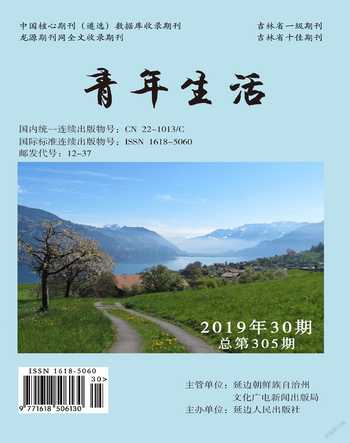女性承擔家務與育兒主要責任的作用機制探討
魏宇菲
引言
整個社會、家庭成員、女性自我對自身角色扮演的期望,導致男女性別不同的角色期待在家務分配與照料孩子的時間分配上體現的尤為突出,女性在家務與照料孩子上的時間投入遠超男性,這在女性已基本在收入上擺脫對丈夫依賴的今天,顯得尤為不公平,甚至出現當妻子成為一個家庭的經濟支柱時,丈夫分擔家務的比例卻并沒有相應升高,反而降低。而這樣結果的出現,是整個社會、家庭成員、甚至是女性對自我的角色定位都是應在照料孩子與家務上更多的付出,將女性在家務和育兒上的“無償奉獻”合理化。本文將探討社會、家庭成員、女性自身的角色期待如何影響女性在家務與育兒上的“額外”與“無償”付出。
一、社會系統的作用機制
(一)社會對女性的“期望”
中國是經歷了儒家文化影響幾千年的國家,在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女性的期望是“相夫教子”,完全退出社會領域,專職在家庭內部事務與育兒事務上,這樣的對女性的“定位”形成了對女性的審美與評判,即家務與育兒上的失敗女性要承擔大部分的責任,即使在今天女性在職場的要求與男性一樣的前提下,社會對女性的要求依然是承擔家務與育兒上的主要責任,原中央電視臺著名主持人、現為紫牛基金的創始人張泉靈女士曾談到媒體的采訪都要問她“作為女企業家,你是如何平衡事業與家庭?”而媒體卻很少去問男性企業家這個問題,即使去問,得到的答案是“媽媽在管家里”,而大眾卻認為這是習以為常的答案,很“正常”。而如果女企業家沒有在家庭上投入更多,媒體則會追問“你的人生不會有缺失嗎?”社會對女性在家庭事務投入上的期望,并沒有因為她們在社會的身份以及取得職業成功而有所改變,尤其是社會強加在女性身上的“母職”上的責任,沒有隨著時代變化而發生改變。
(二)社會支持系統的缺失導致女性在“育兒”上更多投入
中國的男、女工資存在較大差異同時差異正逐步擴大,首部婦女綠皮書《1995-2005 年: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報告》中顯示,中國男女性工資差距在不斷擴大。數據顯示,從1988~1995年:城鎮職工的性別工資差距逐漸擴大。就平均水平而言,女性與男性職工的工資之比,由1988年的0.84下降到1995年的0.82。在工資函數中,1988年女性職工變量的系數估計值比男性低1.8%,到1995年則大約低16%,在中國,從1998-2018年這20年市場機制作用的加深和競爭激烈的加劇,性別工資在持續擴大,在這一結果作用下的家庭決策上,往往出現女性退出勞動領域,以讓家庭規避較大的風險,在面對看護孩子的家庭決策時,往往更容易做出女性回歸家庭的決策。
特別在一些育有孩子的家庭中,如果孩子年齡太小(處于幼兒園前的看護階段),在夫妻雙方都有能力參與勞動的情況下,在孩子接受幼兒園教育之前的這個階段,女性很容易退出勞動力市場進而在家看護孩子,因為孩子在這個階段的看護成本非常高,同時由于幼兒看護支持體系的缺失,這個時候看護孩子很少能通過購買服務來實現,因而女性會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選擇在家看護孩子。
其次,我國幼兒教育體系不完善。隨著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加快,原來由國有企業進行承擔的幼兒教育在國有企業改制后主體發生多元化,一部分效益好的國有企業在繼續創辦幼兒教育的同時積極探索承包制形式,而另一些效益差的隨著國有企業的倒閉一起倒閉,還有一些財政狀況好的地區一起移交給地方政府,成為公辦幼兒園,因而,由于幼兒教育的供給嚴重不足,這給私人辦幼兒教育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同時,一直以來我國大力對九年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進行投資,卻缺少對幼兒教育的投資,進而導致幼兒教育的發展在市場化資源配置的作用下,發生了嚴重的不均衡,幼兒教育的收費較高,幼兒教育的成本在急劇上升,根據家庭生產的時間配置與市場勞動時間配置的關系,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已婚女性選擇時間密集型的家庭生產模式的可能性較大,以降低成本,這也導致很多年輕女性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選擇在家看護孩子的比率大幅提高。
第三,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目前在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中主要以“五險一金”為主體,而其中有關于女性的生育保險的有關政策從規定到執行都極其不完善,產假只單方面規定了女性休息,而沒有規定“爸爸”們休息的權利,由于用人單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優先,一旦職位出現長時間的空缺,就會對用人單位造成損失,用人單位不會讓職位出現長期空缺,因此,很多女性在休完產假以后就會丟失原來的職位,甚至被迫辭職,被迫暫時或長期退出勞動力市場。所以,在市場配置資源講求效率的原則下,由于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導致很多女性被迫退出勞動力市場。
二、家庭成員對女性的角色期待
家庭成員對女性在家務與育兒上的投入有正面的期望,問到孩子希望家里是誰做飯呢?大部分的答案是媽媽,家庭成員中首先是子女更希望媽媽來做更多的家務,這可能與男性在家務上的不熟練,結果難以使家庭成員滿意有關,或者由于前期育兒階段女性投入遠超男性,導致孩子更依賴母親有關,總之,孩子在潛移默化中已認同媽媽應該做更多的家務。
《朱家故事》是英國繪本作家安東尼.布朗的代表作,也是批判性思維課堂上我們和孩子一起精讀的讀本。 故事里的爸爸媽媽都是上班族, 兩個兒子還在讀書。家中所有家務都是媽媽在做。終于有一天,媽媽留下一張“你們是豬”的字條后離家出走。而沒有媽媽照顧的家也慢慢變成“豬圈”,爸爸和兒子們真的變成了“豬”。這本兒童繪本以批判的方式告訴他的讀者們,也即孩子們,媽媽做家務不是理所應當的。
追溯女性應是家務與育兒的主要承擔者,在狩獵或者農業時代,男性在體力上優于女性,導致男人外出狩獵,女人照料家庭,所謂的“男駐外,女主內” 這樣的分工似乎合理公平。問題是現代社會經濟結構早已發生變化,絕大多數工作崗位,不再只能憑借男性獨有的體能優勢才能完成;而除了懷孕與哺乳, 也不存在什么只有女性才能勝任的家務照料工作。在女性廣泛參與社會工作的同時,男性對家庭工作的參與卻寥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8年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顯示,
中國同時是受傳統倫理影響深刻的國家,在其他家庭成員,尤其是男方父母
對兒媳的期待當然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管理好家庭,教育好孩子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即使是女方的父母,受到以往家庭模式和傳統思想的影響,也認為女兒應該承擔更多的家務與育兒責任,女性是家務與育兒的主要承擔者,這似乎是所有家庭成員對女性的期望。
三、女性自我角色期待的內化過程
女性是應承擔更多地家務與照料孩子的責任,這種期望不僅是社會、家庭成員的期望,有時,女性甚至難以分清是到底自己真心愿意做這些事還是整個的社會系統將這樣的定位隱性內化在女性的教育中與角色定位中,最終成為女性的想法。在女性主義發展到今天,即使在發達的西方國家,如英國,很多女性都甚至認為女權主義是“惡”,很多女性表示:覺得人生幸福的意義在于與愛的人結婚并養育幾個孩子,所以她們覺得女權主義之“惡”,阻礙她們對幸福的追求, 但如波伏娜在《第二性》所言:第二性(即女性)是被定義的,女孩兒從小的成長過程就被社會體系所影響,女孩兒的游戲的“過家家”,為女孩兒們提前模擬如何承擔家務,內化家庭分工,在后來的成長中為進入婚姻做準備開始學習如何做家務,在成為母親后,“母職”,所謂“母愛是女性的天性”,塑造出一種價值觀,女性天生有優勢能成為孩子合格的照料者,或者每位女性都是“好媽媽”,女性以成為好媽媽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但事實上,不論男性、女性在第一次成為父母時,面臨的情況是一樣的,誰都是“第一次當媽媽”,這種“好媽媽”人設逐漸內化,使得女性為沒有成為“好媽媽”而愧疚,在家務承擔和育兒上會主動承擔過多,女性的“好媽媽”的自我角色期待是加劇女性成為家庭照料者責任的重要原因。
結論:
整個社會、家庭成員在對女性是家務與育兒的主要責任者形成外化期待并存在評價,而女性自我的成長過程會內化家庭照料者的角色,在女性已大多在經濟上擺脫對男性依賴的今天,家務與育兒的主要承擔者依然是女性,整個社會的作用機制,家庭成員的外在期待和對女孩們的教育都是應該進行思考和反思的。
參考文獻
[1] 西蒙娜·德 ·波伏娃 《第二性》[M].上海譯出版社,2011.
[2]杜 鳳 蓮.《家庭結構、兒童看護與女性勞動力參與——來自中國非農村的證據》[J].經濟研究,2008,(2).
[3]王超. 浮莉萍.《家庭決策、教育體系與勞動參與率——從勞動力供給的角度看中國的失業問題》[J].生產力研究,2006,(4).
[4]姚先國. 譚嵐.《家庭收入與城鎮家庭已婚婦女勞動參與決策分析》[J].經濟研究,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