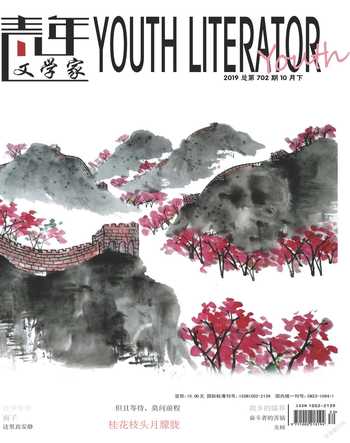從《文心雕龍》看“情”“采”的定義及其關系
摘? 要:“情”與“采”作為《文心雕龍》的一個重要理論范疇具有諸多爭議,劉勰對于“情”的認知更多的是強調其思想純正,與志合二為一,是一種包含了真善美的類似于儒家理想的存在。“采”是一種美學風貌,包含了由“質”到“文”的整個范疇,是文章的外在形式,卻又是自然的產物,“情”正而生“采”,“采”濫則掩“情”。
關鍵詞:《文心雕龍》;情;采;范疇;關系
作者簡介:丁雪,女,山東泰安人,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30-0-02
“情”與“采”作為《文心雕龍》的一個重要理論范疇具有諸多爭議,傳統的觀點認為“情”即是情感,“采”就是文采的華麗。“情采論”類似于“文質論”,屬于文學文本的內容形式層面。現今學者已經看到了此說的局限性,試圖從多角度擴大其內涵,如周振甫先生就將“情”解釋為情理,“采”還包括“精理秀氣”。本篇論文將從整體出發,以《原道》等多篇作為輔助重新審視《情采》篇中“情”、“采”的范疇及其關系。
一、“情”、“采”范疇論
“情”在《文心雕龍》中多次出現,含義略有不同,如《詮賦》篇中說:“原夫登高之旨, 蓋睹物興情。”此處“情”指人自然流露之情,因外物所感發。《徵圣》篇:“則圣人之情,見乎文辭矣。”《情采》篇:“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此處“情”周振甫先生解釋作“情理”,褚春元先生理解為一種審美情感。我們可以將“為情造文”與“為文造情”對比來看,“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郁陶,茍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為情造文”指的是作者“志思蓄憤”即有情志懷憂憤,不得不將情感宣泄出來而進行創作,“為文造情”則是“心非郁陶”,為了創作而虛構情感。通過對比可知“情”就等同于“志”“憤”“郁陶”,即作者郁積于胸的情志,它是在性情的基礎上多加了“理”或“志”等理性成分,突出風雅之思,此“情”為圣人之情,追求儒家的禮樂理想、政治教化。“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仁、義、禮、智、信為五性,五性構成情文,此亦神理之數,先天形成。由此可見,劉勰對于“情”的認知已經主動剔除掉了無意義的惡的一面,而是強調其思想純正,包含了真善美的一種類似于儒家理想的存在,將其稱為神理之數,則是與《原道》篇貫通,試圖從本源的角度為其理論找尋依據。總而言之,“情”無論是作為自然流露之情還是與“理”“志”合為一體的情,對于《文心雕龍》的解讀都是較好理解的,我們將其總稱為情感也并無不妥,但“采”的范疇則是與我們熟知的辭藻華麗具有一定距離。
采的本義是多色的絲織品,《文心雕龍》中“采”也是引申此義而來,我們可以將其稱為“文采”,指文章追求對偶、聲律、辭藻等外在的形式,多指文辭的華麗,《徵圣》篇:“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圣,弗可得已。然則圣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圣人的文章內容雅正,文采華麗,雅與實相對,麗即是華,辭之華者謂之為采。“采”可用“縟”來形容。如《情采》篇:“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為彪炳,縟采名矣。”《序志》篇:“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縟即解釋為文采豐富。鄒奭善于修飾語言,像雕刻龍紋一樣,以雕龍來比喻文章成體,則是著重突出了語言修飾的重要性。但是這其中也存在一個問題,古來文章都是重視語言的外在形式,講求修飾,但皆是文采豐富嗎?像經書這種散行白描文辭怎么能用“采”來形容呢?周振甫先生于是將采的范疇擴大,認為精理秀氣也是采,經書雖沒有豐富的文辭但卻含著精微的道理,有著卓越的才氣,這樣貌似“采”便可以涵括所有文學形式了,但“精理秀氣”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徵圣》篇末的贊言:“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精理為文”指文章含有精深的義理,與“采”無關,而“秀氣成采”指圣人之文,正是由于秀氣,故文成異采,“秀氣”指圣人文章所自帶的靈秀之氣,范疇并不清晰,所以認為“精理秀氣”就是文采也并不準確。
《熔裁》篇緊接著《情采》篇而來,如果說《情采》篇是“以闡明作家創作的真誠為文、以情馭辭為主旨”[1],提出了重“情”又重“采”的情采觀,那么《熔裁》篇則是在創作方法上對于情采觀的具體實踐,所謂“隱括情理,矯揉文采也。”我們可以從具體的創作方法實踐來倒推“采”的范疇。“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熔裁,隱括情理,矯揉文采也。”矯揉意為把木料彎成車輪,也就是說“采”是需要修飾剪裁的。“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好。引而申之,則兩句敷為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核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義顯。”議論精煉,語言簡要,這是屬于極簡略的風格,思想自由奔放,詞句鋪張,是極繁雜的風格,簡練與繁雜適合不同的文章不同的作者,也就是說“采”雖然指文辭的繁縟,但是劉勰也認為“采”也包含“極略之體”,文辭繁縟所以需要刪減,而文章也需要善敷,則從反面說明了文辭的簡練。無論繁復或簡練都是“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采”只是一個“程度詞”。
《通變》篇言:“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于黃世;虞歌《卿云》,則文于唐時;夏歌‘雕墻’,縟于虞代;商周篇什,麗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時,其揆一也。”“志合”也就是“通”,即“序志述時”,指這五個朝代的詩歌在內容思想上的皆是順應時代表達情志之作,“文則”指“變”,即“質”“廣”“文”“縟”“麗”。《考異》云:“《易》有‘天則’,見《乾卦》,《書》有‘王則’,見‘無逸’。則,法也,文則,文之法也。”“文則”也就是創作法則,但這里的“質”“廣”“文”“縟”“麗”更多的屬于在文辭上的區別。我們結合《情采》開篇第一句話“圣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可以推斷,首先這五個時代的文章是圣賢書辭,而圣賢書辭都是具有文采,所以“質”“廣”“文”“縟”“麗”中都能看到“采”影子。周振甫將這幾個詞翻譯為“質樸”、“豐富”、“文采”、“辭采”、“華麗”,我們從中能夠看到一個文辭上的漸進關系,從“質”到“文”皆是屬于“采”的范疇,“麗”為“采”之極。無論是質樸還是華麗,都可以算作“采”,“采”即是文章的一種外在言辭形式,呈現出了一種獨特的美學風貌。《原道》篇中說:“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于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锽: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此處的“文”具有廣泛含義,龍鳳、虎豹、云霞為“形文”,林籟、泉石為“聲文”,有心之器為“情文”。龍鳳用紋理彩色來呈瑞,虎豹用花紋來構成豐姿,云霞構成華彩,草木開花,自然界的一切都有豐富的文彩,“傍及萬品,動植皆文”中的“文”實際上依靠“采”來立論,或者“傍及萬品,動植皆文”可以換成“傍及萬品,動植皆采”。“采”僅僅指一種外在的言辭形式嗎?劉勰在接下來論述稱:“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言之文也,天地之心。”由此可見,“采”雖表外,但與文章的內在范疇本質相同,皆是自然之產物,所以文章以心為出發點,自然有“采”。
二、“情”“采”關系論
由上文的論述可知,“采”是一種美學風貌,包含了由“質”到“文”的整個范疇,是文章的外在形式,卻又是自然的產物,而“情”則是類似儒家理想的存在,與志合一,表文章內在范疇,二者并無直接聯系,屬于文章的兩個不同方面。但正如正文中提到的,劉勰用一個詞“情文”將二者聯系到了一起。“情文”實際上是“情”“文”“采”的融合。“情文,五性是也”“五情發而為辭章”,這里的“文”等同于“采”。“采”的構成方式有三種,五色、五音與五情,五情構成文采,意為情中含采,情感生發而成文章,故圣賢書辭皆具文采。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情”由仁、義、禮、智、信構成,依舊是一種儒家的理想。劉勰在后文接著指出:“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于涇渭之流,按轡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文質”即是“采”的兩種不同程度,劉勰在此明確的說明了“采”附乎“情”,“采”是“情”的產物,只有情志清明雅正,才可以生發文采,駕馭文采。“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情”為“采”之本。“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結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于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翠綸桂餌”與“惡文太章”皆是“采”掩蓋了“情”。“情”正而生“采”,“采”濫則掩“情”,劉勰一方面承認“采”的必要性和適度性,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情”本位的主體性,人為萬物之靈,天地之心,“情”是人最主要的體現,也是產生“采”的根本,歸根到底,《情采》篇的主旨,也是劉勰的理想,則是情采自凝,彬彬君子矣。
注釋:
[1]王少良.《文心雕龍》“情采”范疇釋論.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1期.
參考文獻:
[1]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M].中華書局.2016.6.
[2]詹锳.文心雕龍義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09.
[3]王少良.《文心雕龍》“情采”范疇釋論[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6(01):86-92.
[4]童慶炳.《文心雕龍》“情經辭緯”說[J].江蘇社會科學,1999(06):62-66.
[5]胡言會.郭梅.《文心雕龍·情采》中的“情”“采”關系新解[J].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
[6]劉丹.《文心雕龍》“情采”論之闡釋[D].陜西師范大學,2005.010,26(02):5-8.
[7]左剛.“情采”范疇的確立及演化[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S2):8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