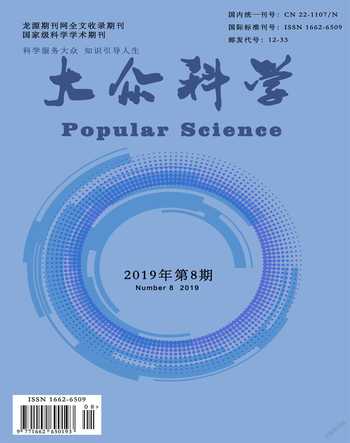秦代的基層社會治理:秦簡所見秦代鄉、里性質與職能考辨
杜瀛
摘 要:秦代基層社會行政系統有縣、鄉、里三級機關。這三級機關除了劃分地域籍貫、編戶齊民的意義之外,還有組織機構的意義。而就組織機構的意義而言,公認的是縣為一級政府機關,但鄉、里兩級機構的性質在目前所見秦簡中并沒有明確的解釋。因此,秦代鄉、里性質一直以來都是學界關注的重點,也有很多學者圍繞此題提出過自己的見解。本文將以秦代簡牘為基本史料,分鄉、里兩個部分分別敘述,就其機構職能、吏員設置和選任和其他細節分別進行分析,并提出鄉、里組織性質之我見。最后簡要勾勒秦代基層行政治理的大致輪廓。
關鍵詞:秦代;鄉;里;基層社會治理
鄉、里及其機構設置、性質、意義一直以來都是學界關注的重點。對于鄉、里的性質,學界目前有以下幾種主要的觀點。前些年在學界的研究中,鄉、里通常被認為性質相同,鄉官和里吏也被統一看待,比如1995年仝晰綱的《秦漢鄉官里吏考》[6]、2006年卜憲群的《秦漢之際鄉里吏員雜考——以里耶秦簡為中心的探討》[9];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鄉、里及其吏員情況應該分別討論,比如1997年張金光的《秦鄉官制度及鄉、亭、里關系》[7]是以鄉官為中心,對鄉、亭、里的性質和關系提出了獨到的觀點。而2007年諸山的《從睡虎地秦簡看秦代鄉里性質》[11]也是將鄉、里兩者分別研究,提出鄉并非獨立的政府機構,同時強調了里籍貫和地域的性質。
而近年來,學界更是傾向于將鄉、里兩者分別看待,比如2017年沈剛的《簡牘所見秦代地方職官選任》[13]一文中通過一些簡牘材料的佐證,認為里吏不屬于國家正式編制體系,因此把里吏從地方職官中排除。這也說明了沈剛先生對里之性質的判斷與鄉不同。但是目前學界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偏重于研究鄉、里的吏治。而在筆者看來,探討鄉、里的性質正是探討吏治的前提,具有很高的價值。因此,本文將對鄉、里的組織性質進行簡要淺顯的分析。
一、鄉、里的地域意義
秦代的基層社會行政系統一般所指的是的是縣及以下的行政機構。因亭是治安機構,所以本文暫不涉及。從基層行政系統而言,在縣以下分為鄉、里兩級,鄉管轄的范圍較里更大。鄉、里作為基層機構,尤其是里,有著劃分籍貫和地區的意義。
有學者指出,里具有籍貫的意義。[11]這種意義就形成于里對居民按照地域進行劃分的功能。根據岳麓簡記載,“1373里自卅戶以上置典、老各一人,不盈卅戶以下,便利令與其旁里共典、老。其不便者,予之典1405 而勿予老。”[5]可見,里的建立以戶數為標準,但是具體戶數不固定,大約為30戶。里之下還有伍,“從云夢秦簡看,有軍功爵位的人和普通農民一樣,都要按照五家為伍的方式編制在一起,區別在于同伍者身份要相同。”[8]
又有學者提出,“里的規劃以居于一定區域,具有一定地緣關系的人戶為標準。里分二類:一為城邑之里。另一類為散戶鄉村之里。這種里,根據村落居民多寡之不一,或一村為一里,或數個自然村合編為一里,其戶數亦不甚整齊劃一。”[7]筆者認為,依照當時的社會條件,這種猜測是很有依據的。而在這種意義之下,里就具有了編戶齊民的最基本單位的意義。里在形式上有垣墻、里門,里門的鑰匙由里典、老保管,這就形成了里的地域實體形態。
而在地域意義上的鄉也就是一定地域內眾里的集合,也就是范圍較里更大的民戶單位。但是除地域意義之外,鄉、里也有著組織機構的意義。
二、鄉的組織性質
鄉是縣之下行政機構。秦中央直接任官到縣一級為止,而鄉則在縣之下。對于鄉的組織性質,筆者認為它不屬于政府機構,而是介乎于政府機構與自治機關之間的一個行政辦事機構。具體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鄉的吏員設置
秦鄉的官吏“職稱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鄉的三老、嗇夫、游徼職責大致與郡的守、尉、監相對應,’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徇禁賊盜’”[3]而正職嗇夫、副職佐的這種名稱則對鄉的性質有所提示。“在秦,嗇夫為各機構之政長,是一個使用極其普遍的職稱名。縣中各機構之長名嗇夫,縣之政長亦或曾名曰嗇夫。秦簡《法律答問》:’命都官曰’長’,縣曰`嗇夫’。’也就是說,都官機構之長曰’長’,縣的下級及縣廷各機構之長曰’嗇夫’。”[7]既然只有縣下級各機構之長曰“嗇夫”,那么假如鄉只是一個與里相同的基層群眾組織,那么鄉之長為何有權稱“嗇夫”呢?因此,一部分學者認定鄉里性質相同的看法恐怕是不可取的。反而,與里相比,從吏員設置來看,鄉的性質可能與縣更相似——只是機構不夠完備,權力不夠大而已。由此推斷,鄉應是在國家的正式行政體系之內。但是,從岳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等篇章中來看,這些簡牘只提到了縣官,而并未提到更下級的部門。[5]這些教育性的文字可見并不是針對高層官吏,而是針對所有官吏的。那么,可以合理猜測,鄉吏被劃歸在了縣官的下屬部門中。也就是說鄉吏屬于縣官吏體系的一部分,而鄉的性質可能與縣廷其他機構類似,屬于縣政府機關的一個部門。
(二)鄉吏員的任職
“都官、郡、縣機關內部的各類官吏,由都官、郡、縣的行政長官自己任命。…縣令對縣內各官府的嗇夫及其它屬吏的任官有批準權。”[2]鄉的長官的任免與縣下屬其他國家機關相同。而在縣之內,“秦鄉嗇夫亦應由縣廷任免,鄉佐則可能由鄉嗇夫提名、除置。”[7]也就是說,鄉吏員的任免總的來說還是由縣決定的。而鄉吏員的任免與與縣下屬其他國家機關相同,也是鄉的性質屬于縣下屬的一個部門的佐證。
(三)鄉的職能
從職能來看,鄉的權力非常之大,所轄事務非常之多。鄉是“掌握民情最為悉備”的“治民最切近之官”,“‘鄉部’號稱’親民之吏’”[7]。對于鄉的職能,有學者作出了如下總結:“一、土地管理權。二、生產監督管理權。三、人事管理權。 四、負責收租、取賦、征兵、派役。五、參與司法。六、參與某些專業事務機構的雙重領導和監督。”[7]可以看到,鄉對民眾生產生活的管理事無巨細,是掌握、統計民眾戶籍狀況、生產情況和其他事務最為完備的機構,又比如民眾有事上請,或官民有事外出時,是能為民眾提供最強大和最切實幫助的機構。
但是有學者考證,基層社會“關涉生產、生活的許多問題,包括大大小小的法律問題,事無巨細,通常直接向所屬縣報告,或以縣為單位進行處理。”[11]也就是說,鄉級機關并沒有獨立處理這些事務的權力和能力。如果鄉有其政府機關,那么這些事務應當不需要上報到縣。
在里耶秦簡J1(16)9簡中有這樣的的內容:“啟陵鄉□敢言之:都鄉守嘉言,諸里…劾等十七戶徙都鄉,皆不移年籍。令曰:移言。今問之,劾等徙...書告都鄉曰:啟陵鄉未有枼(牒),毋以智(知)劾等初產至今年數…□□□謁令都鄉自問劾等年數,敢言之。□□遷陵守丞敦狐告都鄉主:以律令從事。”[4]這條簡文提到,有啟陵鄉諸里十七戶遷居到都鄉,這些人的詳細年齡簿籍需要遷移,因此啟陵鄉請求縣廷命都鄉統計這些人的年齡簿籍以便依令移交和上報。可見,鄉與鄉之間簿籍的轉移不能直接進行,而必須要上報縣,通過縣的命令完成簿籍的轉移。如果鄉是獨立的地方政府,那么管理簿籍的完整權力應當屬于鄉,不可能要通過縣轉移簿籍。從此可見,鄉之職權是不足以作為一個獨立的地方政府的。
(四)鄉的性質之我見
從以上內容可推知,鄉對縣負責,屬于國家行政機關的一部分,但不足以作為一個獨立的地方政府,可能與縣廷其他機構類似,屬于政府機關的一個部門。它與縣、里的性質都是不同的。那么綜上所述,筆者推斷鄉應為一個地方辦事機構。這個辦事機構因為比縣更貼近基層,所以職能廣泛。但是,它并沒有完整的地方行政管理權,應該是一個體制內的基層辦事機構。
三、里的組織性質
里是鄉之下的基層組織,并且在基層管理中有著很強的劃定聚居地域的意義。但是除劃定聚居地域之外,里這個機構在組織機構上的意義更值得探究。筆者認為,里從組織性質上說應當屬于自治組織。具體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里典里老設置:
里之長為里典(或里正),除此之外還有里老。這是里的主要公職人員。
如前所述,縣以下國家機構之長稱“嗇夫”,但里之長只稱“典”(或“正”)。那么,“典”(或“正”)以及“老”又有什么含義呢?“典”與“正”同義,代表著公正;“老”即代表著威望。從字面意思來看,“典”、“正”與“老”是地方有威望、有號召力的人。這樣的身份從名稱來看與國家機構的吏員從資質、職能等等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
并且,有學者提出,“在法律文書中,吏和典分立并列。《睡虎地秦墓竹簡 法律答問》可(何)謂 ‘逋事’,及 ‘乏?(徭)’?律所謂者,當?(徭),吏、典已令之,即亡弗會,為 ‘逋事’,作為法律文書,其行文當十分嚴謹。這其中’吏’、’典’分言,則意味著’里典’并非’吏’,兩者不同。”[13]既然吏、典是兩種身份,那么典、老應當是在國家管理體系之外的身份,而不能說是正式機關的輔助了。
從以上來看,里典、里老的設置與國家機構之長的吏員設置完全不相同,可以說不是同一個體系。這也是從根本性質而言,筆者認為里與鄉完全不同的主要原因。
(二)里典里老的任職:
典、老的任職條件據岳麓簡記載,是“必里相誰(推)”。也就是說要推舉產生。而里典、里老的人選選擇也有其特定的條件:“以其里公卒、士五年長而毋害1291者為典、老,毋長者,令它里年長者為它里典、老。毋以公士及毋敢以丁者,丁者為典、老,貲尉、尉史、士吏主1293者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毋爵者不足,以公士,縣毋命為典、老者,以不更以下,先以下爵。其或復,未當事1235戍,不復而不能自給者,令不更以下無復不復,更為典、老。”[5]可見,為典、老者通常是年長者、無害者,并且一定要是平民。《法律答問》中又有這樣的表述:“可(何)謂“__(率)敖”?“__(率)敖”當里典謂毆(也)。”,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將“率敖”解釋為了“鄉里中豪強有力的人”[1]。總之,里典、里老并不需要是有才能的人,亦不需要為官的辦事能力,只需要在里內有威望,能服人即可。秦的國家機構對里典、里老的人選要求也與對國家機關官吏的要求大不相同,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里屬于基層民眾自治組織。
在任職過程上,里典“必須經過正式的任命程序,由鄉嗇夫提出要求,縣廷審批。在職數和相關任命程序上都有’律令’可據。”[9]里耶秦簡J1(8)157簡載,“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啟陵鄉夫敢言之:成里典、啟陵郵人缺,除士五(伍)成里匄、成。[成]為典,匄為郵人。謁令、尉以從事,敢言之。正月戊寅朔丁酉,遷陵丞昌?(卻)之啟陵;廿七戶已有一典,今有(又)除成為典,何律令?應尉,已除成、匄為啟陵郵人,其以律令。/氣手。/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正月丁酉旦食時,隸妾冉以來,欣發。——壬手”[4]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到,里典和郵人這兩種身份的任命都是由鄉級報告縣級依法審批。而這條案例里的里典任命申請因為其里已有里典,于是縣級審批時沒有批準,而是讓他去做了郵人。既然縣有權根據其里已有里典而做出裁斷,那么可見每里的里典任職情況的登記和匯總也是在縣一級,說明里典的任職到縣一級就可決定,不需要再上報了。而對此,有學者指出,里典的任命與其他官吏也不相同:“從申請者看,其他官吏是縣丞或縣嗇夫等保舉,向上級申請,而里典和郵人則是鄉吏提出申請,由縣丞直接就處理了。”[13]可見里典的任命雖然是正式任命,但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任命還是有所不同的。
總的來說,里最高只需要對縣負責,不需要對中央負責。而在秦制之下,國家機關的官吏是不可能這樣的。這也可以證明,里的性質并非國家行政機關的一部分。
(三)里的職能
里是最低一級的基層行政組織,實際上是一個自治組織。它的職能覆蓋遠不及鄉那樣全面,只是輔助鄉行事。具體而言,里的職能是在所管轄的地域之內,對鄉部分指令的具體承辦。同時作為最基層的自治組織,里所管轄的事務不及鄉那樣全面,但是更加細致,主要分為治安管理和監督生產兩個部分:在治安秩序方面,里的職能有“管理本里居民、協助征役、司法,驅逐賊寇,維持治安,在各種官民事務中做公證人等。”同時,里還承擔著監督生產的職責,比如在睡虎地秦墓竹簡的廄苑律中,有這樣的條文:“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里課之,最者,賜田典日旬;殿,治(笞)卅。”[1]也就是說,里負責耕牛的評選,并有權根據評選結果進行賞罰。
從以上所見里的職能看來,里的性質遠遠不能稱政府機關。它更像是一個自治組織。但里的自治并不是完全不受國家法律約束的自治。固然,因為其靠近基層的性質,上層官吏和皇帝本人很難對里的具體事務進行干涉。但是法律的框架卻一直指導和制約著里的事務。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里典、里老的任免和考核要受到法律制約。雖然里典、里老從嚴格意義而言,并不能算是秦官吏體系中的一員,但是對里典、里老的任免和考核,秦律也不是完全放任不管,而是有相關的規定,這一點在前文已有詳述。
其次,里典、里老必須依照法律履行職責。具體而言,里典、里老需要對其所管轄的區域的治安秩序負責。如果這些地區的治安秩序出現問題,里典、里老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法律答問》中有這樣一條:“賊入甲室,賊傷甲,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審不存,不當論;典、老雖不存,當論。”[1]。也就是說,如果里典、里老所負責的地區有盜竊等治安問題,而典、老沒能在職看守,四鄰也沒在,四鄰不會承擔責任,但典、老會因為失職而被論罪。但《法律答問》又有如下條文:“甲誣乙通一錢黥城旦罪,問甲同居典、老當論不當?不當。”[1]也就是說,如果在里典、里老轄區之內的人員犯罪,但是其罪不屬于里典、里老應當管轄的治安范疇,那么里典、里老無責管轄,也不必承擔責任。這就說明,秦律對里典、里老的具體職責及其履行情況都有嚴格而明確的規定。雖然里典、里老屬于自治機關人員,但秦律還是會干涉典、老的具體職責內容及履行過程,而不是僅僅向地方要求一個治理效果。并且,切實對未能履行職責者予以處罰。
由此可見,里雖然屬于群眾自治機構,但并不是完全放任自流的。雖然秦律對官員的要求與對里典、里老大不相同,但是在秦律中也有專門對里典、里老的要求。因此可見,雖然里的性質從里的職能來看可以被劃為群眾自治組織,但它不是單純的群眾自治組織,而是一個法律框架規范內的,控制力相對強的群眾自治組織。
(四)里的性質之我見:
以上已經證明了,里的性質不同于鄉,也不應被歸為國家行政機關,里的性質應當被劃為基層自治組織。但是這種自治并不是簡單意義上高度自由的自治。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里這個組織雖然處在國家行政體系的邊緣,已經不屬于體制內的機構,但是它還是要受到縣、鄉的管理,對鄉、縣負責。其次,里的自治屬于律法框架之下的自治。法律對地方形成了較為強有力的控制,而這種控制力是與里的自治同時作用于地方社會的。因此,在筆者看來,里屬于法律框架下的;半體制內的基層自治組織。
四、鄉、里性質上之共同特征
雖然前文的論述已經證明,秦代的鄉、里兩機構從根本上說性質并不相同,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兩個機構還是存在一些共同之處。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鄉、里因其貼近基層的特點,都具有一定的自我管理性質。里處于最基層的位置,這種特點也更為明顯。但是,鄉、里都能在某種程度上與民眾一起共同自我管理和運行。
其次,鄉、里都在法律的規范體系之內運行。前面提到,鄉作為一個地方的辦事機構,處在帝國國家機關體系內。而里則處于半體制內的位置,作為一個基層自治組織。但是可以看到,鄉、里同樣都對律法負責,嚴格在律法框架之內運行。而鄉官、里吏只要沒有盡到相關責任,違反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相應的制裁。而國家行政規范也屬于律法規范的一部分。那么,律法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高層機關無法管控的空白,對基層的鄉、里形成了監督和控制。
最后,鄉、里的治理模式都與民眾的日常生產生活緊密結合。可以看到,鄉、里從吏員設置到職能都是緊緊圍繞著民眾的生產生活而進行的。鄉、里對民眾生活之管理事無巨細,在嚴格控制的同時也能夠為民眾的生產、生活起到較強的幫助作用。
那么,從這樣的治理模式之下所脫胎出的,也就是秦統治者所希望形成的基層社會,首先應當是一個高度規范化、秩序化、控制力很強的社會。在鄉、里機關處在律法框架之內對民眾生活高度干預的情況下,民眾也應當是受到法律的嚴格控制的。并且民眾也會擁有比較強的法律意識。這樣的社會自然是處在嚴格的秩序之中。
其次,這種基層社會的治理成本應當較低。這一方面得益于律法的控制力,一方面則歸功于里的自治性質。國家可以在對地方基層社會投入比較小的精力和治理成本的情況下取得比較好的治理效果,并且有助于長時間維系地方社會的穩定。
可以說,在地方行政制度設計上,秦制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優秀經驗。但是以上對于鄉、里治理模式下理想的基層社會形態的敘述只是筆者基于制度設計而進行的一種邏輯推理。在秦王朝實際治理的過程中也許在一些環節出現了偏差,也許其基層治理實踐并不一定遵照這種模式,也許其治理效果并沒有達到上述理想的狀態,這是另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在此暫且不論。
參考資料:
[1]趙進瑜主編:《睡虎地秦墓竹簡》,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1978年11月第1版
[2]栗勁:《秦律通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林劍鳴:《秦漢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王煥林:《里耶秦簡校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5]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壹)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版
[6]仝晰綱:《秦漢鄉官里吏考》,《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6月,第43-47頁
[7]張金光:《秦鄉官制度及鄉、亭、里關系》,《歷史研究》,1997年6月,第22-39頁
[8]臧知非:《秦漢里制與基層社會結構》,《東岳論叢》,2005年6月,第11-19頁
[9]卜憲群:《秦漢之際鄉里吏員雜考——以里耶秦簡為中心的探討》,《南都學壇》,2006年1月,第1-6頁
[10]王愛清:《關于秦漢里與里吏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輯刊》,2006年4月,第134-139頁
[11]諸山:《從睡虎地秦簡看秦代鄉里性質》,《歷史教學》(高校版),2007年4月,第64-66頁
[12]符奎:《秦簡所見里的拆并、吏員設置及相關問題——以<岳麓書院藏秦簡(肆)>為中心》,《安徽史學》,2017年2月,第32-38頁
[13]沈剛:《簡牘所見秦代地方職官選任》,《歷史研究》,2017年4月,第178-1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