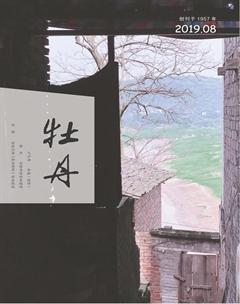立言的不朽
尚志會(huì)
司馬遷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提出了著名的“發(fā)憤著書(shū)”理念,并完成一部偉大的著作《史記》。司馬遷以其獨(dú)特的人格感染著后世文士,“發(fā)憤著書(shū)”理論對(duì)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其主要表現(xiàn)在后世文士追求立言的不朽,以及在中國(guó)文學(xué)的長(zhǎng)河中形成了優(yōu)秀的著述傳統(tǒng)。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是古往今來(lái)無(wú)數(shù)仁人志士的追求。在儒家傳統(tǒng)下,尤其以文士為代表對(duì)“立言”又有著高度的自覺(jué)追求,其表現(xiàn)實(shí)際活動(dòng)上主要為“發(fā)憤著書(shū)”。這一實(shí)踐理論導(dǎo)源于先秦諸子,如孔子對(duì)六經(jīng)的整理等,而在西漢司馬遷時(shí)被提出。司馬遷是中國(guó)偉大的史學(xué)家,其著作《史記》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wú)韻之離騷”。其著述偉大,而遭際坎坷,他所提出的“發(fā)憤著書(shū)”這一理論,具有獨(dú)特的感召力,對(duì)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
一、學(xué)說(shuō)的不朽
何謂“發(fā)憤著書(shū)”說(shuō)?司馬遷在《報(bào)任安書(shū)》中說(shuō):“《詩(shī)》三百篇,大底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lái)者。”《報(bào)任安書(shū)》是司馬遷寫給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在信中以激憤的心情,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發(fā)了為著作《史記》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茍且偷生的痛苦心情。他總結(jié)前人事跡,歷覽史實(shí),得出了經(jīng)典之所以偉大就在于苦難的鍛煉。司馬遷在信中列舉了西伯侯、孔仲尼、屈原、左丘明、孫子、呂不韋、韓非子等先賢前修,他們都以困頓坎坷的遭遇為共同點(diǎn),或身體受損、或精神困頓,但他們最終都以杜鵑啼血的意志完成了驚人的著述,為后世樹(shù)立起一座精神的豐碑。這些人物給予了司馬遷重振精神的動(dòng)力,正如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談自己因李陵之禍遭受刑法后的心情,說(shuō):“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其內(nèi)心苦悶、彷徨,在前修那兒汲取力量,決心著述,求立言不朽。
所謂“發(fā)憤著書(shū)”,即指一個(gè)人因?yàn)槭艿酵獠康拇驌簦鴬^起反抗,以實(shí)現(xiàn)自我的超越。“憤”即指作家心中有所郁結(jié),心理上受到壓迫而不得伸展。借著書(shū)立說(shuō),以發(fā)揮疏通內(nèi)心,從而達(dá)到心理的平衡。應(yīng)當(dāng)指出,“憤”包含了個(gè)人的怨憤情緒,正如屈原著《離騷》,司馬遷在《列傳》中稱:“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同時(shí),“憤”也包含了窮且益堅(jiān)的意志,強(qiáng)調(diào)了作家在逆境中奮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極富昂揚(yáng)的批判精神和戰(zhàn)斗意志去迎接挑戰(zhàn)。司馬遷以“發(fā)憤著書(shū)”理論揭示了歷來(lái)偉大的作品都是作家堅(jiān)持的理想,不畏強(qiáng)暴勇于抗?fàn)幍漠a(chǎn)物。“發(fā)憤著書(shū)”說(shuō)的提出,是中國(guó)文學(xué)史、文論史的一大重要事件。通過(guò)理論的提出與《史記》的寫作,司馬遷完成了古人所講的立言不朽,并達(dá)到了理論與實(shí)踐的統(tǒng)一。
二、經(jīng)典的偉大
一部《史記》,“包括宇宙、總攬?zhí)烊恕⒇炌ü沤瘛保撬抉R遷“立言不朽”“發(fā)憤著書(shū)”的最高詮釋。正如前文所說(shuō),司馬遷因?yàn)槔盍曛湥庥鰧m刑,身陷牢獄。然而,他在痛苦與煎熬中完成了這樣一部著作,給文學(xué)、史學(xué)都留下了寶貴的財(cái)富。
正如魯迅在《漢文學(xué)史綱要》中贊其“史家之絕唱,無(wú)韻之離騷”。《史記》開(kāi)創(chuàng)了紀(jì)傳體史書(shū)的先例,十二本紀(jì)、十表、八書(shū)、三十世家、七十二列傳,司馬遷以其卓越的膽識(shí)、宏大的氣魄,實(shí)現(xiàn)了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創(chuàng)作宗旨。《史記》中所透露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shí)錄精神,是司馬遷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考量,這一精神也為后世著述樹(shù)立了標(biāo)桿。作為史家二十四史之首,《史記》堅(jiān)持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長(zhǎng)于對(duì)宏大場(chǎng)面的敘述,又彰顯了傳奇與現(xiàn)實(shí)的結(jié)合。這些都表現(xiàn)了創(chuàng)作主體在“憤”之后的“奮”,《史記》一書(shū)達(dá)到了史傳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高峰,為后世紀(jì)傳體史學(xué)發(fā)展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從“發(fā)憤著書(shū)”來(lái)看,《史記》給人最為強(qiáng)烈的是不可遏制的“怨憤”之氣及其濃郁的悲劇基調(diào)。魯迅將《史記》與《離騷》并舉,既是從文學(xué)藝術(shù)上給予贊美,又是從創(chuàng)作本質(zhì)上作出的考量。《報(bào)任安書(shū)》云:“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楚懷王聽(tīng)信讒言,疏遠(yuǎn)乃至放逐屈原,于是屈原在無(wú)比沉痛的心境下創(chuàng)作出《離騷》。屈原的“憤”是用文字表達(dá)出來(lái)的,表現(xiàn)了自己見(jiàn)謗的郁結(jié)與無(wú)限的赤誠(chéng)之心。《史記》的創(chuàng)作亦是如此,司馬遷在作品中并沒(méi)有直接流露對(duì)人生的悲絕,但其整體營(yíng)構(gòu)了一個(gè)悲苦的意境,使讀者感受到其心中的強(qiáng)烈之“憤”。《史記》之中,每個(gè)人都有其獨(dú)特的生活環(huán)境,其命運(yùn)與時(shí)代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在《李陵傳》中,太史公寫李陵之事,更帶有自我傷感,從而發(fā)出對(duì)天命的懷疑與命運(yùn)無(wú)常的悲慨。《史記》這部偉大的著作,是“發(fā)憤著書(shū)”的最好展示,同時(shí)在這一精神指導(dǎo)下,文學(xué)史上也形成了浩大的著述傳統(tǒng)。
三、著述的傳統(tǒng)
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上,名家輩出,經(jīng)典燦若星河。大師加經(jīng)典,便等于偉大的傳統(tǒng)。透過(guò)這個(gè)公式,回溯歷史,《詩(shī)經(jīng)》、楚辭、漢賦、唐詩(shī)、宋詞……中國(guó)文學(xué)的繁榮發(fā)展,是炫人眼目的。在眾多經(jīng)典之中,人們以“發(fā)憤著書(shū)”視角來(lái)審視,可以找出一條著述的傳統(tǒng)線索。司馬遷之前,誠(chéng)如《報(bào)任安書(shū)》所敘述。漢降以來(lái),亦有杜甫、韓愈、歐陽(yáng)修、蘇軾、元好問(wèn)、吳敬梓、曹雪芹等可為佐證。下面茲列舉一二。杜甫是唐代最偉大的詩(shī)人之一,與李白并稱“李杜”。歷經(jīng)安史之亂,他懷著無(wú)比深沉的愛(ài)國(guó)之心寫下了“三吏”“三別”和《悲陳陶》《悲青坂》《北征》等膾炙人口的詩(shī)篇,構(gòu)建了作品的“史詩(shī)”特征。“國(guó)家不幸詩(shī)家幸”,杜甫的“發(fā)憤”源自時(shí)代因素,是國(guó)家動(dòng)蕩的無(wú)奈。面對(duì)黑暗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唯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shī)句,方能疏導(dǎo)杜甫心中的滿腔不平。因此,杜甫的風(fēng)格才有了“沉郁頓挫”的特點(diǎn),既有對(duì)社會(huì)的痛訴,又有對(duì)人民的無(wú)限同情。杜甫筆下的“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xiāng)”的人生快詩(shī),同樣與祖國(guó)與人民的命運(yùn)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又如《紅樓夢(mèng)》的創(chuàng)作,“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字字看來(lái)都是血”。《紅樓夢(mèng)》被視為中國(guó)古典小說(shuō)的巔峰,是一部清代社會(huì)的百科全書(shū)。魯迅評(píng)價(jià)《紅樓夢(mèng)》說(shuō):“自有《紅樓夢(mèng)》出來(lái)以后,傳統(tǒng)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紅樓夢(mèng)》的悲劇意蘊(yùn),既有寶黛釵的愛(ài)情悲劇,又有大觀園女兒的青春悲劇,又有賈史王薛四大家族末世回眸的沒(méi)落悲劇,更有時(shí)代傾頹的毀滅悲劇。這一切都是曹雪芹獨(dú)特的人生經(jīng)歷所感受的,也是作者發(fā)憤而為的產(chǎn)物。
四、精神的長(zhǎng)存
“發(fā)憤著書(shū)”理論對(duì)中國(guó)文學(xué)影響深遠(yuǎn),意義重大。
首先,這一理論既有先秦的繼承,又有對(duì)后世的影響。追根溯源,孔子在《論語(yǔ)》中曾談道:“《詩(shī)》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屈原在《惜頌》中提出“發(fā)憤以抒情”,展現(xiàn)了詩(shī)人創(chuàng)作是內(nèi)在情感的強(qiáng)烈抒發(fā),司馬遷“發(fā)憤著書(shū)”對(duì)此進(jìn)行了深入發(fā)展。自司馬遷之后,出現(xiàn)韓愈的“不平則鳴”、歐陽(yáng)修“詩(shī)窮而后工”等一系列學(xué)說(shuō)。韓愈“不平則鳴”在“發(fā)憤”之外更強(qiáng)調(diào)“不平之氣”,是指外在的一切觸動(dòng)對(duì)創(chuàng)作主體所產(chǎn)生的沖撞。“鳴”則是作家內(nèi)心受到強(qiáng)烈的震蕩而進(jìn)行的情感宣泄,即所謂“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歐陽(yáng)修“詩(shī)窮而后工”進(jìn)一步發(fā)展,主要強(qiáng)調(diào)創(chuàng)作主體的經(jīng)歷對(duì)作品的作用,即“窮”與“工”的關(guān)系。
其次,“發(fā)憤著書(shū)”還促進(jìn)“怨刺”傳統(tǒng)的形成,對(duì)后代文學(xué)家、文學(xué)作品具有一定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司馬遷扛起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大旗,從《詩(shī)經(jīng)》到《史記》,再到杜甫等,對(duì)現(xiàn)實(shí)人生的解釋是文學(xué)書(shū)寫上的一條重要路徑,其與浪漫主義共同構(gòu)成中國(guó)文學(xué)的不同美學(xué)范式。
最后,從司馬遷個(gè)人的品格來(lái)看,其憑借超人的意志,堅(jiān)定的毅力,完成《史記》一書(shū),從而身體力行地實(shí)踐了自己的理論主張,以高度的人格品質(zhì)激勵(lì)了后來(lái)的文人士子。
五、結(jié)語(yǔ)
“著書(shū)壽千秋,豈在骨與肌。”作家用氣心血書(shū)寫心中之“憤”,使作品產(chǎn)生強(qiáng)大的感染力,達(dá)到強(qiáng)大的沖擊力,可“懲創(chuàng)人心”。在《典論·論文》中,曹丕指出“蓋文章經(jīng)國(guó)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發(fā)憤著書(shū)”理論是司馬遷對(duì)中國(guó)文論做出的重要貢獻(xiàn),他是中國(guó)歷史長(zhǎng)河里大浪淘沙后的一顆明珠,給中國(guó)文學(xué)增添了昂揚(yáng)、向上、奮發(fā)、抗?fàn)幍慕】狄蜃樱鵀闅v代文學(xué)家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