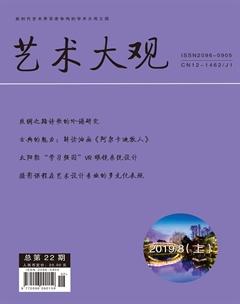精神壓抑中的美學釋放:打破本能與夢境的反烏托邦勵志
鄭潔琳
摘要:《爆裂鼓手》這部影片不同于一般的勵志片充滿了黑色與壓抑的元素,本文將從主角與其導師的角度去分析該片在精神層面上對于美學的認知和突破。
關鍵詞:反勵志片;黑色電影;鏡像認識;電影美學符號
一、傳統勵志片中的本能作用及符號展現
本能一直是人物立于影片的基礎與根本,而對本能的戰勝是從自我到超我的一個過程,這對于勵志類影片的人物通過情節和外界力量的幫助去不斷靠近超我的過程,一直影片基礎塑造的重點,例如《心靈捕手》《墊底辣妹》《死亡詩社》《風雨哈弗路》《模仿游戲》等等一大類的勵志影片,它們都是通過本能去決定人物的動向,已經導師一類的象征符號作為一個良性助力,完成勵志片的完整架構,讓主角達到對于夢想或者目的的完成。而《爆裂鼓手》與傳統勵志片不同的一個點,它運用了黑色電影的元素,在一個極具壓抑的環境下,通過人物精神世界去完成影片。
二、精神壓抑下完成的鏡像認同與反勵志片展現
該片在勵志片的架構下滿足了里面該有的導師與夢想這兩個元素,卻拍攝了一部反勵志反夢想反烏托邦的影片,影片導師的符號成了一個不斷去打壓主角的一個存在,拉康的理論中的自我認同在主角身上,成了一個在夢想與鏡像中迷失掉的關鍵詞,他從未被認同,在勵志在概念上只有一個人的堅持和反抗,影片的冷色調燈光框架構圖無疑不展現著主角的困境和壓抑的環境。夢境與夢想之間的界限就是勵志片把握的關鍵,影片把握這個界限的關鍵就是對于導師這個符號的塑造,他對于主角的否認與打壓,使得影片不斷走向壓抑,而工具式的訓練,只是不斷在摧毀認同這一概念,影片對于生這一本能的摧毀下來展現夢境或夢想強有力的作用,把勝利欲望這一符號不斷地擴大,將攻擊本能放在了生存本能之上,把夢想與恨意的力量結合,形成了人物為了不斷在絕境中完成自我認同的局面,而這也是該反傳統勵志片的精神層面的第一個展現,在本能的界限上把恨放在了愛之上,用精神壓抑去達到自身虐待后的反彈。
影片的鏡像認同,是在于導師和主角之間,他們在攻擊本能下互相傷害,其實隱喻的表象了俄狄浦斯情結中孩子與父親同化的階段,進而去完成替代這一工作,主角就是在替代戰勝的精神壓力下,去完成從鏡像外到走進鏡像內,去成為導師那樣偏執殘忍而又沒有人情味的瘋子,夢想在影片中的概念,更趨近夢境是在被壓抑狀態下本性欲望的追逐與呈現,人物不是去達成夢想,而是在將導師這一鏡像元素成為追逐的目標后被夢境所吞噬,在鏡像審視面前完成蛻變,但是也是將自己變成了那個攻擊的對象,可簡單地理解為對于父權的替代,最后通過自我摧毀新生的過程完成自我認同,這就是影片反勵志反夢想的目的達成的過程,深挖精神層面對于現實人物的作用完成勵志片單人物的巨大蛻變,可以將勵志片的展現不再單一化。
三、壓抑下的美學呈現與美學對于壓抑精神的意義
影片的展示集中于影片的一大元素爵士樂上,爵士樂對于美國文化與歷史有著它超出音樂本身的意義,它風靡與20世紀30年代,是黑了白人文化結合的一個象征符號,它本身有著結合的意義。而對于爵士樂的美學欣賞恰恰和影片壓抑至極的精神狀態形成了對比,在極度壓抑的環境下去完成音樂世界的釋放,給主角形成一種沉浸與追逐的基礎,在情節對比上使得觀眾對于音樂的審美與欣賞可以隨著情節而完成,讓其審美心理集中于角色與音樂上,無限釋放的音樂將欲望與追求自由的主題通過美學進行了一場跌宕起伏的呈現,爵士樂的釋放與爆發恰恰是壓抑的精神下人物所追求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