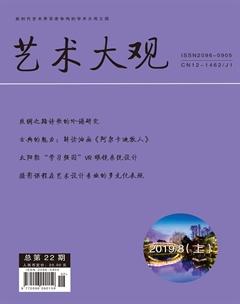從社會歷史批評視角再論茨威格《象棋的故事》
張鈺如
摘要: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創作的中篇小說《象棋的故事》,是其生前發表的最后一部小說,悲痛地講述了一個遭到納粹精神折磨的人的經歷。本文從20世紀30、40年代的歐洲社會歷史入手,以社會歷史批評的視角再論《象棋的故事》,由小說具有的真實性、傾向性、社會效果等進行深入解讀,挖掘文本背后蘊含的社會價值與歷史價值。
關鍵詞:茨威格;《象棋的故事》;社會歷史批評;社會價值;歷史價值
一、《象棋的故事》所具有的歷史真實性
文學離不開社會歷史,本質上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再現,正如杜勃羅留夫提出的:“必須滲透著人民的精神,體驗他們的生活。”真實是作家素材與靈感的來源,通過對文本真實性的挖掘,有助于審美主體更好的深入理解作品。真實性主要包括三大方面:時代背景的真實、人物性格的真實與作品細節的真實。《象棋的故事》就具有明顯的真實性,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小說時代背景真實可靠
《象棋的故事》創作于1941年,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上演。回顧這段歷史,納粹黨奪取德國政權,茨威格遭到納粹驅逐遷居英國,并于1938年加入英國籍,1940年經紐約去巴西。在巴西,茨威格開始寫作《象棋的故事》,開始研究棋譜中著名的棋局,通過時常與妻子對弈,這才有了小說中對棋手們下棋時的狀態及心理深入人心的生動描寫。
茨威格企圖在小說中不經意間還原歷史,“他們的間諜和奸細到處都是,包括陶爾斐斯和舒什尼格的私人府邸在內。”對應了1934年奧地利的總理被法西斯分子槍殺的歷史事實。“在舒什尼格宣布辭職的當天晚上,也就是希特勒進入維也納的前一天,我就已經被黨衛軍逮捕了”則是還原了1938年3月11日舒什尼格下臺,納粹黨徒賽斯·英夸特上臺組閣的歷史事實。與其他虛構的小說世界不同,茨威格將人物置于真實的環境中,地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每個細節都經過仔細的推敲,力圖還原人們的現實世界,使得小說時代背景真實可靠。
(二)小說人物性格真實生動
茨威格用極大的篇幅對小說的兩位主人公進行深刻的心理、動作、語言等描寫,將人物性格刻畫的鮮活生動,如果說《象棋的故事》是一盤棋局,那么B博士和琴多維奇就是棋盤上的白子與黑子,兩人性格的強烈沖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物因此顯得真實且生動。
茨威格從琴多維奇年少時期入手,側面剖析了琴多維奇性格形成的原因及過程,對琴多維奇的描寫符合人物性格的發展邏輯,因此具有真實性。極其貧苦的琴多維奇在喪父后被神父收養,此時的他是一個遲鈍呆滯、脾氣乖僻、犟頭倔腦的鄉村少年,剛剛接觸到了圍棋;在接受了半年的專業訓練之后,有了名氣的琴多維奇開始利用下棋的才能盡可能多地斂財,在逃離貧苦的路上,琴多維奇不擇手段、愚蠢無恥,住最便宜的旅館,隨意出賣肖像權、著作權,金錢與名利的驅使早已讓他放棄了尊嚴。從貧苦的鄉村少年一躍成為世界冠軍,琴多維奇無法擺脫自身階級的局限性,言談舉止沒有教養且利欲熏心,只有名利可以為從小缺乏家庭關愛他帶來安全感,性格的殘缺與扭曲導致了他畸形的言行。
與琴多維奇不同,B博士“他那近乎羞怯的謙遜同職業棋手不可動搖的自負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在未經允許參與棋局之后馬上道歉請求原諒,在甲板上“我”剛走近他,他就立刻客氣地站起來進行自我介紹,雖然是一家古老的名門望族,但絲毫沒有凌駕于他人之上的優越感,他的表達自然而真誠,在陷入癲狂被我點醒之后,他彬彬有禮地道歉并對琴多維奇鞠了一躬,與琴多維奇的傲慢虛偽形成了強烈對比。茨威格追溯到B博士的家族,又通過一系列謙遜的行為上勾畫出一位非常有教養的紳士,即使在發病的之后,也依舊不忘風度。
(三)小說細節真實入微
茨威格細膩的心思使得兩位主人公不再是“扁平人物”,而是被注入了血肉與靈魂,這些都少不了對細節的重視與展現,尤其是對B博士的細節描寫:
在小說的開頭,一艘客輪從紐約開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與作者自己由紐約前往巴西的經歷契合;“我”從侍者那里打聽到B博士是奧地利人,而茨威格本人也是奧地利人;B博士被釋放后,被要求兩周之內離開自己的祖國,辦理了上千個手續,“要弄到軍事機關、警察局的證明,要繳稅,要領護照、出境簽證、健康證明”,仿佛是再現自己被納粹驅趕離開祖國四處流亡時的場景。茨威格通過B博士這樣一個虛構的小說人物,傾吐著自己痛苦掙扎的內心世界,無助的靈魂和漂泊的肉體,都讓茨威格更加懷念昔日和平輝煌的歐洲文明世界。
茨威格在寫B博士被囚禁的部分時,將故事的講述權交還給了B博士,讓他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進行還原,跟隨著B博士的鏡頭,再一次重溫他慘痛的囚禁時期的經歷。他將囚禁比作是酷刑,納粹分子故意拖長候審的時間,使得B博士不得不盯著看大衣上的水珠滴落、數大衣上的紐扣轉移注意力,控制心緒不讓自己崩潰這些真實的細節描寫都表現出了B博士在精神上長期備受煎熬,被隔絕在完全封閉的空間中,被強烈的虛無感包裹著,在這樣可怕的壓力下,一旦有絲毫異于平常的事情發生,就會對薄弱的神經造成強烈的刺激,使人達到幾近癲狂的興奮狀態。還有對空房間里床、桌子、洗臉盆、窗戶、糊墻紙等物品的描寫,在文中反反復復一共出現了八次,B博士被這些東西折磨著卻又無法擺脫,好像整個生命里只剩這些東西了,在接觸圍棋之后,B博士的這種情緒被放大到極致:新鮮—享受—虛無—自我分裂—癲狂,心理描寫作為最直接反映人物內心的描寫方法,比其他的描寫更具有情感表達力度,茨威格一連串心理細節的抓捕對B博士的內心世界進行了深刻、細致的挖掘。
二、《象棋的故事》具有鮮明的傾向性
文學作品應當具有一定的傾向性,它一方面反映在作者對文本中的人物、事件的情感態度,另一方面還反映在作者對現實世界的控訴與不滿、贊美與歌頌。對文本的傾向性進行分析,重視作家的思想傾向,有助于讀者了解作者的創作意圖,進而更好的挖掘本文深層次的意味。
(一)強烈的反戰傾向
茨威格在自傳《昨日的世界》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生長的時代稱為“黃金時代”,反觀小說,B博士在講述自己被囚禁的故事時說:“這個美妙的偉大的時代”,經過戰爭的劫難,“黃金時代”已經逝去,轉而被“美妙的偉大的時代”代替,茨威格贊美時代的文明進步,歌頌像B博士一樣忠誠可靠、熱愛和平的戰士們,諷刺挖苦納粹分子的種種惡行,批判他們對文明的踐踏與摧毀,體現出茨威格強烈的反戰傾向。
一戰期間從事過軍事檔案工作的茨威格曾去過前線,親眼目睹了戰爭的災難,深切了解到前線士兵和百姓們的厭戰情緒,在自傳中說道:“我一定要為反對戰爭而斗爭!我心中已經有了素材……”在《象棋的故事》中茨威格選擇了施暴者琴多維奇和受虐者B博士的形象來作為表達,前者直指希特勒及納粹分子對B博士及無辜的人民的非人折磨,深刻地揭露了法西斯地對西方世界的殘暴和對生命的踐踏,以激起了人們反戰、反法西斯、追求和平的思想;后者則暗示自我的戰爭經歷,B博士被囚禁在大旅館的單間里,納粹分子從精神上腐蝕他,用可怕的、靜止的時間擊垮他,使他陷入無窮無盡的虛無與沉寂之中。這也寫出了茨威格自己的感受,流亡生活壓抑的處境與精神世界的負擔都使作者而感到絕望,他看不到一絲生命的活力,也摸索不到任何出路,所有的希望被完全封鎖起來,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中控訴著納粹對生命無情的毀滅,反對戰爭對人類殘忍的摧殘,渴望著和平的生活可以再次回歸,期盼著昔日的故鄉歐洲能早日重新恢復生機。
(二)控訴種族歧視
家境優渥的茨威格從小便接受良好的教育和上流社會的文藝陶冶,維也納“這座城市的每一個居民都在不知不覺中被培養成為一個超民族主義者、一個世界主義者、一個世界的公民。”早年的成長環境并沒有給他造成什么精神上的壓抑感和屈辱感,他甚至以身為一名維也納的猶太人感到溫暖而自豪,以“世界公民”自居,但在法西斯殘暴地統治之下,如同遭遇災禍的猶太人一般,他成了沒有故國、不受任何保護逃亡者。
丹納在《<英國文學史>序言》中提出“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學說,其中種族是指“天生的和遺傳的那些傾向……而且它們通常更和身體的氣質與結構所含的明顯差別相結合”。納粹認為弱肉強食、優勝劣汰是支配人,特別是種族發展的主要原因,德國民族為保純潔便要避免非純種族分子,也就是猶太人的玷污,希特勒認為猶太人種是危險的、破壞德意志民族的腐蝕劑,應從肉體上進行毀滅,實行種族滅族。
基于以上原因,納粹分子對猶太人開始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身為猶太人的茨威格也無法幸免于難,在希特勒上臺后,茨威格被趕出祖國,1940年去巴西的時候,法西斯勢力越來越猖獗,茨威格目睹了他的“精神故鄉歐洲”的沉淪,納粹一切的所作所為都讓茨威格感到無比的絕望,他痛恨親手毀滅家鄉的敵人,痛恨自己的無能為力,沉重濃厚的感情郁結在作者的心中無法散開,凝結在字字血淚的《象棋的故事》之中,作者反戰、反種族歧視的傾向性更加深沉的在小說中顯示出來。
三、《象棋的故事》所體現的人道主義情懷
優秀的文學作品一定會引起讀者的思想共鳴,引發人們進行思考與反思,社會歷史批評在側重研究文學作品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和作家的思想傾向的同時,也同樣重視文學作品的社會作用。小說通過創造了兩個文學形象即B博士和琴多維奇,對讀者的思想情感造成了強烈的沖擊,更加激起了人們反法西斯、反戰的人道主義思想。
(一)茨威格的人道主義情懷
茨威格在自傳中提及自己的家族,“‘名門世家是指一個猶太家族通過它對另一種文化和盡可能是一種兼容一切的文化的適應。”兼容一切文化的家庭教育在茨威格的心里埋下了一顆人道主義的種子,而他從小生長的城市維也納也成為他人道主義情懷形成的催化劑,這座偉大的城市的真正的魅力就在于把一切具有極大差異的文化熔于一爐,追求人格平等、尊重差異,關注人的價值、尊嚴及權力在茨威格之后的人生經歷及寫作中不斷地體現并且深化,茨威格有意識地深入底層社會,了解底層人民的生活經歷和精神世界。
《象棋的故事》凝結著他此生濃厚的人道主義情懷,文中B博士對自由的強烈渴望最終導致他患上了“精神的急性錯亂”,表現出“象棋癲狂”的后遺癥:在空蕩蕩的房間里走來走去時不自覺地畫出了他從前囚室的大小,咬嘴唇、腳后跟敲打地板等神經質的舉動,茨威格從側面抨擊了戰爭對人民正常生存生活的嚴重影響,他雖然沒有戰斗到戰爭終止的最后一息,但正義感始終支撐著他沒有同法西斯妥協,他在絕命書中盼望人們能看到和平的旭日再次升起升,也將內心僅有的一束希望的曙光注入《象棋的故事》中。
(二)對遭受戰爭苦難的人們的深切同情
小說中慘遭折磨的B博士,被關在一間狹小的房間里,珍貴的時間對于他來說只不過是一把鋒利的劍,每一分每一秒都更加用力地刺進他的靈魂里,使他愈發深陷虛無,無法脫身;起初仿若是救命稻草一般的棋譜,到最后也淪為讓他深陷泥潭的石頭,再次讓他陷入另外一種形式的癲狂,無法被救贖,而造成這一切的就是慘無人道的希特勒及納粹分子,透過茨威格的行行書寫每個讀者都能感同身受,納粹對人的毀滅不僅僅是肉體的折磨與蹂躪,還有令人發指的精神摧殘,讓一個鮮活的生命由內到外的瓦解,茨威格書寫出了對遭受戰爭苦難的人們的深切同情。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茨威格為獲得萊比錫島嶼出版社“長年的公民權”而感到自豪,這強化了他在創作上的責任感,《象棋的故事》創作于1941年,當時的茨威格被痛苦與絕望籠罩著,但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及和平主義者,他勇敢地用手中的武器,大膽揭露了法西斯的殘暴行徑,描繪了受折磨的人民的悲慘困境、戰爭帶來的死亡以及不可逆轉的精神傷痛,也從側面表達出對遭受戰爭人民的同情,這種情緒也感染著小說面前的每個讀者,無論是當時身處戰爭炮火的他們,還是現在擁有和平安全的我們,都可以透過依舊溫熱的文字感同身受。
四、結語
綜上所述,文本通過社會歷史批評的方法,從真實性、傾向性、社會效果三大原則出發對茨威格《象棋的故事》進行解讀,重點對兩位主人公進行了分析,茨威格以尖銳諷刺的筆鋒刻畫了琴多維奇的形象,顯示出對法西斯納粹分子的痛恨與仇視;又展現了B博士的真實經歷與內心最深處的情感體驗,表達出對遭受戰爭苦難的人民的同情,讓讀者更好的理解茨威格對和平主義及人道主義的永恒追求,同時激起人們強烈的反戰、反法西斯的情感,有助于我們把握《象棋的故事》所蘊含的社會價值與歷史價值。
參考文獻:
[1]斯蒂芬·茨威格.斯·茨威格小說選[M].張玉書,等,譯.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2.
[2]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M].舒昌善,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
[3]楊榮.茨威格小說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3.
[4]楊榮.斯·茨威格之死[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04):95-98.
[5]王峰.自我對話的悖論——茨威格《象棋的故事》的一種解析[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6(06)97-102.
[6]周軼.《象棋的故事》的故事——絕望的世界主義者茨威格[J].世界文化,2006(08):12-13.
[7]杜勃羅留科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M].辛未艾,譯.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8]伍蠡甫.西方文論選(下卷)[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