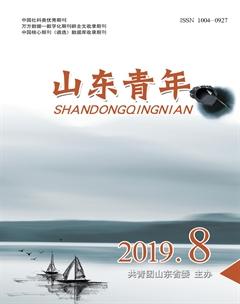豫東南地區中共的發展模式
陳義龍
摘 要:大荒坡暴動,也稱大荒坡起義,是中共于國共分裂后領導發動的諸多武裝暴動中的典型一例。與之前國共合作不同的是,至始至終,中共豫東南特委都發揮了領導和組織作用。雖然這次暴動以失敗收場,但是作為豫東南地區規模較大的武裝暴動,其意義重大,因為大荒坡暴動不僅僅是一場暴動,更是中共在豫東南地區發展模式的集中體現。
關鍵詞:大荒坡暴動;豫東南;中共
一、 大荒坡暴動介紹
大荒坡,位于固始縣西南方,是固始、潢川、商城三縣交界處,平時被人們稱為“三不管”[1],在這荒蕪之地上,前后有三個土樓,分別住著張省山、張重山、張現貴三戶劣紳。這三戶地主為本宗本族,宗族祠堂就設在這里。三人中住在上樓的張省山有錢有勢,在民國初年橫行于此,其子張秋石和其侄張建勛俱為民團中隊長,手下“握有三十多條槍”[1]67,住在下樓的張重山有兩子,分別擔任偽保長和國民黨七十一師參謀[1]70,住在曾小營子的張七爺(張現貴外號),有三子,都在潢川省立第七中學讀書,并且先后加入中共。
一九二七年秋,為落實八七會議關于以河南暴動掩護湖北暴動的決議,中共黨員江夢霞同徐智雨等人返回潢川,做農民工作,宣傳黨的政策①,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調查,江夢霞向潢川縣委提議把潢川、固始、商城三縣交界的大荒坡作為秘密農運中心據點。在建議被采納后,江夢霞花名陳化然,會同化名為余小三的徐智雨,潛居在大荒坡本土黨員張相舟家中,進行長期農民組織工作[1]68。
一九二七年底,受信陽四望山農民暴動的鼓舞,豫東南地區農民的革命熱情逐漸升溫,為此,潢川、固始、商城三縣縣委在大荒坡舉行了聯席會議,會議認為大荒坡的地理位置和丘陵起伏的地形以及上樓的張秋石家握有槍支,便于奪取。據此,會議決定由潢川縣委領導,組織大荒坡農民暴動。張相舟等人根據會議指示,在此地公開宣講共產學說,辦起了紅色夜校。[1]71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共河南省第三次代表大會在開封召開[2],會上根據豫東南的情況,決定“組織光(光山)、潢(潢川)、商(商城)、固(固始)、息(息縣)五縣特委,派汪厚之②為特委書記,改造五縣黨部,極力發動五縣暴動”[3]。同月11號,潢川縣委組織30余人前往張秋石所住的上樓,準備活捉張秋石,但是因為張秋石率民團外出掠奪而撲了個空,只打死了張秋石的奶奶、媽媽、哥哥等七人[1]72。出此原因,汪厚之在特委擴大會議上決定,繼續攻打張秋石,并決定在三月十七日夜舉行暴動。
三月十七日,汪厚之率領一百余人,摸黑向張上樓前行,不料誤了時間,抵達地點時已經臨近天明,加上張秋石提前有了準備,經過一番戰斗,一百余人一部分逃脫,一部分犧牲,另有包括汪厚之在內的十八人被捉,當晚受盡了嚴刑拷打,第二天早上,十八人全部被砍殺在上樓東北角的松山上。至此,大荒坡暴動失敗,潢川的革命組織因此受到重創。③
二、豫東南地區中共的發展模式
自1921年中共成立以來,豫東南地區便有中共成員的活動痕跡,但是中共此時還處于初期的混沌局面。即便是在北伐戰爭的激勵與號召之下,中共在此地快速發展并取得一系列的成果,但這些成果仍然是以國民黨名義為依托,所表現出來的也是一種“寄人籬下”式的發展模式。如中共黨員霍懷仁在息縣建立黨組織的活動,就是受了鄭震宇的委托④,并以籌建國民黨息縣黨部為掩護所秘密開展起來的。[4]因此這個時候的中共活動,因為與國民黨的合作關系,并沒有將自身獨特的發展模式展現得非常明顯。直到大革命失敗之后,特別是八七會議之后,中共在豫東南地區開始獨立摸索發展道路時,才展現出了其獨具特色的發展模式。而這些發展模式,都能從大荒坡暴動中窺見部分。
(一)跨區域聯動
跨區域聯動的發展模式,在中共成立初期就已經初見端倪,比如在武漢中學學習的袁漢銘、董漢儒等人就倡議成立學會來對家鄉商城輸入新文化 [2]14,同樣就學于武漢的光山縣籍中共黨員江夢霞,學成之后立刻返鄉開展革命活動[5]。這些中共的早期成員,都是通過在武漢、北京、上海等地學習或者工作,接觸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由此可以看出,跨區域的聯動是中共早期傳播相關思想和舉措的重要方式,只是此時的跨區域聯動,依舊是以一個人或者一個小團體為單位,且主要的作用對象是知識分子,甚至聯動雙方都是知識分子,這種聯動并不具有廣泛性,只能在小范圍內產生一定的影響。
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共面臨發展困境,各地之間的聯系,無論是方式、道路、還是次數都因為失去了國民黨的支持與掩護而開始受限。同時,大量的中共成員被殺,幸存下來的人大多“渙散或消極不干了”[5]17,在光山,中共黨員和農協干部大量被捕,范功臣等人犧牲[1]297。在商城,黨的聯絡處“商城書社”被摧毀,吳靖宇被捕[2]45,豫東南地區的中共勢力被迫轉入地下,為了能夠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劫后余生的各地區開始了聯系與互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7年黃柏勁與蔣鏡青來商城“參加了商城特支的領導工作” [2]46,在多方努力之下,商城縣委會于同年11月成立⑤。如果將著眼的區域進一步擴大,那么鄂東北與豫東南的聯動則更能說明區域聯動是中共在這段時間內主要發展模式之一。認識到“在豫南歷史很短”[4]135的豫南特委,也認識到自身在此地只能算“稍有根礎”,南五縣也是“情形差不多”[4]135。因此,“缺乏創建根據地的實踐經驗”的豫東南特委,“有向鄂東黨學習的意念” [4]213。鄂東特委對豫東南特委也是幫助至深。通過這些事例不難看出,跨區域聯動使得中共的各地區組織能夠形成一種互補,從而更好的為革命活動調兵遣將,做到“好鋼用在刀刃上”。
在這樣一個區域聯動的大背景之下,大荒坡暴動具體事宜的商定和執行也勢必透露出區域聯動的信息,而這些信息中最重要的有兩點,其一為潢川、固始、商城三縣縣委在大荒坡舉行的聯席會議,其二為汪厚之等外地人直接參加了大荒坡暴動。在這兩點中,三縣縣委的聯席會議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正是這一次會議,使得大荒坡暴動的區域聯動性得到確定,而汪厚之以及外來的三十余人,正是因為區域聯動的助推,義無反顧的參加了大荒坡暴動。通過這兩點的單獨介紹可以得出大荒坡暴動是在區域聯動助推下產生的這一結論,但這種發展模式并不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區域聯動的互補性很強,但是一旦這種互補起到的不是共同增強的作用而是平衡作用時,取長補短的作法很可能會適得其反。
(二)以知識分子為先驅
如前文所述,早期的黨員發展依賴的是各地區之間知識分子的溝通與串聯,這一方面展示了區域聯動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以知識分子為先驅的發展模式。豫東南地區早期的中共成員中,很多都是在外讀書的進步青年,如前文的袁漢民、董漢儒、江夢霞、熊少山、吳靖宇,以及在大荒坡暴動中犧牲的汪厚之等人。正是因為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有機會接觸并有能力理解和運用革命思想,豫東南地區中共黨組織的發展才具有可能性。
但是,僅僅依靠所學知識以及新思想,是很難大規模發展黨員的,想要把黨組織發展壯大,就需要吸納更多的進步人士入黨,但又并非人人都具有進步性,大部分人還是需要通過教育宣傳才能點醒,這就需要一個篩選及教育的過程。這一過程,具體的來說,就是創辦一些文學社或者教學班等文教組織。例如1922年,光山縣的汪厚之從武漢求學回到家鄉后, 與進步知識分子周慕容、黃介人、李世瑾等人組織“光山學界同人研究會”[6]。1924年,熊少山、殷仲環、杜彥武三人返回家鄉光山縣西部的柳林河,籌辦了一座學館,館址就設在熊少山家中,并親自做對聯“沂水春風,須構成兒童樂感。鳶飛魚躍,要喚起稚子動機”[7]。借助這一學館,熊少山得以向學生們傳授國語、算術等新知識,并以此為基礎,在鄉民中宣講革命思想。在商城,1925年,“春季畢業于武昌武漢中學”的袁漢民于同年“秋季定在商城縣小學服務”[8],一邊從事教育工作,一邊創辦一些“讀書會”和書社。同時,商城南部也相繼成立了“筆架山”農校,周維烔、漆德瑋等商城起義的領導者皆畢業于此。[2]22李梯云等人也在商南斑竹園創辦共進小學,并由此成立了斑竹園黨支部[2]22。在潢川,1926年。江夢霞“為了能公開地領導群眾開展斗爭……開辦了‘潢川書店”[5]263,出售《向導》、《中國青年》等進步書刊。
通過以上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以知識分子為先驅是中共發展的又一模式,而在大荒坡暴動中,同樣可以看到知識分子在其中發揮的領頭羊作用,首先,大荒坡三大地主之一的張七爺,其膝下三子都是在潢川讀書時接受了中共的革命思想并入黨,此后兄弟三人積極從事革命,不僅發展周邊的親朋好友,更在張七爺的曾小營子里“公開樹立紅旗,辦起了紅色夜校,宣傳共產學說”[1]71。其次,知識分子直接參與了大荒坡暴動。在大荒坡暴動中被捉和犧牲的人,多為“分發頭、學生裝的識字人”[1]68,不僅如此,也有知識分子負責暴動的幕后工作,暴動中需要的“酒精、炸藥、化學藥品……都由三名學生負責運送” [1]76。而這些學生大部分是在潢川省立第七中學就讀的學生,他們大多是在先驅知識分子的教育之下被點醒,從而參與暴動。最后,是對青年學生進行思想啟發的教師們,如江夢霞、吳麗泉、馮新宇等人,他們是這次暴動的策劃者和智囊團,在省委的安排之下,來到潢川為大荒坡暴動獻言獻策。
綜上所述并結合大荒坡暴動的史實,以知識分子為先驅的發展模式就可以理解為,早期在各地求學的知識分子們,在接受了中共革命思想和馬列主義后,紛紛回鄉籌辦以“學社”“讀書會”為主要形式的教育場所,并以此為基礎,發展具有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及農民加入中共組織。通過一段時間的積累,在有了相當的力量之后,先驅知識分子與新晉知識分子繼續扮演先驅者的角色,進一步指導和部署暴動相關事宜。
(三)借助傳統因素
以知識分子為先驅的早期豫東南地區的中共成員在擔負起宣傳革命的使命之后,便以無上的熱情投身于其中,但是革命事業的開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循循漸進的過程,因此,如何邁出第一步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直接關系到革命事業的基礎,而最直接也是最方便的方法,便是借助傳統因素。這里所說的傳統因素,主要是指以宗族、宗派為主的家族親屬關系以及地緣關系。同時,為了動員起這些關系,所采用的方法很多也具有傳統色彩。
應當重視的是,雖然利用的這些關系和采用的方法并沒有完全落實嚴格且正規的考核篩選準則,但是取得的成果還是相當豐碩的。如光山縣的熊少山、熊全甫等人,將開辦的學館直接設在自己家中,這種作法不僅便捷高效,而且利用了家族的傳統因素,有效的節約了成本。同時,熊少山等人扎根于自己的老家柳林河,首先開始對朝夕相處的親朋好友以及鄰里鄉親的工作,為他們講述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鄉親們聽得入神,并經常留熊少山在家吃飯[1]293,至今還有許多當地的老一輩人清晰得記得熊少山的講演。“串黨跑遍了南五縣,一夜磨破一雙新鞋”的熊少山[7]208,靈活借助傳統因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為光山縣的革命發展奠定了群眾基礎。與熊少山作法類似的還有很多,如江夢霞以看望老友萬紹卿為名,在潢川東北部通過萬紹卿的掩護,進行秘密活動⑥、吳靖宇在商城和商南之間往來奔波,秘密進行革命活動、袁漢民在農村開辦夜校和識字班,從窮苦農民中發展進步人員,白天教書,夜晚找人談心,為革命事業尋找可靠的戰士、周維烔等人利用親屬關系打入縣、區民團,作兵運工作。這些例子都說明,借助傳統因素是豫東南地區中共的又一發展模式。
這一現象同樣發生在大荒坡暴動中,大荒坡暴動能夠發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爭取到了張七爺的兒子們,從而進一步的了解和掌握大荒坡的具體情況,并以此為基礎,繼續利用傳統的親屬關系,對身邊的人進行革命思想改造,成功的借傳統親屬關系和地緣關系,在大荒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暴動開始時,不僅有汪厚之等人率領的師生隊伍,還有“馮家崗、徐家寨、大荒坡附近的農協會員和群眾八十余人”[1]56。而這些本地人的參加,恰恰說明了利用傳統因素的重要性,也同樣是因為中共借助了傳統因素,分化了以宗族和地緣為鏈接紐帶的傳統人際關系,所以在大荒坡暴動失敗之后,“張七爺一家子當天跑了……他的稞都被張秋石霸占了”[1]73,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借助傳統因素的發展模式反過來松動了鄉村中傳統因素的支配地位,具有一定積極作用。
三、小結
豫東南地區的中共通過跨區域聯動、知識分子為先驅、借助傳統因素三個發展模式,開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動。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種發展模式并非毫無關聯,中共在豫東南的實踐也表明,三種發展模式不可能只用其一。這是因為,首先,跨區域聯動需要有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二者,而且,無論是何種內容的聯動,都需要有人參與其中,正是因為這種原因,散落在全國各地求學的知識分子成為了最佳人選,他們互相往來,溝通交流,形成氣候,為跨區域聯動注入了活力。其次,聯動完成之后,知識分子需要尋求進一步擴大革命影響,于是最直接有效的借助傳統因素的發展模式便被廣泛運用。最后,當借助傳統因素發展成熟后,各地的知識分子和新晉骨干為了更大更遠的目標會更進一步地進行跨區域聯動,最終開辟一片又一片的根據地。
[注釋]
①詳情參閱《立志救國 青史留名——江夢霞烈士傳略》,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豐碑:中共信陽黨史資料匯編》第三輯P265。
②原文件中并未寫出特委書記姓名,此為筆者根據其他資料比對后自行添加上去的。
③關于大荒坡暴動的詳情,請參閱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豐碑:中共信陽黨史資料匯編(一)》P54-P81。
④當時鄭震宇的職務是國民黨河南省黨部駐豫南黨務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⑤詳情參閱中共商城縣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商城革命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P46。
⑥萬紹卿是基督教徒,江夢霞因此以傳教的身份住在在潢川東北部上油崗的福音堂內。
[參考文獻]
[1]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豐碑:中共信陽黨史資料匯編(一)[M].1984:55
[2]中共商城縣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商城革命史[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48
[3]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M].1984:127
[4]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豐碑:中共信陽黨史資料匯編(六)[M].1984:265
[5]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豐碑:中共信陽黨史資料匯編(三)[M].1984:250-263
[6]李愛峰.論知識分子在創建豫東南革命根據地中的作用[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3
[7]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豐碑:中共信陽黨史資料匯編(五)[M].1984:206
[8]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上)》[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429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歷史系,安徽 合肥 2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