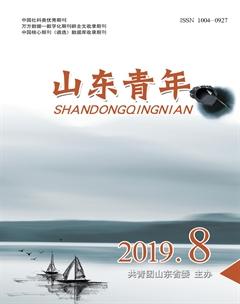中國內地刑法與澳門刑法故意犯罪階段形態之比較研究
洪巍 潘高鵬
摘 要:對中國內地刑法與澳門刑法進行比較研究,有助于推動兩地之間區際刑事司法協助關系的建立和發展。關于故意犯罪階段形態的理論及其相關規定方面,兩地刑法主要在犯罪預備、犯罪未遂之概念及其處罰以及犯罪中止的表現形式等三方面存在差異,可謂“各有千秋,各有優劣”,實有相互取長補短之必要。
關鍵詞:內地刑法;澳門刑法;故意犯罪;犯罪未遂;犯罪中止
澳門回歸后,根據澳門基本法所確立的“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澳門法律一方面成為中國法律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具有依附于國家主權的從屬性;另一方面卻又同中國內地法律分而治之,因而表現出高度的獨立性。刑事法律領域同樣如此。正是基于澳門刑法的這種雙重性質,筆者認為全面、深入地對中國內地刑法與澳門刑法進行比較研究,不僅有助于加強兩地學者的學術交流和溝通,而且也有助于推動兩地之間區際刑事司法協助關系的建立和發展。本文旨在圍繞故意犯罪階段中的形態問題,就兩地刑法的相關理論及立法規定,作一些簡要的純學理性的比較研究,文中所述之觀點僅為個人之學術觀點。
通常來說,一個完整的直接故意犯罪,可以包括犯意的產生、犯罪的預備、犯罪的實行和犯罪的完成這樣一個發展過程。純犯意之產生屬思想范疇,一般不作為故意犯罪過程中階段形態的研究對象。比較中國內地與澳門刑法關于故意犯罪階段形態之理論與立法規定,雖兩地刑法都有關于犯罪預備、犯罪未遂及犯罪中止方面的規定,但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在立法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犯罪預備
所謂犯罪預備,指行為人產生犯意之后,為實施既定的犯罪而著手進行各種必要的準備的情況。對犯罪預備行為是不是要處罰,比較內地與澳門刑法就可以發現其立法觀念差異很大。
(一)犯罪未遂的立法規定
根據內地刑法規定,犯罪預備在實踐中可分為準備工具和制造條件兩種;對于預備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不難發現,立法者在觀念上對犯罪預備是采取了“預備犯可處罰”的立法宗旨。而澳門刑法,對犯罪預備的概念并無規定。根據《澳門刑法典》第2O條規定,犯罪預備行為不予處罰,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所謂“另有規定者”。即指《澳門刑法典》分則及其他單行法律的規定,該立法者對犯罪預備在觀念上采取的是有條件的處罰制度。
(二)兩地刑法比較研究
由上可知,內地刑法與澳門刑法對犯罪預備的規定,主要差別在于立法者對犯罪預備的立法觀念不同。內地刑法是以“原則上處罰”的立法觀念為基礎,而澳門刑法是以“原則上不處罰”的立法觀念為基礎。對此,筆者比較認同澳門刑法的立法觀念。這一立法觀念的長處在于不僅在立法上體現了相對的靈活性,即對某些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的預備行為可另行規定,故不會輕易放縱嚴重犯罪的預備行為,而且有利于體現刑法的必要性原則。因在一般情況下,犯罪預備畢竟未進入犯罪的實行階段,其對社會的危險性是有限的,故原則上無必要以刑罰懲罰之。當然,如果預備行為已觸犯刑法所規定的其他犯罪,則另當別論。此外,從司法實踐觀之,即使在內地,真正處罰單純的犯罪預備的情況也極為少見,故如果在立法上采“原則上處罰”的規定,而實踐中卻以“原則上不處罰” 為慣例,這種立法與實踐的強烈反差無疑會大大削弱法律的權威性(實際上是一種不必要的權威),并且在實踐中也極易產生混亂,引致法律適用的不統一。
二、關于犯罪未遂之概念及其處罰制度
(一)犯罪未遂的概念
犯罪未遂,在理論和立法上主要有兩種觀念和立法模式。一種觀念認為,一旦犯罪進入實行階段以后,只要犯罪未達致既遂狀態的,不管是出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還是意志以內的原因,都構成犯罪未遂。第二種觀念則認為,當犯罪進入實行階段后,凡出于行為人意志以外原因而使犯罪未達致既遂的,才是犯罪未遂;如果是出于行為人意志以內原因而使犯罪未達致既遂的,則構成犯罪中止。內地刑法和澳門刑法關于犯罪未遂概念的規定,作為兩種不同的區分犯罪未遂的觀念,本質上并無差別。
(二)犯罪未遂的處罰制度
如上所述,因不同的犯罪未遂概念會涉及犯罪中止的性質,為表述之方便,故這里的犯罪未遂權以“德國模式”的犯罪未遂概念為標準,包括了障礙未遂和中止未遂。
1.障礙未遂的處罰制度。比較兩地刑法,對障礙未遂的處罰,其區別主要在于處罰的起點及減輕處罰的心證程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典》規定,對于未遂犯(即相當于“障礙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這一規定表明,內地刑法對犯罪未遂采用的是“一概處罰”的立法觀念和原則,而在減輕刑事責任方面,則賦予了司法機關一定的心證權利,即從實際案情考慮,可以減輕刑事責任,也可以不減輕刑事責任。而根據《澳門刑法典》規定,只有當對有關之既遂犯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3年之徒刑時,犯罪未遂方予處罰, 但另有規定者除外。對犯罪未遂,以可科處于既遂犯而經特別減輕之刑罰處罰之。這一規定表明,澳門刑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對犯罪未遂(實際上是指“障礙未遂”)采取了有條件處罰的立法觀念和原則,即相應的既遂犯的法定最高刑超過3年徒刑的(不包括3年徒刑)才處罰;如果處罰則必須減輕刑事責任,法院無心證之權利。
三、關于犯罪中止的表現形式
立法者對犯罪中止(或中止未遂)都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不僅在處罰制度方面規定了不同于一般犯罪未遂(或障礙未遂)的處理原則,而且對犯罪中止的表現形式,也都有明確的規定。比較兩地刑法關于犯罪中止表現形式的規定,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之處。
(一)立法規定
根據中國《刑法典》規定,犯罪中止有兩種犯罪表現形式:即“犯罪的預備中止”和“犯罪的實行中止”。而澳門刑法中犯罪中止首先是作為一種犯罪未遂形態規定的,只能是犯罪實行階段的中止,并不涉及犯罪預備階段的中止。根據《澳門刑法典》規定,在犯罪的實行階段中,犯罪中止形式可以包括四種:第一種是行為人因己意放棄繼續實行犯罪,此中止形式實際上相當于內地刑法所規定的“犯罪的實行中止”或“普通的犯罪中止”。第二種是行為人因己意防止犯罪既遂,此中止形式相當于內地刑法所規定的“特殊的犯罪中止”。
(二)犯罪中止的比較研究
比較兩地刑法關于犯罪中止形式的規定,筆者認為澳門刑法更為具體,也更符合犯罪中止的實際情況。從澳門刑法的規定來看,主要體現了以下兩個特點:澳門立法者充分注意到“危險犯”中止的特殊性。作為“危險犯” 的既遂,理論上都一致認為無須以實害結果的發生為要件,只要法定危險狀態形成,就構成“危險犯”的既遂。因此“危險犯”的中止,通常是發生在犯罪既遂后的中止,故而是一種特殊的犯罪中止形式。毫無疑問,“危險犯”之所以在既遂后仍能構成犯罪中止,取決于“危險犯”本身的犯罪特點,即危險與實害結果的分割性以及實害結果的嚴重性,因而在理論上認同這種既遂犯的中止,有利于鼓勵“危險犯”的行為人中止犯罪,防止或盡可能減小對社會的實際損害。
[參考文獻]
[1]張明楷.未遂犯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陳興良.本體刑法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3]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總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
[4]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
[5]祝銘山.中國刑法教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6]馬克昌.犯罪通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作者單位:天臺縣人民法院,浙江 天臺 31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