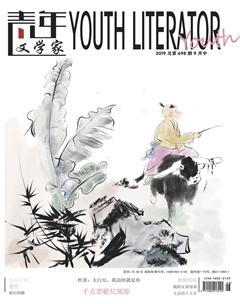文人在壓抑中的特殊寫作
摘? 要:新中國成立后近三十年,是當代中國的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這段時期的文學作品,表面上看似乎只有符合政治話語的“黨的文學”,但事實上,仍是交織著明與暗、官方與民間、公開與“潛在”等力量的隱形角逐與對抗。通過“地下文學”“潛在寫作”這些概念的提出,使得活躍在地下、在當時不能發表的作品受到更多的關注,使其慢慢的浮出 “地表”。因此,“潛在寫作”這個概念為我們想象歷史和還原歷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關鍵詞:潛在寫作;文學性;政治話語
作者簡介:王文慧(1994.7-),女,內蒙古赤峰人,陜西師范大學2017級碩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6-0-03
“十七年文學”以及“文革文學 ”這兩個概念,無論是從宏觀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還是具體到中國當代文學來看,都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歷來第一次文代會被視為當代文學的起點,它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新中國文藝的總方針,確定了文藝發展的方向,要求文藝是為大眾服務的、為工農兵服務的、為政治服務的。長期的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文藝批評標準,迫使文學逐漸走向畸形。但是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有很多文人堅持著自己文化人的底線,開始進行“潛在寫作”。
一、戴著鐐銬跳舞的書寫
十七年文學是普及第一、為政治服務以及文學與政治一體化的文學,而寫作在這個時候就必然成了一種政治任務,這個時候的作家沒有干預文學的自由,只有著歌頌的責任。某種程度上,十七年文學史是文學主體意義上的非文學史,我們在讀那個時代的政治氣息和那個時代人們的某些精神特征的時候,唯獨感受不到的是寫作主體的存在。他們從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已經與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絕緣,這成為作家的寫作方向走向為工農兵服務道路的基石。
追溯延安時期對王實味、丁玲等人的批判,已經顯示出政治權利介入文學發展、促使其一體化的現象。在這種環境下,作家們為了生存,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立場,包括那些國統區的作家,作為“被解放者”,寫作風格也需要向解放區作家的風格轉型,人物形象的刻畫也要樹立高大全的形象,只能從事“遵命文學”的寫作,書寫那個年代所需要的文學。
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從文藝界開展整風,知識分子就成了這場“大革命”中最先受到影響的群體。自1966年開始,各類文藝刊物相繼停刊。1968年,《文匯報》上刊登了文藝創作的三突出原則,“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到了1972年,雖然開始出現少量文藝刊物,但依舊是書寫黨的文學,文學為政治服務、階級斗爭服務在這個時期被推向了極端。《紅旗》雜志作為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時期 的黨刊,上面也刊登了諸如老舍、周立波等人的文學作品,但是從這些作家在這個時期所刊登在《紅旗》上的文學作品的內容上來看,也能看出來文學在為政治權利所用的路上越走越遠的事實。
二、1949-1976年期間“潛在寫作”的構成
陳思和先生將“潛在寫作”定義為當代文學史上的特殊現象。“它由于種種歷史原因,一些作家的作品在寫作時得不到公開發表,‘文革結束后才公開出版發行。”與1949-1976年期間標語口號式的主流作品相比,這些“潛在寫作”作品更具有文學性。在這將近三十年的時間里,“文學服務于政治”的要求使大多數的作家不得不使自己寫出來的作品充滿了政治話語,從而放棄了文學本身應該具有的思想深度。
但是,在文學作品無論在思想內容、藝術水平、話語形式各個方面都相當貧乏的文革時代,有許多被剝奪了正常寫作權利的作家依然保持著對文學的摯愛和創作的熱情,他們寫作了許多在當時客觀環境下不能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他們訴說著自己的無奈和痛苦,不知道何去何從的無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現實的反抗,他們訴說著自己內心最真實的感受。在這種寫作環境下,能夠不忘自己的初心,仍然堅持藝術水準,關注人性光輝的“潛在寫作”的作家,是十分令人尊敬的。在他們的作品中,總會有意無意地 在所生活的環境里收集素材,體現那個時代獨有的特點,因此,“潛在寫作”下的作品,可以讓我們在作品中獲取一些時代的信息,還原當時的歷史環境,體會作家當時的心情和處境。
對于50-70年代的“潛在寫作”,陳思和先生做出了這樣的分類:“第一種是屬于非虛構性的文類,如書信、日記、讀書沒批與札記、思想隨筆等私人性的文字檔案。第二種是屬于自覺的文學創作。”私人性文字檔案如沈從文的《從文家書》中《囈語狂言》這一部分,在受到左翼文學的批判后,沈從文開始陷入精神危機,曾經一度精神失常,在1949年以后就絕筆于文學創作,但他寫的家信卻是文情并茂,細膩地表達了他對時代、生活和文學的理解。書信的私密性可以讓1949年后被邊緣化了的沈從文在相對安全的言說環境中繼續用筆,在那個失去文學主體性的文學資源匱乏的時代,這些書信不能不說是當時最有真情實感的文學作品之一。
自覺性創作,更能表達那個時代的特色。十七年期間,真正有文學性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在當時不能發表的,甚至作家也沒想發表出來的作品。比如當時被剝奪寫作權利的‘七月派和‘中國新詩派詩人的創作、無名氏所創作的多卷長篇小說《無名書等》,如今卻成為了 那個時代最有特色的文學創作。文革時期 ,“潛在寫作”則以手抄本小說和地下詩歌為主。在越少動筆就越安全的文革年代 ,手抄小說和詩歌的廣泛流傳,恰恰體現了那個時代人民對精神世界的渴求。
文革時期“潛在寫作”的小說相對來說比較薄弱,較著名的有畢汝協的《九級浪》、佚名作者寫的《逃亡》、張揚的《第二次握手》、趙振開(即北島)以筆名“艾珊”寫作的《波動》、靳凡《公開的情書》、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等作品。但是詩歌成為“潛在寫作”的重頭戲。在那個時期,人們為了傳播當時的“非主流”文學,想盡各種方法使其在民間流傳。之所以詩歌數量最多,是因為其傳播途徑無非就是手抄傳閱和口耳相傳。詩歌的篇幅相對較短,部分作品還押韻,因此,其他文體更適合背誦和傳抄。所以,詩歌一定程度上更能還原當時的歷史環境,比如,食指的《相信未來》。北島、江河、楊煉等在詩歌領域有所成就的詩人,也都受到了食指的影響。
這些“潛在寫作”作品的存在,為我們探究文革期間的文學現象有重要的價值,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還原當時那個年代的寫作環境與現實面貌,由此為“潛在文學”的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讓我們更加準確的認識這一段歷史。那些作家們面對政治高壓,卻堅持用“地下”寫作的方式吐露心聲,維護文學應有的地位和價值,堅守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底線。
三、1949-1976年期間“潛在寫作”的寫作主體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人們精神生活的極度匱乏是“潛在寫作”下的小說、詩歌、散文等得以廣泛流傳的根本原因。“地上”的文學的假大空,不能滿足人們對文化的需求,整個社會都處于一種精神缺失的境地,因此,有了“潛在寫作”之后,作家盡可能書寫的與文革話語相抗衡的文學,更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期待視野。
在這一時期,有很多被迫中斷或者處于邊緣地位的老一代作家,包括沈從文、陳寅恪、錢鐘書、無名氏等。這些作家活躍在現代文學時期,創作了很多直面黑暗人生的寫作,在現代文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到了當代,迫于政治壓力和知識分子的良心,一部分作家便自覺停止了以往的文學創作。但是無名氏的寫作生涯卻貫穿了現代和當代,他所書寫的《無名書》在文革 時期被查抄,但是慶幸的《無名書》沒有被毀掉,而是在文革 結束后被完璧歸趙,后來才被發表出來。這部命運坎坷的作品,恰恰成為了“潛在寫作”的珍貴資料。
1955年因胡風冤案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們,也是通過“潛在寫作”為文學的文學性貢獻自己的力量,這些作家包括胡風,綠原、曾卓、牛漢、聶紺弩、昌耀、蔡其矯等等。在那個時期,他們遭遇了像隔離、入獄、流放等等苦難,他們都失去了再用自己的名字寫作并發表作品的權利。但是,盡管被剝奪了發言的權利,他們寫作的積極性卻沒被壓制,他們遭受到的苦難反而讓他們更堅強,投身于“潛在寫作”,以這種方式對自身和時代進行反思。這些夾縫中求生存的詩人們,在詩歌的藝術水平上保持了相當的水準。在詩歌的內容被忽略,詩人的寫作主體性缺失的年代,這些詩人使得這個年代的詩歌不單單只有一種聲音。在很多五四以來的詩人已經停下手中的筆的時候,他們還在“地下”堅持著多種形式的詩歌的創作。同時,文革期間 有著一批新生代作家群體,這批年輕詩人群體是“潛在寫作”作家群體中最活躍。除了北京的地下沙龍,白洋淀詩群之外,在上海、貴陽、廈門、成都、內蒙古都活躍著這些年輕的作家們,甚至在一些偏遠的農村也活躍著文學創作的知青。他們在“遵命文學”之外另辟一條新路,顯示出個人的覺醒。
四、“潛在寫作”的研究所遇到的問題
“潛在文學”作品流傳于“地下”,所以它不用服從于政治,不受主流文學的控制。正因如此,這些作品才恰好體現那個年代的人民所處的境遇,才能把人人口中所有筆下所無的情緒訴之于筆端。但是,同樣也是因為這些文學作品存在于“地下”,在研究“潛在寫作”時,各種各樣的問題也就存在了。
在1949-1976年這近三十年間,“潛在寫作”作品得以流傳,都依靠手抄或口耳相傳。因此,在整理這些已經出版的“潛在寫作”的史料的同時,要辨別它的真偽,在創作和發表之間的這一較長的時間差使得這些公開出版的文本,無論其內容,還是發表方式,事實上已不是文革中的那些手抄本,后者的原來面貌已無法重現。或者是有的作品是經過修改的、甚至是文革 之后才定稿的作品。這一類作品則雖然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作者當時的個人情感,但是通過反復修改過的作品卻是作者的情感逐漸變得理性的過程,不能完全還原作者當時的寫作情緒或者所想要披露的問題。所以真偽的辨別就很重要,我們一定要在認定這些“潛在寫作”的作品是真實的材料之后再對它進行合理的研究,從而發揮其應有的文學史料價值。
鑒定材料的真偽的同時,我們還要注意這些作品的創作的時間。由于“潛在寫作”是特殊時代的產物,因此在文革 結束之后才被公布于眾。然而,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由于在那個特殊時期,“文革”前后政治壓力程度不一,作家遭受到的政治災難的程度也并不相同,寫作心境也不可能一樣,所表達的心境也不同。有些作品只有置身于并還原到當時的時代語境中,才能還原它本身的歷史和文學地位,因此一定要判定一個作家的作品創作于哪個時期,才能更好地 還原歷史場景,從而更準確地對作家的心境進行分析。
除了對已經公開發表的作品研究遇到問題以外,還存在著一些未能被發掘出來的“潛在寫作”作品的問題。在1949-1976年這三十年中,到底有多少默默地進行“潛在寫作”的作家,我們不得而知,他們究竟創作了多少作品我們也無法統計。比如穆旦去世后,他的妻子回憶,“在整理遺物時,孩子們找到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密密麻麻的小字,一些是已發表的詩的題目,另外一些可能也是詩的題目,沒有找到詩,也許沒有了,也許寫了又撕了……”
結語:
1949-1976年這近三十年的主流文學,都是服務于政治的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與五四以來的啟蒙文學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在表面看來,“五四”啟蒙文學在進入當代文學一直到文革 結束這期間似乎是消亡了。而對于“潛在寫作”的研究使得這種懷疑不攻自破。這個時期的“潛在文學”仍然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給現代文學和新時期文學牽線搭橋,添補著那個時代文學單一性。“潛在寫作”是研究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史料的挖掘,仍然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易彬.個人寫作、時代語境與編者意愿——匯校視域下的穆旦晚年詩歌研究[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
[2]張詩悅. 作為一種史觀的“關鍵詞”——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文藝爭鳴.2015.
[3]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4]劉志榮著.潛在寫作1949-1976[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5]陳思和著.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6]丁帆,王世城著.十七年文學“人”與“自我”的失落[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