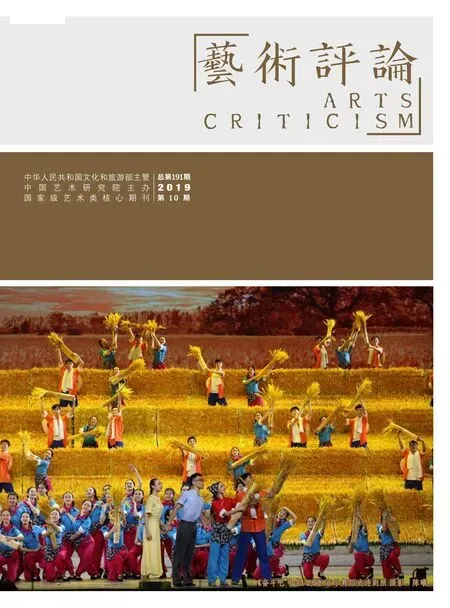電影《媽閣是座城》:被虛焦的澳門城市與歷史文化
[內(nèi)容提要]作為紀(jì)念澳門回歸20周年的獻(xiàn)禮之作,改編自嚴(yán)歌苓小說的李少紅電影《媽閣是座城》遭遇了票房口碑雙失利。影片主要問題表現(xiàn)為:一是澳門的歷史文化、精神特質(zhì)被虛焦模糊、概念化圖解;二是主要人物扁平化,“一女三男”的復(fù)雜兩性情感邏輯混亂;三是淹沒了導(dǎo)演、編劇及原著等創(chuàng)作核心的優(yōu)勢。
2019年的電影《媽閣是座城》改編自嚴(yán)歌苓同名小說,集結(jié)了李少紅、蘆葦在內(nèi)的一流創(chuàng)作團(tuán)隊,公映前早早被視為乘風(fēng)萬里之作,但最終票房、口碑均失利。究其原因,一是澳門的歷史文化、精神特質(zhì)被虛焦模糊、概念化圖解;二是主要人物扁平化,“一女三男”的復(fù)雜兩性情感邏輯混亂;三是淹沒了導(dǎo)演、編劇及原著等創(chuàng)作核心的優(yōu)勢。愛之深責(zé)之切,面對眼光越來越高的中國觀眾群體,電影《媽閣是座城》自然頗有幾分不堪大用的意味。
一、被虛焦的澳門城市與歷史淵源
作為澳門回歸20周年獻(xiàn)禮之作,電影《媽閣是座城》的導(dǎo)演選擇了以小人物的個體經(jīng)歷映射大時代的脈搏。在電影有限的視聽時空中,這樣的選擇無疑是明智的。但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一座城市的變革往往是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那么究竟什么可以代表澳門?如何將20年間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歷程展現(xiàn)得具有可看性?什么樣的小人物才能擔(dān)負(fù)承載起澳門精神?
人們對澳門最廣泛而深刻的記憶來自聞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澳門》:“你可知媽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離開你的襁褓太久了,母親!”這里的“媽港”即“媽閣”。澳門自明朝嘉靖年間被葡萄牙侵占,歷經(jīng)數(shù)百年文化交融,早已形成獨特的文化面貌。時至今日談及澳門,它既是國人心中的歷史隱痛,又是不可忽視的中華文化多元中的重要一支。澳門面積很小,占地不足30平方公里,開車環(huán)島半小時即可飽覽全貌。然而這彈丸之地卻又充滿了傳奇性。這種傳奇性來自“一國兩制”的政治體制、唯一合法的博彩經(jīng)營權(quán)、異域風(fēng)情的美食美景……因此,觀眾熟識、想象、期待的澳門空間元素均在《媽閣是座城》中被保留,影像上煙花絢爛中的大三巴牌坊、高聳入云的旅游塔、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以及媽祖廟的鼎盛香火,稱得上紫陌紅塵的浮華世界。
但不可忽視的是,嚴(yán)歌苓小說《媽閣是座城》并沒有將澳門城市的發(fā)展變遷精心融合進(jìn)人物的情感命運中,更無從談起對澳門回歸20周年的獻(xiàn)禮用意。除卻表象的地標(biāo)建筑,作為城市空間出現(xiàn)在電影中的澳門,它的城市精神要如何理解和定位?為此,編導(dǎo)團(tuán)隊大膽嘗試,將澳門回歸以來的20年變革拆解為時間和空間兩種樣態(tài)進(jìn)行分別展示:從視聽角度而言,澳門的地標(biāo)建筑僅僅作為間歇性提醒觀眾不要忘記“這里是媽閣”的提示牌,成為了孤立無援的空間展現(xiàn);而時間元素被單獨提取出來,字幕一次次提醒澳門回歸20年來的時間推進(jìn)及物理空間不斷變化,填海造陸日新月異。然而,這些時間并沒有與電影的核心矛盾產(chǎn)生密切關(guān)聯(lián),反而成為敘事無力的佐證。通覽全片,我們無從感知澳門這座歷史悠久、包容多元文化的城市品格。恐怕創(chuàng)作團(tuán)隊也并沒有思考清楚這些,因此造成大量的戲劇設(shè)計被觀眾無效接收,“媽閣”變相成為了一塊寫滿“小我情感”冗言的背景板。
從空間呈現(xiàn)而言,作為充滿禁忌的特殊場域,具有一定傳奇性的故事主體空間——賭場,伴隨賭博行業(yè)而生的“疊碼仔”和這個職業(yè)背后的行業(yè)秘密,讓觀眾產(chǎn)生滿滿的好奇心。賭博題材電影在影史上的成功案例并不在少數(shù):就賭場奇觀而言,美國導(dǎo)演馬丁·斯科塞斯最成功的電影《賭城風(fēng)云》將賭城具象化為繁華的虛無空間,主題圍繞貪婪、信任、人性、愛恨、忠誠與背叛等具有原罪性質(zhì)的人性問題,賭城之中眾生百態(tài),賭客們意亂情迷,莊家們趁虛而入,黑色罪惡觸目驚心。就身份奇觀而言,韓國導(dǎo)演崔東勛的電影《老千》講述了賭場內(nèi)的生存法則,連環(huán)布局邏輯嚴(yán)密,主人公在出千和被抓的兩難之間險象環(huán)生,賭桌上下被師父設(shè)計、被朋友設(shè)計、被賭場老板設(shè)計……生死一線帶給觀眾充分的新奇和感官刺激。就行業(yè)文化奇觀而言,王晶的“賭神”系列和“澳門風(fēng)云”系列是成熟樣本,花樣繁多的賭博種類、千變?nèi)f化的賭博規(guī)矩、眼花繚亂的賭術(shù)技巧、萬丈豪情的賭場義氣,交織成為賭場內(nèi)外的生態(tài)奇觀。如果影片將賭場的空間奇觀和“疊碼仔”的身份奇觀及其背后的行業(yè)文化奇觀使用得當(dāng),電影《媽閣是座城》依舊不失為一部佳作。當(dāng)然,作為獻(xiàn)禮之作,賭博題材并不是正向選擇,但就主體意識而言,“博彩風(fēng)云”的確是澳門最鮮明的代表性身份標(biāo)簽。
電影《媽閣是座城》雖然將重頭戲放在賭場中,更以大色塊的金色去裝飾賭場,展現(xiàn)物欲橫流皆為利來的交錯往復(fù),但就視覺效果而言,并沒有跳出港式賭片的紙醉金迷,更多還是將賭場作為簡單的敘事空間。片中對“疊碼仔”的職業(yè)塑造,等同于接待內(nèi)地游客體驗澳門賭場、抽取特殊傭金的導(dǎo)游;“洗碼”“打喜”“分吃”等具有隱秘性質(zhì)的行業(yè)流程被淹沒在臺詞中一筆帶過,“疊碼仔”與賭場老板之間的等級制度語焉不詳,甚至簡化成略顯幼稚的江湖姐妹情,至于“疊碼仔”身份背后的歷史淵源更是只字不提。
但事實上,梅曉鷗從事“疊碼仔”是有特殊原因的,影片進(jìn)行模糊處理直接淹沒了梅曉鷗作為核心人物的特殊個性和文化身份。原著中,嚴(yán)歌苓用寓言化的宿命隱喻,將身為梅家女性的悲劇刻畫進(jìn)了人物的骨血中。曾祖父梅大榕一次次海外求財,卻在歸國途中因賭博而千金散盡、無顏歸鄉(xiāng),直接導(dǎo)致了與他定親的梅吳娘從小姑娘等成老新娘,促使梅吳娘將對丈夫、賭博的怨恨轉(zhuǎn)嫁到了兒子身上,她被異化為“美狄亞”,為報復(fù)丈夫而上演了顛覆倫理的“殺子復(fù)仇”。這種極端復(fù)仇深深影響了梅家后人。血色家族傳說將梅曉鷗推向了另一個悲劇中,如果說梅吳娘是慘烈的“美狄亞”,那么梅曉鷗則是蒙昧的“普賽克”。梅曉鷗繼承了梅吳娘的睿智,卻不能識別自己身邊男人的真面目:身邊的段凱文、盧晉桐、史奇瀾都在得到她之后,暴露出賭徒的丑陋,反而她自身陷入愛情、選擇犧牲、備受傷害。血脈的力量實在強(qiáng)大無比,梅曉鷗即便以女兒之身擺脫了賭博金錢的欲望,但賭的卻是更危險的愛情,也正因這種來自骨血的仇怨,才讓梅曉鷗發(fā)現(xiàn)兒子沾染賭博后上船抓賭,回家將錢倒在浴缸里燒個干凈,她害怕“盧晉桐的基因加上梅大榕的血緣最終勝過了梅吳娘和梅曉鷗,成為支配性遺傳”。令人詫異的是,具有原罪性質(zhì)的宿命設(shè)計和豐厚深沉的家族淵源,竟然在影片中消失殆盡,梅曉鷗直接去除了角色悲劇的毒根,斷絕了她從事“疊碼仔”這一特殊職業(yè)報復(fù)男人的源動力。這樣,梅曉鷗不再是見慣了丑惡、游走在人性灰色地帶的“疊碼仔”,而被簡化成失去魂魄和記憶的殘缺者,根本無法承載時代的變遷。
就文化的移植與再造而言,電影《媽閣是座城》沒有處理好宏觀的城市歷史文化、精神氣質(zhì)與微觀的人物個體宿命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全片呈現(xiàn)出一種異常含混的虛焦?fàn)顟B(tài),僅沉溺于被觀眾早早期待的賭場內(nèi)欲海浮沉和浮生百態(tài)。于媽閣這座城而言,無論是梅曉鷗還是盧晉桐、段凱文、史奇瀾,他們都是外來人、闖入者、賭徒,區(qū)別只在于賭的是金錢還是感情。一群外來人,他們的身心是不統(tǒng)一的,不過是將身體寄居在媽閣,因此媽閣只給了他們一個暫時性的空殼,真實的血肉靈魂無處依托,外來者是注定沒有辦法扎根在媽閣汲取水土精神、文化滋養(yǎng),自然也無法代表這座城市去言說在地性的故事。
二、被模糊的人物個性與情感關(guān)系
《媽閣是座城》展示了賭場里的浮世悲歡。進(jìn)入賭場,所有人都被賦予新的身份,進(jìn)而引發(fā)吊詭的權(quán)力邏輯的大逆轉(zhuǎn):原本高高在上的社會身份(官員、富商、藝術(shù)家)都變作賭桌上一擲千金的賭客,成為被“疊碼仔”和賭場奉為上賓的金主和吸盡血汗的冤大頭;而當(dāng)賭客們背負(fù)巨債離開賭場時,盡管權(quán)柄在握的社會身份又回歸加持,卻依舊難抗“疊碼仔”追債下的左支右絀,卑微低下的“疊碼仔”轉(zhuǎn)瞬之間如噩夢隨行,令人艷羨的家庭、地位、聲望等都成為“疊碼仔”的決勝籌碼。賭客與“疊碼仔”之間就這樣形成了互為制衡的關(guān)系。
梅曉鷗作為女性“疊碼仔”,在靠心狠手辣立足的男權(quán)體系中掙扎求生,女性身份使其另辟蹊徑。梅曉鷗對“疊碼仔”的工作性質(zhì)有充分自覺,正如小說中提到的“海鷗是最臟最賤的東西,吃垃圾,吃爛的臭的剩的,還不如耗子,耗子會偷新鮮東西吃。梅曉鷗從來不避諱一個事實:自己跟鷗鳥一樣,是下三濫喂肥的”“她存心忽略客戶們的姓名,有名有姓的人容易讓她用意氣,動感情”。但凡事皆有例外,茫茫客戶中有三個特例男人擁有了姓名,成為她悲劇的肇始和終結(jié)。當(dāng)“疊碼仔”與賭客相頡頏的關(guān)系被打破,其中蘊(yùn)含的戲劇張力之大、矛盾之復(fù)雜,必然成為觀眾關(guān)注和討論的重點。
就人物塑造而言,“疊碼仔”如此特殊的職業(yè)并沒有給梅曉鷗增光添彩:為了曖昧的情欲,她幫助自己的債主拖延日期,一次又一次被欺騙卻選擇原諒……一個金錢至上的職業(yè)“疊碼仔”,卻被徹底拉到情感的漩渦中,堅定不移地做著散發(fā)圣母光芒卻自身難保的泥菩薩,她輸了房產(chǎn),失了事業(yè),老了容顏,賠了感情,最終連兒子也踏上歧路。作為單身母親,梅曉鷗的根源困境是需要戰(zhàn)戰(zhàn)兢兢尋找“疊碼仔”和寂寞女人之間的微妙平衡,小心翼翼揣摩“本我”和“超我”的邊界,這原本是隱喻性的內(nèi)涵設(shè)計。但電影《媽閣是座城》浪費了這一困境設(shè)計,只讓觀眾看到共情兩性之間的癡纏和決絕,伴隨著賭客與疊碼仔才能發(fā)生的金錢利益和澎湃情欲之間劇烈的交割,扁平化處理人物身份、減少職場的沖鋒陷陣直接導(dǎo)致矛盾核心人物性格弱化,情感狀態(tài)和精神內(nèi)涵蒼白無力。梅曉鷗的情感狀態(tài)從主動進(jìn)攻變成守株待兔,戲路急轉(zhuǎn)直下,成為眾所周知的秦香蓮式“癡情女子負(fù)心漢”,收獲的不過是觀眾的悲憫和同情而已。
回溯嚴(yán)歌苓的作品,女“疊碼仔”的身份之于梅曉鷗,一如旗袍琵琶之于玉墨豆蔻、蛇舞之于孫立坤、天浴之于文秀,原本是最為有力的武器,也是區(qū)別于其他女人的根本。而被殘缺處理的梅曉鷗,失去了這種越禁忌越迷人的性吸引力,即失去了疊碼仔所賦予她的同男人們斡旋取勝的魄力和魅力,不再是可供男人們追逐的勢均力敵的征伐對象。面對舊愛賭棍(盧晉桐)、殺伐果斷的地產(chǎn)大亨(段凱文)、文藝知性的情人(史奇瀾),“賭感情”的梅曉鷗毫無還手之力。
事實上,片中三個男性角色的個性也是被模糊處理的。小說文本中,盧晉桐、段凱文、史奇瀾與梅曉鷗的情感定位是精巧設(shè)計的。盧晉桐是梅曉鷗的“孽”,他身上映射著宿命般的梅曉鷗曾祖父的貪婪和無恥,“盧晉桐為賭一個總統(tǒng)套房的氣,賭掉了手指頭,賭掉了產(chǎn)業(yè),最后賭掉了梅曉鷗和他們的兒子”,直接導(dǎo)致梅曉鷗不得不飄零在澳門,淪落為在賭場討生活的單身母親。前夫以道德綁架享受到“天倫之樂”之后又將感染賭癮的孩子還給梅曉鷗,讓她在事業(yè)和家庭中煎熬。段凱文是梅曉鷗的“劫”,他從窮困中成長起來,曬煎餅讀大學(xué)篳路藍(lán)縷,而他的自負(fù)和驕傲引發(fā)了債臺高筑,更直接導(dǎo)致了梅曉鷗的事業(yè)崩盤。病態(tài)的慕強(qiáng)心理,直接導(dǎo)致了梅曉鷗對段凱文欺騙的真實面目一次次忽略,直至積重難返。而史奇瀾則是梅曉鷗的“緣”,他的藝術(shù)家氣質(zhì)和最終能浪子回頭的魄力,是梅曉鷗生活中唯一的光芒。梅曉鷗對他“愛得想把自己橫陳到這雙手下面,讓它們打磨拋光,拋掉所有其他男人的指紋”,所以兩人同居數(shù)年,梅曉鷗幫他重拾藝術(shù),然而當(dāng)他回歸合法家庭,梅曉鷗的希望又徹底落空。三個男人讓梅曉鷗賭了半輩子青春和感情,卻竹籃打水,如同疊碼一樣,讓梅曉鷗在精神上對愛的憧憬覆水難收,在物質(zhì)上傾家蕩產(chǎn),變得沒有指望。
影片中,導(dǎo)演在努力貼靠小說文本,卻鮮見三個男人性格上的區(qū)別化塑造,除去“富二代”、地產(chǎn)商人、雕塑家的社會身份和結(jié)識梅曉鷗的前后時間順序被交代清楚,三人的面目都被處理為淹沒在物欲和利益誘惑中的賭徒。就藝術(shù)處理手法而言,結(jié)尾處史奇瀾終于被梅曉鷗救贖,成為了“贏了起身就走”的回頭浪子,人性終于戰(zhàn)勝了賭徒的魔性,“最后一賭”成為兩個主人公共同的高光時刻。但這樣的華彩段落實在太少,分量太輕。影片的不足之處還在于,原本在賭場之外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背負(fù)巨債的抉擇更能暴露出人性的不同側(cè)面,梅曉鷗追債的過程也成為雙方博弈的看點。
被統(tǒng)一化的賭徒面孔讓觀眾從根源上懷疑:三個男人和梅曉鷗建立感情的基礎(chǔ)是什么,三個男人之間的區(qū)別是什么?文似看山不喜平,電影更是如此,在有限的時空內(nèi),沒有鮮明的人物個性,精彩的戲劇沖突便無法落實。由于梅曉鷗形象的矮化,連鎖引發(fā)了三個主要男性角色的模糊處理,三個簡單的臉譜化的賭徒形象讓觀眾產(chǎn)生疑問,進(jìn)而從情節(jié)中抽離。電影最終以人物缺少波瀾的平鋪狀態(tài)呈現(xiàn)在銀幕上,自然不能給觀眾帶來滿足感,對影片評價的不理想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面對三個男人,梅曉鷗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小三”。這一身份是被倫理社會所不容的,是男人們上不得臺面的齟齬秘辛,以小三的身份做的又是引人向惡的“疊碼仔”營生,自然會被處于道德制高點的正妻們以家庭為籌碼贏回男人的身心,最終男人們都將梅曉鷗拋諸腦后,這更加深了梅曉鷗的悲劇。
三、被淹沒的創(chuàng)作特質(zhì)與風(fēng)格展現(xiàn)
《媽閣是座城》的電影本身,像極了一群優(yōu)等生皓首窮經(jīng)寫出的不及格試卷,演員表演、劇作技巧、導(dǎo)演風(fēng)格均呈現(xiàn)出一種意外膠著的混沌感。
白百何作為女主角,并沒有將梅曉鷗這個女性角色塑造得立體鮮活。梅曉鷗是內(nèi)心盤根錯節(jié)的大女主形象,她的職場如戰(zhàn)場,她的生活如戲劇,既有血脈的悲劇性,又有生活的悲劇感,是一個具有多層次呈現(xiàn)性格余地的角色。作為演藝低谷的觸底反彈之作,白百何原本應(yīng)該以出塵之姿完成演繹,但或許表演用力過猛,結(jié)果卻是辜負(fù)了人物本身所具有的復(fù)雜性和可塑性,她的表演平庸乏力。這種蒼白的底色或許來源于她對“疊碼仔”這個職業(yè)并沒有深入體驗。例如三亞追債段落,梅曉鷗編造雜志記者的身份對段凱文的正妻余家英伏低做小,套取到段凱文的行蹤,繼而轉(zhuǎn)弱為強(qiáng),扭轉(zhuǎn)局勢趕赴海口逼迫段凱文簽訂還款合同,中間還夾雜著監(jiān)視史奇瀾在越南坑取表弟賭資,與盧晉桐爭奪兒子注意力的博弈……如此復(fù)雜的戲劇人物,要求演員具有極高的表演技巧和極強(qiáng)的控制能力。但白百何選擇一種“撒嬌”式表演,以一個似乎受盡寵愛、吸盡男人目光的“瑪麗蘇”大女主形象,借助不斷示弱的手段,在幾個男人之間左右逢源,將戲劇任務(wù)統(tǒng)一引導(dǎo)向“渣男鑒定”;將個體人物的柔軟和堅強(qiáng)、戲劇張力的收縮和延展、情節(jié)矛盾的爆發(fā)和解決,全盤淹沒在令人不適的錯位感中。
以李少紅以往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來看,例如歸亞蕾對武則天女皇政治身份的掙扎,王姬對繁漪為妻為母的倫理身份的抉擇,周迅對秀禾叔嫂妻妾復(fù)雜關(guān)系的拿捏,成功的女性角色往往依靠一份女性的柔情,以情之一字予人力量。演員通過細(xì)膩的表演表現(xiàn)女人在愛與被愛之間的兩難處境、在家庭與事業(yè)之間的掎角狀態(tài),進(jìn)而得以釋放角色的戲劇力量,給觀眾呈現(xiàn)具體而微的女性悲劇。反之,不走心的表演往往迫使人物的戲劇力量依附于恰切的演員面孔,人物的悲劇往往來自常規(guī)的愛意恩絕,而不是特殊的個體抉擇,這樣的梅曉鷗即便賭得遍體鱗傷、輸?shù)醚緹o歸,也無法給人以共情的體驗。
就編劇而言,電影《媽閣是座城》的問題非常明顯:整部電影偏向于通俗的情節(jié)劇,文戲過多,節(jié)奏緩慢,更兼臺詞贅余,乏味無奇。大量的室內(nèi)戲與現(xiàn)代都市場域比例失衡,空間沒有被有效利用,犧牲了媽閣生態(tài)中的眾生相、人世情,喪失了陌生化審美與觀眾想象的先天優(yōu)勢。為強(qiáng)化情感沖突,一味鉆營兩性關(guān)系因金錢而異化的對立,男性角色成為臉譜化、概念化的賭徒,變相借助流逝的時間機(jī)制,將媽閣的歷史錯位整合成無差別的歷史,將賭場的波詭云譎具象為展示人性假丑惡的舞臺。實際上,影片改編創(chuàng)作難度極大:一則嚴(yán)歌苓的小說文本時間跨度大、空間范圍廣,人物關(guān)系復(fù)雜且各自性格鮮明,人物的取舍、時間的挑選、場景的定奪,凡此種種需要勇氣去刪繁就簡;二則“獻(xiàn)禮”主題之下,如何凸顯龐大宏觀的城市歷史與精神文化,如何尋覓、發(fā)現(xiàn)、建構(gòu)確立回歸20年間澳門文化主體的高度自覺,也都全部仰賴編劇巧思;三則在城市場域中,一面銘寫一個時代的夢想與欲求,一面是反身書寫、形塑個體的羅曼史,更是難上加難。為此,原著作者嚴(yán)歌苓、著名編劇蘆葦親自操刀,他們與曾寫出《功夫》的香港金牌編劇陳文強(qiáng)攜手,但由于個人審美風(fēng)格、話語體系不同,最后的效果是創(chuàng)作體認(rèn)無法統(tǒng)一。總之,《媽閣是座城》經(jīng)過刀砍斧削的改編之后,僅僅成為一個特殊群體(“疊碼仔”)的微型肖像。
就人物塑造而言,李少紅曾說:“我的電視劇不能單獨定義是悲劇,是女性的史詩。”從《雷雨》《大明宮詞》到《橘子紅了》,從《血色清晨》《紅粉》到《生死劫》,李少紅對女性的書寫在業(yè)內(nèi)首屈一指,片中往往沒有絕對的壞人,有的只是時代和社會的隱秘和陣痛。而這些隱痛的縫隙中,卻往往生發(fā)出深刻而綿延的女性的痛苦和悲劇,女性角色往往被賦予既雷霆萬鈞又細(xì)雨潤物的戲劇性。《媽閣是座城》中,李少紅試圖創(chuàng)新,全片幾乎看不到原著中提及的“假如可能,段凱文們,史奇瀾們,盧晉桐們都會像梅曉鷗此刻一樣,躲藏到一抹煞白的面具后面,去賭,去劫,去造孽,甚至去愛。也像她此刻一樣懷有一線無望的希望:揭開的面具下會露出個更好的臉龐,更好的自己”的那份救贖意味,但正因為這份求不得的希冀,《媽閣是座城》才能濃云褪盡,梅曉鷗人生的悲劇才更悲哀。
就影像風(fēng)格而言,《媽閣是座城》延續(xù)了李少紅風(fēng)格化的大色塊美學(xué),例如以富麗的金色為主色調(diào)的賭場裝飾,區(qū)別于以白色為主色調(diào)的梅曉鷗住家環(huán)境,隔離開“疊碼仔”梅曉鷗的雙重身份。片中囚禁史奇瀾的綠色公寓,整體空間沉靜素樸,這里是梅曉鷗在媽閣的第一處落腳點,也是最后一道心靈防線,而這座隱喻女性堡壘的空間關(guān)進(jìn)了史奇瀾這樣的男人,無異于將梅曉鷗身心俱疲后的唯一一塊綠洲袒露給史奇瀾。由于媽閣本身存在現(xiàn)代城市的文化氛圍和內(nèi)在律動,都市特色應(yīng)是鏡頭語言表現(xiàn)的重點。媽閣作為城市并不具有庭院深深的曲徑通幽,也沒有風(fēng)月無邊的花好月圓,反而容納了相當(dāng)體量的現(xiàn)代城市景觀:煙火、霓虹、教堂、廟宇、海港、山丘、立交橋、小巷弄……換言之,由于視覺上的龐雜難辨,媽閣是一塊底色并不單純的奇特畫布。而李少紅堅持的以穩(wěn)拙優(yōu)雅見長的古典大色塊,與雄渾喧闐的現(xiàn)代都市遭遇,勢必如冰遇火被萬千燈火吞沒,其結(jié)果就是片中精心設(shè)計的幾處大色塊場景被凸顯出來,成為一種不合時宜的敗筆。
綜上而言,電影《媽閣是座城》是一部在無序狀態(tài)下唐突完成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媽閣作為城市的精神與歷史被虛焦處理,男女主人公的個性與糾葛被模糊損耗,暴露了李少紅對于展現(xiàn)小人物困境的乏力,影片整體呈現(xiàn)出促狹逼仄的小格局感。然而,《媽閣是座城》對中國電影中的處理文化和歷史的關(guān)系、銜接個體人物與宏觀時代地域的氣質(zhì)、改編移植文學(xué)文本、書寫當(dāng)代女性形象與價值觀等核心問題,具有探討和反思的價值。
注釋:
[1]美狄亞是科爾喀斯國王埃厄忒斯之女、地獄女神的祭司,守護(hù)著神圣的金羊毛。因愛上了前來盜取金羊毛的伊阿宋而追隨至希臘定居在科任托斯,育有二子。十余年后,出于私利的考慮,伊阿宋決定迎娶科任托斯王的女兒為妻。悲痛之下,美狄亞手刃兩個兒子對伊阿宋進(jìn)行報復(fù)。
[2]羅馬著名的神話人物,愛神丘比特的妻子。因為兩人只在夜里相會,普賽克無法忍受不知道丈夫真實身份和外表的焦慮,而點燃蠟燭偷看睡夢中的丘比特。一睹面容的同時,燈油滑落嚴(yán)重?zé)齻怂瘔糁械那鸨忍氐谋郯颉G鸨忍伢@醒后憤怒傷心地飛走了。
[3]“媽閣”即澳門。為與影片片名一致,以下論述將沿用片名中的“媽閣”這一稱呼指代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