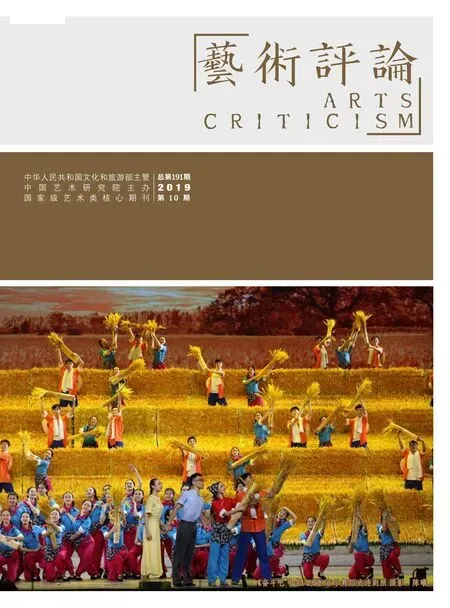《上海堡壘》:一部“偽高概念”電影的內(nèi)部塌陷
[內(nèi)容提要]《上海堡壘》體現(xiàn)出典型的“高概念”電影特征,但又違背了“高概念”電影普遍收獲“高回報(bào)”的邏輯規(guī)律。本文提出《上海堡壘》在世界觀建構(gòu)與“在地化”改造、主要角色性格塑造與次要角色形象展現(xiàn)、電影節(jié)奏的把握與情節(jié)推進(jìn)三方面存在相應(yīng)的問(wèn)題,使其未能形成應(yīng)有的突破,只能被算作一部具備“高概念”外部特征的“偽高概念”電影。
作為2019年暑期檔引發(fā)了巨大爭(zhēng)議的國(guó)產(chǎn)科幻影片,《上海堡壘》體現(xiàn)出典型的“高概念”電影特征。“高概念”(High Concept)這一術(shù)語(yǔ)最早來(lái)源于美國(guó)廣播電視網(wǎng)(ABC)節(jié)目總監(jiān)巴里·迪勒(Barry Diller),其以“一句話征集節(jié)目”的點(diǎn)子聞名業(yè)界。其后,“高概念”通過(guò)電視電影的拍攝被逐步引入主流電影行業(yè),成為一種特殊的電影模式。根據(jù)美國(guó)電影學(xué)者賈斯汀·懷亞特的總結(jié),“高概念”電影具有以下三點(diǎn)鮮明的特征:“其一,由著名導(dǎo)演執(zhí)導(dǎo)或大牌明星主演,甚至兩者兼?zhèn)洌黄涠适虑楣?jié)相對(duì)簡(jiǎn)單,可以用一句話簡(jiǎn)明概括;其三,電影可以與之前流行的文藝作品形成一種‘互文’的關(guān)系,電影有原作為基礎(chǔ),而且那些原作已有了相當(dāng)廣泛或者比較穩(wěn)固的受眾,如名著或暢銷小說(shuō)改編的電影、漫畫改編的電影、續(xù)集電影等。”
《上海堡壘》正是一部由著名導(dǎo)演滕華濤執(zhí)導(dǎo)、知名作家江南同名小說(shuō)改編的電影,影片匯集了鹿晗、舒淇等演員擔(dān)綱主演,具備高額的資金投入和豐富的高科技科幻元素;其故事內(nèi)核簡(jiǎn)潔而具有典型性,可以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上海堡壘的戰(zhàn)士通過(guò)犧牲自己保衛(wèi)地球,最終戰(zhàn)勝了強(qiáng)大的外星入侵者”;此外,《上海堡壘》與諸多好萊塢“高概念”大片(《獨(dú)立日》《世界大戰(zhàn)》《2012》《異形》《安德的游戲》)以及知名電子游戲(《星際爭(zhēng)霸》《紅色警戒》《使命召喚》)等形成了較強(qiáng)的互文關(guān)系。以上可見(jiàn),《上海堡壘》幾乎覆蓋了“高概念”電影所應(yīng)具備的一切外部特征。然而,其最終慘淡的電影票房和近乎一邊倒的負(fù)面評(píng)價(jià),卻又違背了“高概念”電影普遍收獲“高回報(bào)”的邏輯規(guī)律。
所謂“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本文通過(guò)分析得出結(jié)論——《上海堡壘》實(shí)際只能算作一部具備“高概念”外部特征的“偽高概念”電影,其在世界觀建構(gòu)與“在地化”改造、主要角色性格塑造與次要角色形象展現(xiàn)、電影節(jié)奏的把握與情節(jié)推進(jìn)等方面存在諸多問(wèn)題,使其實(shí)難支撐高概念大片本身應(yīng)具有的成熟架構(gòu),最終導(dǎo)致“堡壘”內(nèi)部的塌陷與瓦解。
一、草率的“世界觀”建構(gòu)與流俗的“在地化”改造
豐滿而扎實(shí)的世界觀建構(gòu),往往是科幻電影得以“扎根開(kāi)花”所依托的重要“土壤”。《上海堡壘》以上海這一知名城市作為故事鋪開(kāi)的主要戰(zhàn)場(chǎng),通過(guò)對(duì)未來(lái)世界中高聳矗立的東方明珠、震旦大廈等地標(biāo)建筑的展現(xiàn),第一時(shí)間拉近了觀眾與故事發(fā)生背景間的距離,透露出充分考慮中國(guó)觀眾接受度的智慧與巧妙。但是縱觀全片后發(fā)現(xiàn),相比于《阿凡達(dá)》“十四年磨一劍”對(duì)于納美星球龐大而精密的世界觀建構(gòu),《流浪地球》充滿“黃金時(shí)代科幻氣質(zhì)”的哲學(xué)思辨和對(duì)于未來(lái)上海、北京等城市地下“賽博朋克”般市井生活形態(tài)的想象,以及《指環(huán)王》《霍比特人》依托中土世界闡發(fā)的宏大敘事與天馬行空的文化重塑而言,《上海堡壘》主創(chuàng)明顯缺少對(duì)未來(lái)世界于“運(yùn)行方式”層面的深入思考和邏輯推演,這導(dǎo)致影片所描繪的未來(lái)世界和其中的運(yùn)轉(zhuǎn)規(guī)則,存在較大瑕疵和邏輯困局。這種缺陷僅從片中人類指揮部對(duì)于重要能源“仙藤”隨意而不負(fù)責(zé)任的處置方式,以及人類抵御外星入侵者時(shí)“拍腦門”般的“無(wú)腦”戰(zhàn)略決定就可見(jiàn)一斑。科幻電影對(duì)于未來(lái)世界觀的建構(gòu)不僅應(yīng)是一種大膽而超前的展望,更應(yīng)是符合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的合理預(yù)測(cè)。但《上海堡壘》影片并未形成支撐未來(lái)世界合理運(yùn)轉(zhuǎn)的邏輯自洽,其構(gòu)建的諸多場(chǎng)景和設(shè)計(jì)的若干情節(jié)都難以經(jīng)受住深入推敲。
由于整體世界觀結(jié)構(gòu)上的草率與盲目,《上海堡壘》會(huì)讓觀眾產(chǎn)生諸多邏輯結(jié)構(gòu)層面的懷疑。例如,影片開(kāi)宗明義地提到能量“仙藤”具備強(qiáng)大的可復(fù)制性,已成為人類用以替代石油的優(yōu)質(zhì)資源,完全可以承擔(dān)上海大炮乃至整個(gè)上海地區(qū)的能量來(lái)源;但影片進(jìn)行到中段,卻突然告知上海大炮的發(fā)射會(huì)耗盡所有的“仙藤”能源,致使“仙藤”不足以再支撐上海堡壘的防御耗能。所謂“兵馬未動(dòng),糧草先行”,如果不能保證基本的防御,那么建造出“上海大炮”這樣“任性”的殺傷性武器,意義到底何在?豈不是丟了西瓜,撿起芝麻?而且,“仙藤”如此不堪使用,外星人拼了命來(lái)?yè)寠Z它的意義何在?又如,影片前半段中,上海大炮命中敵方“德?tīng)査概灐保瑓s被證實(shí)效果不佳;而當(dāng)母艦卷土重來(lái)時(shí),指揮部為何還讓上海大炮去孤注一擲地再次射擊?既然已證明效果不佳,同時(shí)發(fā)射將導(dǎo)致上海堡壘本身的防御系統(tǒng)停擺,那為何還要如此賭博式地“玩火自焚”?再如,指揮部很清楚下令上海大炮“再來(lái)一發(fā)”的決定將立刻導(dǎo)致上海整體“陸沉”,外灘、靜安寺、武康大樓等珍貴的地標(biāo)建筑和文化古跡將立刻毀于一旦,同時(shí)這一命令純粹源于楊建南司令官一意孤行的逞強(qiáng)行為,而非“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的無(wú)奈之舉,那么為何還要下達(dá)這樣“殺敵三千,自損一萬(wàn)”的錯(cuò)誤決定?凡此種種缺乏邏輯性的情節(jié)安排,會(huì)讓觀眾感到片中人物如同在打電子游戲一般隨意而毫無(wú)嚴(yán)肅性,感受不到任何地球即將毀滅的真實(shí)壓迫感和大敵當(dāng)前的應(yīng)激緊張感。以上邏輯漏洞會(huì)導(dǎo)致受眾頻繁被動(dòng)“出戲”,從而減弱對(duì)影片的期待。
世界觀建構(gòu)上的不扎實(shí)還體現(xiàn)于影片在場(chǎng)景設(shè)計(jì)上的粗糙和應(yīng)付。有研究者指出,“當(dāng)電影制作進(jìn)入‘高概念’運(yùn)作之后,電影人自覺(jué)或不自覺(jué)地放棄了由衷而發(fā)的人文情懷,愈來(lái)愈淡化甚至割舍文學(xué)的情思,單純地追求‘鏡像化’,追求技術(shù)上的絢麗奪目,刻意營(yíng)造鏡像奇觀”。但僅從這方面來(lái)看,《上海堡壘》也沒(méi)有通過(guò)自身的想象力展現(xiàn)出特別突出的奇觀化“視覺(jué)溢出”效果。影片費(fèi)盡心力構(gòu)思的外星大本營(yíng)“德?tīng)査概灐保允贾两K只能看到一個(gè)邊緣部分,雖然影片對(duì)于外星士兵“捕食者”的形象塑造比較下功夫,并且由“捕食者軍團(tuán)”的打造形成了一種密集強(qiáng)大的“大兵壓境”氣勢(shì),但對(duì)于母艦形象的整體構(gòu)思既不具體,也不夠隱晦,給人以虎頭蛇尾的敷衍感,沒(méi)有形成像《獨(dú)立日》那樣由巨型外星母艦真正壓迫籠罩地球的震撼場(chǎng)面。我方軍隊(duì)設(shè)計(jì)方面則更顯潦草——與現(xiàn)代戰(zhàn)爭(zhēng)服裝毫無(wú)二致的軍服和軍帽,與當(dāng)今標(biāo)準(zhǔn)幾無(wú)差別的手槍和沖鋒槍,普通的迷彩坦克和裝甲車,簡(jiǎn)單而毫無(wú)科技感的上海堡壘地下指揮中心,以及殘破如同廢棄工廠的上海堡壘地面廠房。這些毫無(wú)“未來(lái)感”的戰(zhàn)備物資和軍備場(chǎng)所,在唯一充滿科技感的上海大炮面前更顯寒酸,同時(shí)反倒令重金打造的上海大炮顯得更加鶴立雞群,味同雞肋,格格不入。《上海堡壘》將重點(diǎn)精力放在提升外星“捕食者”的特效感和科技感之余,似乎沒(méi)有再花什么精力去思考影片預(yù)設(shè)時(shí)間——2035年的人類可能進(jìn)步的哪怕一點(diǎn)點(diǎn)的科技感,而是完全以缺乏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態(tài)度去照搬當(dāng)今人類現(xiàn)有的生存形態(tài)和模式。應(yīng)該說(shuō),《上海堡壘》的主創(chuàng)沒(méi)有將自己置于未來(lái)世界的可能性中,沒(méi)有仔細(xì)揣摩未來(lái)人類自身的存在和定位,更談不到真正站在未來(lái)去“回顧”現(xiàn)在的“歷史”。這樣缺乏代入感的創(chuàng)作決定了影片很難讓觀眾感同身受,造成受眾期待視野的不斷衰減,最終導(dǎo)致了觀眾的無(wú)限失望。
正如有學(xué)者指出的,“好萊塢式的中國(guó)高概念電影秉承了好萊塢高概念電影的技術(shù)主義風(fēng)格,簡(jiǎn)單明了的善惡對(duì)立,華麗震撼的視聽(tīng)奇觀,酷炫逼真的動(dòng)作打斗,穿插普適動(dòng)人的人性橋段在敘事中”,但“畫虎畫皮難畫骨”,這種模仿和對(duì)標(biāo)如若沒(méi)有戳到核心精髓,則容易被逼入“學(xué)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藩籬。《上海堡壘》在很大程度上就遇到了這樣的尷尬,尤其是影片的“在地化”改造也僅僅是流于形式,沒(méi)有深耕和挖掘中國(guó)本土化的特征和受眾心理,因此顯得不倫不類。
例如,“吃飯”的戲份設(shè)置歷來(lái)是電影中讓人物卸下戒備、敞開(kāi)心扉、真情流露的極好手段,《飲食男女》《深夜食堂》都是通過(guò)餐桌上人與人之間的坦誠(chéng)交心推進(jìn)故事走向。《上海堡壘》為數(shù)不多的“走心”戲份安排在了上海弄堂里的一間面館里,這本應(yīng)是讓鹿晗飾演的小兵江洋和舒淇飾演的教官林瀾增進(jìn)感情的出彩段落,也是體現(xiàn)這部具有上海特色的科幻電影的“本土化”特色的最佳場(chǎng)景,但是影片卻沒(méi)有將面館賦予海派氣息與上海特色,反而莫名其妙地給面館起了“KK面館”的西式名稱,并且面館老板一張嘴說(shuō)的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立刻沖淡了本應(yīng)內(nèi)涵豐富的上海城市特色。加上鹿晗的北京口音以及舒淇自帶的香港口音,這段本應(yīng)最能體現(xiàn)“在地化”特色的戲份仿佛變成天南地北的白領(lǐng)們邊吃工作餐邊聊閑天的場(chǎng)景重現(xiàn),不客氣地說(shuō),即使將這一場(chǎng)景移置到青春偶像電視劇中也毫無(wú)違和感。從這一個(gè)例子就可以看出,《上海堡壘》只是將上海作為包裹影片宣傳外殼的手段,卻沒(méi)有將好萊塢高概念影片的科幻思路進(jìn)行踏踏實(shí)實(shí)的“在地化”改造。相比于《流浪地球》中精心設(shè)計(jì)的北京地下城雖簡(jiǎn)陋但卻飽含市井風(fēng)俗的“包餃子、打麻將、舞龍舞獅”的場(chǎng)景,以及特別安排的的由Mike隋飾演的“京片子”人物,《上海堡壘》的“在地化”改造可謂流于形式,其收獲的評(píng)價(jià)流于平庸甚至飽含負(fù)面情緒也就在所難免了。
二、“淺嘗輒止”的主角性格塑造與“臉譜化”的配角形象展現(xiàn)
《上海堡壘》引發(fā)話題討論的一大焦點(diǎn),就在飾演男主角江洋的演員鹿晗身上。可以說(shuō),近年來(lái)受眾的關(guān)注點(diǎn)始終都沒(méi)有離開(kāi)過(guò)對(duì)于“流量明星”的爭(zhēng)議。自2013年《小時(shí)代》將“小鮮肉”這個(gè)詞迅速推上輿論熱點(diǎn)以來(lái),“流量明星”就頻頻成為沒(méi)有演技、只有顏值卻擁有大批忠實(shí)粉絲的代名詞。然而平心而論,《上海堡壘》中鹿晗與角色本身的匹配度是足夠的,男主角江洋作為一個(gè)頭腦與動(dòng)手能力都極強(qiáng)的天才少年,其身上洋溢的“少年感”和對(duì)愛(ài)情的懵懂單純恰好符合鹿晗本身帶給觀眾的印象,如果設(shè)計(jì)合理,這恰恰符合如施瓦辛格之于《終結(jié)者》、約翰尼·德普之于《加勒比海盜》一樣的高概念影片“類型化”主角的特點(diǎn)。而關(guān)于“厚劉海”和戰(zhàn)爭(zhēng)過(guò)程中很少浴血破相的“美顏”等細(xì)節(jié),其實(shí)也并未過(guò)多影響觀眾觀看影片的進(jìn)程。事實(shí)上,《上海堡壘》對(duì)于角色在性格塑造上普遍存在的“淺嘗輒止”態(tài)度才是影片使觀眾“代入感”和“共情”不足的核心原因。
舉例來(lái)說(shuō),男主角江洋的角色設(shè)定就是一個(gè)單純的大男孩,他具備極高的操作雙系統(tǒng)控制無(wú)人機(jī)擊退敵人的天賦,也具備團(tuán)結(jié)灰鷹小隊(duì)各個(gè)成員的領(lǐng)導(dǎo)能力。隨著影片進(jìn)程中與外星“捕食者”的不斷較量,他也最終成為一名合格的指揮官。對(duì)比可見(jiàn),這一人物形態(tài)設(shè)置與好萊塢高概念影片《安德的游戲》產(chǎn)生了明顯的互文關(guān)系。《安德的游戲》也是根據(jù)知名小說(shuō)改編的電影,同樣講述了為抵抗外星蟲族的攻擊,人類艦隊(duì)著力培養(yǎng)一名天賦異稟的小男孩安德,并通過(guò)不斷的實(shí)戰(zhàn)訓(xùn)練使其最終成長(zhǎng)為核心指揮官并挽救了地球的故事。同樣是天才少年的設(shè)定,同樣是缺少人情世故的磨礪,《上海堡壘》對(duì)于江洋這一角色的最大缺陷就體現(xiàn)在沒(méi)有遵循“英雄成長(zhǎng)模式”的成熟規(guī)律,讓江洋自始至終都過(guò)于“完美”,缺少人物遇到重大挫折后的跌倒、反思和重新崛起。正如美國(guó)電影理論家大衛(wèi)·波德維爾非常強(qiáng)調(diào)“起因,結(jié)果,心理動(dòng)機(jī),克服障礙推動(dòng)力,最終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的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一樣,這些敘事上長(zhǎng)久流傳的英雄成長(zhǎng)“套路”仍然被證實(shí)是最有效的吸引受眾的方法。可以說(shuō),《上海堡壘》在本已缺少創(chuàng)新性想象力的情況下,連現(xiàn)成的“模式套路”都不愿意去“套”。從這方面看,《上海堡壘》既不愿意走別人走過(guò)的路(例如嵌套好萊塢高概念影片中的經(jīng)典敘事模式),也沒(méi)有花力氣自己去創(chuàng)出一條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新路(例如學(xué)習(xí)《流浪地球》中以小集體的犧牲去換取大集體勝利的中國(guó)模式)。
“高概念”電影中對(duì)于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的刻畫,往往符合美國(guó)比較神話學(xué)者坎貝爾對(duì)于希臘神話中英雄成長(zhǎng)的模式總結(jié)——“分離—傳授奧秘—?dú)w來(lái)”是英雄成長(zhǎng)的必由之路。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角色必須經(jīng)歷不斷的磨煉和打擊,最終換來(lái)的成功和榮耀才能令觀眾感受到十足的心理補(bǔ)償,體會(huì)到心理觀影快感。對(duì)比與《上海堡壘》同期上映的高票房國(guó)產(chǎn)影片可見(jiàn),災(zāi)難大片《烈火英雄》中黃曉明飾演的消防隊(duì)隊(duì)長(zhǎng)正是在經(jīng)歷了因自大而害死隊(duì)員的巨大挫折后,克服心魔重新戰(zhàn)勝自己,最終以一己之力抗擊熊熊烈火,在挽救了城市的同時(shí)也完成了對(duì)自我的救贖;《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小哪吒也是歷經(jīng)眾人的排解、嘲諷、打擊后,擺脫了人心深處“本我”的束縛,最終得以勇敢選擇以柔弱幼小但又強(qiáng)大寬厚的“超我”胸懷力抗天劫,成長(zhǎng)為真正的英雄。羅伯特·麥基在《故事》中指出,“人物性格真相在人處于壓力之下做出選擇時(shí)得到揭示——壓力越大,揭示越深,其選擇便越真實(shí)地體現(xiàn)了人物的本性”。無(wú)論是《流浪地球》中吳京飾演的父親以毀滅飛船來(lái)?yè)Q取整個(gè)地球和人類的希望,還是《烈火英雄》中黃曉明飾演的隊(duì)長(zhǎng)以血肉之軀在高溫的火場(chǎng)中硬生生轉(zhuǎn)了“8000次”轉(zhuǎn)盤最終關(guān)上閘門,抑或《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曾經(jīng)不知天高地厚“懟天懟地”的小哪吒最終成長(zhǎng)為勇敢承受天劫的蓋世英雄,這些影片都在“英雄成長(zhǎng)”過(guò)程中,設(shè)計(jì)了超乎尋常的困難和西西弗斯式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正是如此,由跌落神壇的“人”到最終英雄崛起的“超人”的轉(zhuǎn)變,才能真正通過(guò)感召力上的觸底反彈去觸動(dòng)受眾,使其內(nèi)心受到強(qiáng)烈的震撼并獲得滿足感。
反觀《上海堡壘》,其角色設(shè)置總帶有“浮光掠影”的虛弱感,在最應(yīng)深入塑造人物性格的時(shí)候往往選擇“輕描淡寫”。影片對(duì)江洋這一“優(yōu)等生”的角色把握總給人“捧在手里怕化了”的感覺(jué),沒(méi)有安排任何“扎”進(jìn)人物內(nèi)心的性格塑造,使得這個(gè)本應(yīng)經(jīng)歷戰(zhàn)爭(zhēng)重壓和愛(ài)情挫折后,由大男孩成長(zhǎng)為真正男子漢的角色,毫無(wú)熱血拼搏,沒(méi)有矛盾沖突,缺少放手一搏,從未咬牙切齒,硬生生將這一人物高高捧起,塑造成了一個(gè)只可遠(yuǎn)觀卻并不能攝人心魄的“木頭人”形象。《上海堡壘》在人物設(shè)計(jì)上,很像一部包裹著科幻外衣的“小清新”校園青春劇的模式——江洋如同高考班中那種“別人家的孩子”(片中他天賦異稟),立志要考上最好的大學(xué)(片中他報(bào)名上海堡壘戰(zhàn)區(qū),立志未來(lái)當(dāng)一名指揮官);而舒淇飾演的林瀾如同充滿成熟女性魅力的班主任(片中是江洋的教官)。江洋在沖刺備戰(zhàn)高考(片中他在上海堡壘中經(jīng)受戰(zhàn)備訓(xùn)練)的過(guò)程中總是獲得第一名,而且很有領(lǐng)導(dǎo)能力,和他的同班同學(xué)(片中灰鷹小隊(duì)的其他成員)一起并肩作戰(zhàn)、努力復(fù)習(xí),他們關(guān)系融洽,沒(méi)有發(fā)生過(guò)任何矛盾和沖突(片中灰鷹小隊(duì)成員間極其團(tuán)結(jié))。這時(shí)候從未品嘗過(guò)失敗滋味的江洋由于青春的懵懂開(kāi)始“暗戀班主任”(片中江洋給林瀾送花表達(dá)愛(ài)意),但是班主任為了讓他更好地備戰(zhàn)高考(片中江洋的核心任務(wù)是擊退外星人)而對(duì)他若即若離(片中林瀾對(duì)江洋發(fā)來(lái)的問(wèn)候總是回復(fù)得“不痛不癢”),使他感受到了“少年維特之煩惱”。最終,高考來(lái)臨(外星人發(fā)起總攻),其他幾名同班同學(xué)相繼失利(片中灰鷹小隊(duì)其他成員全部犧牲),只有江洋成功考取高考狀元(片中只有江洋最終完成任務(wù)且死里逃生),五年后當(dāng)他再次回到母校時(shí)(片中江洋回到和林瀾相識(shí)的面館),感受到正是老師當(dāng)年的顧全大局才使自己沒(méi)有偏離方向而實(shí)現(xiàn)了自己的價(jià)值(片中他擊退了外星人,成為了一名合格的指揮官)。以上可見(jiàn),影片對(duì)于江洋性格內(nèi)在的張力幾乎沒(méi)有任何展現(xiàn),作為一部科幻大片中具有“救世”屬性的主角,卻被處理成一名毫無(wú)內(nèi)在性格沖突和成長(zhǎng)變化的“好好先生”,同時(shí),對(duì)江洋的人物設(shè)定屬于“孤身一人”——他似乎沒(méi)有家人,也沒(méi)有任何和家人的牽絆,在巨大的壓力面前,他只能想起一個(gè)“暗戀”的“班主任”作為寄托。這樣略顯虛假的情感投射就決定了這一角色無(wú)法讓觀眾真正認(rèn)同,因此,《上海堡壘》既沒(méi)有達(dá)到青春片那種吸引受眾引發(fā)青澀過(guò)往“回憶殺”的目的,又沒(méi)有贏得科幻電影受眾對(duì)于熱血與想象力的期待。
《故事處方》的作者丹提·W·摩爾曾指出:“你的角色不是由你來(lái)定義的。這是因?yàn)榻巧陨淼男袨椤⒎磻?yīng)、不作為、說(shuō)過(guò)和沒(méi)說(shuō)過(guò)的話,共同定義了角色的性格特征。”但《上海堡壘》對(duì)于眾多配角的塑造也同樣只傳遞出蜻蜓點(diǎn)水和千篇一律的敷衍感。例如除女主角林瀾被設(shè)計(jì)成一名難以接近的指揮官外,總司令邵一云和掌管上海大炮的司令官楊建南的外在形象也都和林瀾一樣,永遠(yuǎn)呈現(xiàn)一幅冷若冰霜的“撲克臉”,完全體現(xiàn)不出不同角色在片中應(yīng)起到的或搞笑調(diào)節(jié)氣氛、或堅(jiān)毅果敢體現(xiàn)“導(dǎo)師”的作用、或溫情脈脈展現(xiàn)女性的柔美、或軟弱無(wú)能反襯英雄的偉大等輔助作用。對(duì)江洋戰(zhàn)友們的塑造更是“簡(jiǎn)單粗暴”,例如曾煜和潘隊(duì)都被設(shè)定為勇猛、直接、熱血、沖動(dòng)的形象,令觀眾對(duì)二人“傻傻分不清楚”;唯一的女性配角路依依前半段暗戀著江洋,中后段又突然毫無(wú)征兆地展現(xiàn)出對(duì)潘隊(duì)?wèi)偃税愕牟簧幔粌H對(duì)前史毫無(wú)交代,而且情感轉(zhuǎn)換也顯得生硬、充滿荒誕感。對(duì)比之下,在《烈火英雄》中,即將奔赴“有去無(wú)回”的火災(zāi)戰(zhàn)場(chǎng)時(shí),影片安排黃曉明飾演的犯過(guò)錯(cuò)誤的前任隊(duì)長(zhǎng)與杜江飾演的一直對(duì)前任隊(duì)長(zhǎng)耿耿于懷的現(xiàn)任隊(duì)長(zhǎng)相對(duì)而視,他們共同拿出香煙就著火場(chǎng)的火焰點(diǎn)煙后相視一笑。這樣精彩細(xì)致的角色刻畫,不用過(guò)多言語(yǔ)就把巨大壓力下戰(zhàn)友之間的一笑泯恩仇躍然于銀幕之上,令人淚目。但在《上海堡壘》中,當(dāng)面對(duì)即將吞噬掉人類的外星捕獵者的大兵壓境時(shí),那些彌足珍貴的戰(zhàn)友情和本應(yīng)令人血脈賁張的殺敵的緊迫感,卻完全被阻擋在了影片對(duì)于角色設(shè)限的桎梏之外。在《上海堡壘》呈現(xiàn)的戰(zhàn)場(chǎng)上,那些面對(duì)死亡恐懼時(shí)戰(zhàn)友互相視為救命稻草的巨大精神支撐感蕩然無(wú)存,更談不上體現(xiàn)如同《紅海行動(dòng)》《湄公河行動(dòng)》《戰(zhàn)狼2》中的戰(zhàn)斗場(chǎng)景那樣真實(shí)而熱血的“燃”感了。可以說(shuō),拋開(kāi)影片對(duì)于主要角色“英雄成長(zhǎng)模式”上的敘事軟肋,這些對(duì)次要角色的同樣“臉譜化”的性格認(rèn)定也給《上海堡壘》減分不少。不給力的配角形象會(huì)讓觀眾感覺(jué)就像在看一部冗長(zhǎng)乏味的網(wǎng)絡(luò)電視劇而非情節(jié)緊湊的電影,觀眾隨時(shí)會(huì)產(chǎn)生快進(jìn)或者跳過(guò)的沖動(dòng)。《上海堡壘》既沒(méi)能夠體現(xiàn)高概念科幻電影特有的奇觀化的“視覺(jué)溢出”效果,又沒(méi)能展現(xiàn)主人公由弱變強(qiáng)、以弱勝?gòu)?qiáng)的英雄成長(zhǎng)模式,還不能以豐滿立體的次要人物群像輔助提升影片的情感訴求,這體現(xiàn)出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在科幻元素展示與角色性格塑造權(quán)重選擇上的重心不穩(wěn)、顧此失彼。
三、電影節(jié)奏的失當(dāng)與情節(jié)推進(jìn)的業(yè)余
隨著電影生產(chǎn)模式的不斷研究與實(shí)踐,針對(duì)高概念電影本身逐漸產(chǎn)生了一套較為成熟的敘事運(yùn)行規(guī)范——“減弱的敘事”(Reduced Native)。這一理念同樣由美國(guó)電影學(xué)者賈斯汀·懷亞特提出。“減弱的敘事”的核心就體現(xiàn)在單一淺顯的敘事主題和明細(xì)有力的敘事節(jié)奏上。正如有學(xué)者的研究所指出的,“劇情簡(jiǎn)單是高概念電影特征之一。但是,情節(jié)相對(duì)簡(jiǎn)單并不等于對(duì)故事性的要求降低……相反地,是要在一個(gè)相對(duì)簡(jiǎn)單的概念下發(fā)展出足夠復(fù)雜的人物和故事,讓觀眾維持觀看興趣,由此吸引更多的受眾。這就是好萊塢成功的高概念影片與國(guó)產(chǎn)高概念影片在劇情掌控上最大的區(qū)別”。
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上海堡壘》與《獨(dú)立日》在結(jié)構(gòu)和故事上具備相似之處——在背景建構(gòu)上,兩部影片同樣設(shè)計(jì)了人類面臨巨型飛碟般的外星母艦的挑釁,同樣具備面對(duì)外星人來(lái)勢(shì)洶洶攫取資源的困境;人物設(shè)置上,同樣安排了高冷女性與低地位男性之間的人物互動(dòng);戰(zhàn)斗過(guò)程中,同樣呈現(xiàn)了我方戰(zhàn)機(jī)面對(duì)敵方數(shù)量龐大軍隊(duì)的寡不敵眾局面,也同樣安排了高潮處以主人公犧牲自己沖向母艦換取最終勝利的壯烈橋段,等等。正因如此,《上海堡壘》與高概念大片《獨(dú)立日》具備很強(qiáng)的互文關(guān)系和互通之處。作為一部罕見(jiàn)的展現(xiàn)“地球反擊戰(zhàn)”的美國(guó)電影,《獨(dú)立日》一改好萊塢高概念科幻大片通常裹挾的“拓殖邏輯”,轉(zhuǎn)“星際殖民”之“攻”為“保衛(wèi)疆土”之“守”,與東方傳統(tǒng)中以農(nóng)耕文化為主的文化思維相契合。從這個(gè)方面來(lái)說(shuō),對(duì)于《獨(dú)立日》成功因素的挖掘和剖析,有利于側(cè)面反思《上海堡壘》失利的原因。
與《獨(dú)立日》相比,《上海堡壘》在影片氛圍塑造上沒(méi)有形成較強(qiáng)的緊迫感和流暢性,其在電影節(jié)奏的把握方面有很大的欠缺,這僅從影片對(duì)于整個(gè)戰(zhàn)爭(zhēng)過(guò)程中“壓迫感”的烘托失敗就可見(jiàn)一斑。影片開(kāi)始階段,當(dāng)?shù)弥庑侨司薮蟮牡聽(tīng)査概瀬?lái)襲,上海堡壘基地倉(cāng)促通知召開(kāi)紅色緊急會(huì)議時(shí),影片并沒(méi)有給觀眾形成“大兵壓境”時(shí)強(qiáng)烈的緊張氣氛,這是因?yàn)樵诖酥埃捌瑢?duì)于情節(jié)的鋪墊不足,前期我方士兵嚴(yán)陣以待的備戰(zhàn)感不強(qiáng),致使影片內(nèi)在張力缺失,影片推進(jìn)雖然流暢但就像流水賬一樣,過(guò)于平緩淡定。“‘高概念電影’在進(jìn)行核心敘事過(guò)程中,通過(guò)發(fā)展一系列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情節(jié)實(shí)現(xiàn)某個(gè)中心目標(biāo)。在觀賞這個(gè)目標(biāo)實(shí)現(xiàn)過(guò)程中,觀眾感受不到導(dǎo)演或攝影機(jī)的存在,感受到的只是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的流暢性和連續(xù)性。”但《上海堡壘》在節(jié)奏把握上就明顯呈現(xiàn)出缺失,顯得并不專業(yè),就像圍棋高手對(duì)決,前期準(zhǔn)備的戰(zhàn)術(shù)思路不到位,就注定了全局最終失利的結(jié)果。
希區(qū)柯克著名的“定時(shí)炸彈”理論指出,要讓炸彈在觀眾的內(nèi)心出現(xiàn),并且不能讓其爆炸,以保證這種緊張感和壓迫感將觀眾代入影片的節(jié)奏之中。同樣是呈現(xiàn)外星人大兵壓境的局勢(shì),《獨(dú)立日》精心設(shè)計(jì)以母艦在地面上形成的巨大的陰影來(lái)烘托氣氛,當(dāng)母艦的黑影不斷籠罩在美國(guó)最具有標(biāo)志性的建筑物(林肯像、白宮、金門大橋)上,甚至完全遮蔽了自由女神像使其不再“自由”時(shí),觀眾內(nèi)心對(duì)于外星母艦的巨大好奇感與恐懼感被無(wú)限喚起,影片就得以最大限度營(yíng)造出“末世情結(jié)”下“黑云壓城城欲摧”的恐怖氣氛。為了渲染這種氛圍,《獨(dú)立日》甚至搬出了總統(tǒng)被迫逃亡的窘迫以及白宮被輕易摧毀的情節(jié)。此外,《獨(dú)立日》高潮部分體現(xiàn)了典型的“最后一分鐘營(yíng)救”的緊迫感:當(dāng)人類方唯一帶有武器的戰(zhàn)機(jī)發(fā)現(xiàn)導(dǎo)彈意外卡住后,編劇順勢(shì)“推波助瀾”,安排敵方母艦迅速打開(kāi)流光炮,即將毀滅人類指揮部。千鈞一發(fā)之際,人類方戰(zhàn)機(jī)駕駛員決定以自己和戰(zhàn)機(jī)作為“炮彈”,直沖向敵方露出的炮口,進(jìn)而在電光石火間從暴露的敵方缺口攻入,與母艦同歸于盡。如此緊張跌宕的情節(jié)設(shè)計(jì)牢牢把握了觀眾的內(nèi)心高潮點(diǎn),令觀眾屏住呼吸,欲罷不能。與此相反,《上海堡壘》在情節(jié)設(shè)計(jì)上,卻安排影片在進(jìn)行到34分鐘時(shí),就用我方最強(qiáng)的武器“上海大炮”一炮把對(duì)方母艦“轟”沒(méi)了,致使影片第一次高潮過(guò)早到來(lái)。這樣的安排導(dǎo)致影片又進(jìn)行了半小時(shí),當(dāng)觀眾面臨再次到來(lái)的高潮時(shí),早已失去了對(duì)這一本應(yīng)令人血脈賁張的“天地對(duì)決”部分的新鮮感。《上海堡壘》在情節(jié)安排上的脫節(jié)是影片的敗筆之一。這樣的安排輕易浪費(fèi)掉了好不容易累積起的觀眾情緒,“一鼓作氣,再而衰”,到了真正的最終高潮時(shí),影片已經(jīng)錯(cuò)過(guò)了觀眾心理期待的最佳興奮點(diǎn),觀眾的內(nèi)心必然毫無(wú)波瀾、無(wú)動(dòng)于衷。
綜上可見(jiàn),《上海堡壘》雖然試圖在科幻片與愛(ài)情片的結(jié)合上進(jìn)行嘗試,但仍在諸多方面存在嚴(yán)重的問(wèn)題,因此,它只能算作一部披著“高概念”外衣的“偽高概念”電影。筆者期望努力試水新類型的中國(guó)電影創(chuàng)作者,在借鑒和套用成熟電影工業(yè)模式這些外在“皮囊”的基礎(chǔ)上,能更加腳踏實(shí)地研究好電影語(yǔ)言和敘事結(jié)構(gòu)上的內(nèi)在“硬核”,形成如《流浪地球》和《哪吒之魔童降世》一樣在更多電影類型領(lǐng)域的偉大創(chuàng)新與突破。
注釋:
[1][2][7]遠(yuǎn)牧.國(guó)產(chǎn)“高概念”電影:喧囂背后的蒼白[J].粵海風(fēng),2013(2):65,66,66.
[3]吳冠平.當(dāng)下中國(guó)電影的美學(xué)之變[J].當(dāng)代電影,2018(2):114.
[4]轉(zhuǎn)引自周學(xué)麟.“高概念”電影與國(guó)產(chǎn)大片[J]. 上海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2):16.
[5]〔美〕羅伯特·麥基.故事:材質(zhì)、結(jié)構(gòu)、風(fēng)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M].周鐵東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99-100.
[6]賀欣欣.彼得·杰克遜與高概念電影的規(guī)定敘事[J].電影文學(xué),2019(2):93.
[8]周學(xué)麟.“高概念”電影與國(guó)產(chǎn)大片[J].上海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