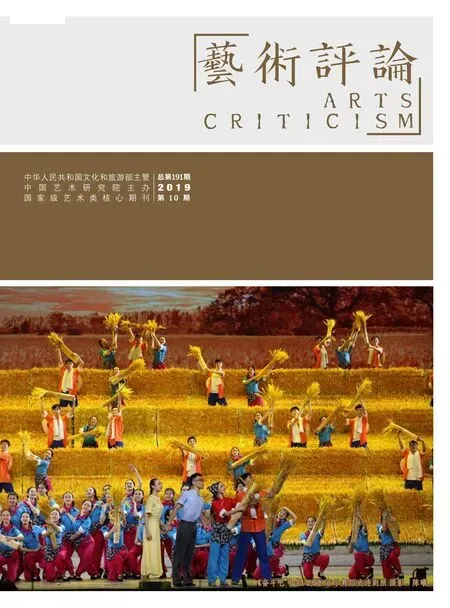人工智能寫作與文學(xué)契約的重建
[內(nèi)容提要]文學(xué)契約是在長時期的文學(xué)活動中形成的一些具有基礎(chǔ)性、規(guī)范性、示范性意義的準(zhǔn)則或傳統(tǒng)。文學(xué)契約既具有歷史連續(xù)性,又表現(xiàn)出時代色彩。文學(xué)契約的形成,保障了文學(xué)的持續(xù)再生產(chǎn),推動了文學(xué)經(jīng)典的誕生,也使文學(xué)在社會文化結(jié)構(gòu)中占有獨特位置,形成了自身的話語表達(dá)空間。迄今為止,以“人”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寫作行為仍然是這份文學(xué)契約的起點,并相繼擴展至在文學(xué)傳播、文學(xué)批評和文學(xué)史研究等領(lǐng)域。隨著人工智能寫作的發(fā)生,新的寫作主體開始成為人們的關(guān)注重點。這個事實或事件,動搖了以往文學(xué)契約的穩(wěn)定性與可靠性。人工智能寫作的發(fā)生,既是審視以往文學(xué)契約的契機,也是重建文學(xué)契約的契機,同時也使我們再次思考寫作之于人類的重要意味。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是研究、開發(fā)用于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的理論、方法、技術(shù)及應(yīng)用系統(tǒng)的一門新的技術(shù)科學(xué),又稱智能、機器智能。我們俗稱的“機器人”就是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成果體現(xiàn)。這一項在科技領(lǐng)域中出現(xiàn)的新生事物,很快就成為了我國當(dāng)前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熱門詞匯,既是新聞媒體聚焦的一個重要話題,又是廣大民眾津津樂道的主要談資。媒體的介入,推動了作為術(shù)語概念和物質(zhì)實體的“人工智能”的廣泛傳播,從而提升了這一新技術(shù)的影響力;民眾的談?wù)摚瑒t生動地說明了這一旨在改變?nèi)藗兾磥砩顖D景的新科技展現(xiàn)出的強大生機和活力。事實上,盡管人工智能目前尚處于政策支持、產(chǎn)品研發(fā)、資本流入的階段,還未大規(guī)模、成批量地投入生產(chǎn)和應(yīng)用,但人們已經(jīng)樂于描繪由其所構(gòu)造的種種現(xiàn)實圖景,如AI+物流、AI+醫(yī)療、AI+教育,AI+交通等。的確,相對于航天、生物、量子物理等高精尖的前沿科技而言,人們對“人工智能”并不像對待前者那樣抱有畏懼之感,反而是多了幾分親切。可以說,人們對“人工智能”的概念內(nèi)涵、內(nèi)部構(gòu)成、工作肌理等知識性成分并不了解,但對于由此促成的現(xiàn)實生活的變動和重構(gòu)卻頗為期待。簡單而言,正是由于人工智能之于人的社會生活的應(yīng)用化前景,引發(fā)了公眾對這一新技術(shù)的趨之若鶩。
相比科技界的雄心勃勃、資本界的暗流涌動和社會公眾的熱切期待,從事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的學(xué)者要冷靜、清醒得多。這些學(xué)者分別從自己所在學(xué)科的特性展開論述,認(rèn)為人工智能的出現(xiàn),不能也難以替代他們所從事的工作。還有一部分學(xué)者,則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現(xiàn)代技術(shù)的無限制發(fā)展,表示出并非杞人憂天的擔(dān)憂,在以深度學(xué)習(xí)、無限仿人作為目標(biāo)的人工智能開始進入人類日常生活的情境下,重新思考物與人的關(guān)系。
具體到文學(xué)領(lǐng)域而言,人工智能寫作的發(fā)生,可以稱得上是一個事件。人們對此既震驚、好奇,又懷疑、拒絕。這自然不是傳統(tǒng)對現(xiàn)代、保守對先鋒的天然性反感,也并非某種偏袒,而是由這兩種有著截然不同的運行機制的事物決定了的:一個以工具理性為標(biāo)榜,一個則以情感體驗為標(biāo)識;一個建基于計算之上,一個被想象之光所籠罩。對文學(xué)的“侵入”和“占領(lǐng)”,或者說文學(xué)的主動接納和迎合,既是人工智能發(fā)展自然而然的一個結(jié)果,又是文學(xué)緊跟時代潮流的鮮活體現(xiàn)。不過,相比于以往技術(shù)與文學(xué)的結(jié)合而言,這一次人工智能對文學(xué)的參與,卻有著更為重大的信號釋放,直接觸動了以往文學(xué)契約的穩(wěn)定性和可靠性,或可引發(fā)包括作者、讀者和批評等在內(nèi)的文學(xué)契約的重建。
文學(xué)契約與文學(xué)活動
契約精神是現(xiàn)代社會的一塊基石。契約一詞多出現(xiàn)在法律、經(jīng)濟等社會活動中。把這一詞引入文學(xué),并非是對文學(xué)做出某種硬性規(guī)定——事實上文學(xué)從來就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本質(zhì)性規(guī)定,這也正是文學(xué)的活力之源——而是指文學(xué)有著自身的若干特性。這些特性直接關(guān)聯(lián)著文學(xué)活動的發(fā)生和展開。文學(xué)是寫作者個體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但也并非毫無禁忌或規(guī)范。盡管以往的規(guī)范構(gòu)成了后來文學(xué)突破和反抗的對象,但在突破和反抗之后,又將建立起新的美學(xué)原則。規(guī)范和反規(guī)范,正構(gòu)成了文學(xué)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的內(nèi)在動力。因此,所謂的文學(xué)契約是指在文學(xué)內(nèi)部具有基礎(chǔ)性、規(guī)范性的準(zhǔn)則,具體表現(xiàn)為文類構(gòu)成、文類等級、文類規(guī)則、嚴(yán)肅與通俗之分等。文學(xué)契約的形成,囊括了包括文學(xué)創(chuàng)作、傳播、接受和批評等在內(nèi)的諸種文學(xué)活動。
文學(xué)契約既具有時代性,總要受到時代風(fēng)氣和特定文化語境的影響,這意味著它常常是變動的;又具有歷史性,總有某些因素是無法更易的,這意味著它是穩(wěn)定的、連續(xù)的。
以中國文學(xué)史為例,在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詩、文在文學(xué)場域中占據(jù)著絕對中心的位置,小說則處于被輕視的境況。直到晚清時期,這一局面才開始被打破。從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到五四新文學(xué)運動,小說的價值受到了肯定和表彰,一改往日面目,在傳播新知、抨擊時弊、播撒文明、教化大眾等方面展現(xiàn)出積極的作為。迄今,小說仍然穩(wěn)坐文學(xué)王國中的頭把交椅。時代變遷中文化語境的轉(zhuǎn)變,使得文類之間的等級發(fā)生了變動。
正是由于文類等級的作用,在如今的文學(xué)界,一部小說,顯然比一篇散文更容易獲得關(guān)注;而在小說內(nèi)部,一部長篇小說,比一部中短篇小說更具分量,一部有著嚴(yán)肅主題的小說,要比一部精彩的武俠小說更值得批評家剖析。如是這些,并非勢力使然,正是文學(xué)契約潛移默化的結(jié)果。
文學(xué)契約,有的是以理論形態(tài)存在著,有的則是以約定俗成的方式獲得了通行證明。當(dāng)我們接受了文學(xué)契約時,就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小說的虛構(gòu)特權(quán),就不能把小說當(dāng)作散文來讀,不能對文學(xué)作品中描寫和講述的眾多事件進行對號入座,更不能要求作者對此付出法律責(zé)任或經(jīng)濟代價,也要尊重文學(xué)語言的內(nèi)指性、模糊性、多義性等。如此,創(chuàng)作者的寫作和讀者的閱讀才可能是順暢的,理論范式的建立也才有了可靠的前提。
盡管文學(xué)內(nèi)部遍布著如此之多的規(guī)則,這些規(guī)則又處于不斷調(diào)整的狀態(tài),但文學(xué)活動最基本的構(gòu)成則是艾布拉姆斯所言的作者、世界、作品和讀者四個要素,“每一件藝術(shù)作品總要涉及四個要點,幾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論總會在大體上對這四個要素加以區(qū)辨,使人一目了然”。20世紀(jì)文學(xué)理論分別經(jīng)歷了“作者中心”“作品中心”和“讀者中心”的轉(zhuǎn)向。對文學(xué)四要素中某一要素重要性的強調(diào)和放大,與其說是謀求該要素的獨立,不如說是在理論造成的偏執(zhí)中再次論證了四要素在整個文學(xué)活動中的基礎(chǔ)性、整體性和完整性。可以說,這四個要素,正是文學(xué)契約形成的前提和基礎(chǔ)。
如今,一個新的、不同于人的創(chuàng)作主體正在誕生,這份文學(xué)契約還能繼續(xù)穩(wěn)定地發(fā)揮作用嗎?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當(dāng)人工智能開始成為新的寫作主體時,其所帶來的變動是意味深長的。
文學(xué)與技術(shù)
在探討人工智能寫作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時,我們有必要梳理一下技術(shù)與文學(xué)的歷史性關(guān)系,探討技術(shù)在其中所發(fā)揮的作用。
一部文學(xué)史,不僅是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白話文學(xué)等構(gòu)筑的文學(xué)審美鏈條,還包括著經(jīng)濟、社會、文化等在內(nèi)的具體歷史語境。在這種語境內(nèi),技術(shù)的參與同樣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具體表現(xiàn)為各種樣式的媒介。“文學(xué)的存在基礎(chǔ)必須是傳播媒體,文學(xué)文本的存在必須依靠物質(zhì)和技術(shù)手段,其傳播與接受也只能通過技術(shù)手段的中介來實現(xiàn),因此,文學(xué)的歷史從一開始便可視為一部媒介史。”
僅僅從寫作字?jǐn)?shù)的增加這一表象來看,就可以看出媒介變革對文學(xué)發(fā)展和傳播所產(chǎn)生的重要推動作用。如果沒有媒介的參與和變革,文學(xué)的發(fā)展和繁榮是不可想象的,文化的普及和推廣也是難以進行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生和發(fā)展,既有源自對本民族文學(xué)進行糾偏的內(nèi)在沖動,又受到了來自異域思想文化藝術(shù)的外在影響,同時也離不開包括報紙、期刊、雜志、書局、出版社等以印刷媒介為主要物質(zhì)支持的文化組織的參與和推動。這些紙媒有效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傳播范圍,增強了這一運動的影響力,使一小部分精英人士的努力與愿景成為了具有深遠(yuǎn)歷史影響的啟蒙運動實踐。由此可見,印刷媒介在我們的社會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流布》中毫不夸張地肯定了印刷媒介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構(gòu)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20世紀(jì)90年代以后,互聯(lián)網(wǎng)和電子媒介的相繼出現(xiàn),再次引發(fā)了文學(xué)寫作的變動,使文學(xué)內(nèi)部的關(guān)系再次調(diào)整,形成了新的文學(xué)存在狀態(tài)。“數(shù)字化電子媒介和網(wǎng)絡(luò)的超強信息傳播功能可以把作家和讀者實時性地連接在一起進行即時溝通甚至在線互動,從而形成數(shù)字文學(xué)特有的‘適時交互一體化’的文學(xué)動態(tài)存在。”
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興起和發(fā)展,正得益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達(dá)。在眾多作家、批評家和學(xué)者的努力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合法性日益鞏固。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中的“網(wǎng)絡(luò)”毋寧說是一個空間性的存在,為文學(xué)寫作和傳播提供了新的寫作載體和傳播渠道,并由于寫作者的可匿名性而獲得了新的可能性。但無疑,這些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品,仍然是由人來完成的,這其中泥沙俱下,甚至出現(xiàn)了復(fù)制、拼貼、剽竊、抄襲等不良現(xiàn)象,產(chǎn)生了一大批格調(diào)低下的作品。饒是如此,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尚未動搖文學(xué)活動的基本環(huán)節(jié),對文學(xué)契約的改動也還只是在內(nèi)部展開。
在技術(shù)發(fā)展的有力支撐下,手機、博客、微博、微信公眾號、視聽APP(如抖音、快手、蝦米等)等各種新的媒介形式相繼出現(xiàn),使寫作人數(shù)大為增加,寫作的速度日益加快,文學(xué)傳播和閱讀的渠道更為多樣、便捷,傳播的鏈條有所延長。以喜馬拉雅APP為例,這是一款以聲音作為主要產(chǎn)品(商品)的應(yīng)用軟件,開發(fā)大量聲音資源,包括廣播、戲劇、書籍、課程、音樂、談話等在內(nèi),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通過聽覺感官接受知識和信息。至此,文學(xué)作品再度享受了技術(shù)的便利。
新媒介的出現(xiàn)和應(yīng)用,并非是對舊媒介的否定,而是對舊媒介的擴充。時至今日,口耳相傳仍然是人類的一個基本行為,紙質(zhì)媒介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xué)獎的《繁花》就是首先在網(wǎng)絡(luò)上完成“草稿”的,在寫的過程中,即寫即發(fā),并與讀者即時互動。經(jīng)過對“草稿”的刪改后,先是發(fā)表在《收獲》雜志上,后又出版發(fā)行。《繁花》的創(chuàng)作過程,不僅體現(xiàn)了網(wǎng)絡(luò)寫作的即時互動和傳播特性,也體現(xiàn)了電子媒介與紙質(zhì)媒介之間的互動,具有典型性。人工智能寫作恐怕同樣需要借助印刷媒介,實現(xiàn)自身由虛擬形態(tài)向?qū)嵨镄螒B(tài)的轉(zhuǎn)變。只要這還是一個由人主導(dǎo)的社會,人工智能寫作就不能罔顧已然成為一種傳統(tǒng)的文化慣性。
從口耳相傳到印刷媒介,再到五花八門的電子媒介,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廣泛應(yīng)用,不僅改寫著文學(xué)的寫作載體、生產(chǎn)方式、傳播方式,并靜悄悄而不失深刻地改變了個體的生活方式、記憶方式、體驗方式等。在口耳相傳的文化語境中,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聯(lián)系尤為緊密,群體性的生活因而成為一種主要形態(tài);在印刷媒介構(gòu)成的文化語境中,個人對他人的需要程度已經(jīng)大為降低,個人主義開始成為興起;電子媒介的發(fā)展,更是助長了個人主義的盛行,以“宅”為代表的生活方式正是一個鮮明的表征。
種種跡象表明,技術(shù)的力量不可小視。技術(shù)直接參與了文化語境的生成,并在其中占據(jù)著顯赫的位置。試想,今天的人們離開種種技術(shù)后,將會是一幅怎樣的情景呢?以往的社會文化經(jīng)驗已經(jīng)告訴我們,建基在現(xiàn)代技術(shù)之上的各種新媒介,在彌補了印刷媒介的不足,延伸人的感覺器官、延長人的時空軸長時,也將人和社會引向日益破碎、膚淺的文化節(jié)奏中,使人過度地追求刺激與快感,并安然于瞬時的感官愉悅。對此,著名媒介學(xué)者尼爾·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娛樂至死》與《技術(shù)壟斷》三部著作中有過精彩的描述、分析和論述,其中提出的許多觀點,振聾發(fā)聵。
人類創(chuàng)造的技術(shù),反過來也在創(chuàng)造著“人”,甚至有可能對人產(chǎn)生壓制。技術(shù)作為信息的服務(wù)方,轉(zhuǎn)而成為了信息的提供方,甚至是壟斷方。因此,面對技術(shù)背后的文化陷阱,我們保持需要清醒的認(rèn)識,并有針對性地做出反抗,捍衛(wèi)人之為人的主體性、主動性。比如說,媒介的多樣化,為人們的閱讀和求知提供了日益便捷的途徑,使人們在時間的邊角縫隙都可以展開這些活動。但一個醒目的結(jié)果便是,閱讀時間碎片化、閱讀對象碎片化,使我們似乎已經(jīng)很難靜下心來長時間地閱讀和思考,而越來越接近于一個“單向度的人”。
面對技術(shù)造成的諸多“惡果”,我們不應(yīng)該一味地責(zé)怪它,尤其是當(dāng)技術(shù)作為一種力量已經(jīng)嵌入整個社會的文化背景之后。我們所能做的,就是以人文的方式,對這種現(xiàn)實進行制衡,使技術(shù)更好地為人類美好生活作出貢獻。文學(xué)也是一種其中方式,而且是相當(dāng)重要的一個方式。
通過梳理文學(xué)與技術(shù)的關(guān)系,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方面文學(xué)從來就沒有拒絕過技術(shù)的參與,反而常常借助技術(shù)來擴大自己的領(lǐng)地;另一方面技術(shù)也絕非僅僅只是一種被人所使用的工具,毫無自己的意志。文學(xué)與技術(shù)的結(jié)合,并非只是1+1這樣簡單的關(guān)系,而是互相滲透、互相改造。有鑒于以往的經(jīng)驗,我們對人工智能寫作的恐慌和焦慮并非沒有源由。人工智能寫作的發(fā)生,無疑將會再一次地使我們進入一個新的文化語境中。這種語境會是怎樣的呢?又將給我們帶來哪些改變呢?文學(xué)又將走向何處呢?
盡管人工智能也是一項技術(shù),但由于它更加主動、直接地參與到文學(xué)寫作中,還是顯露出了與其他技術(shù)相比而較為特殊的一面。也就是說,當(dāng)人工智能開始成為新的寫作主體時,以作者為開端的文學(xué)活動將會產(chǎn)生多米諾骨牌效應(yīng),從而導(dǎo)致文學(xué)契約的再度改寫。作為一種正在進行著的、新的文學(xué)活動,人工智能寫作固然充滿了生機,但其中是不是同樣也隱含著危機呢?
作者是“誰”:主體的隱退
據(jù)葉永烈講述,曾翻譯過錢鍾書作品的德國漢學(xué)家鄧成博士(C.Dunsing)在北京拜訪錢鍾書時,錢鍾書對鄧講:“現(xiàn)在,許多青年學(xué)者看了我的小說《圍城》,一定要看一看我是什么模樣的。其實,你吃了雞蛋,何必一定要看雞呢?”
在這里,向以幽默著稱的錢鍾書以生動、形象的比喻描述了作者和作品的關(guān)系,表現(xiàn)了錢的謙遜和低調(diào)。但讀者對作者的關(guān)心和好奇,恰恰也反映了作者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突出位置,“一部文學(xué)作品的最明顯的起因,就是它的創(chuàng)造者,即作者”。
如果說在20世紀(jì)中葉引起廣泛爭議的“作者之死”還只是一種規(guī)定性的理論范式,旨在強化文學(xué)文本的獨立性,推崇包括研究者在內(nèi)的讀者的介入,那么,今天的人工智能寫作則直接通過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主體——人的取代而消弭了這一論爭,但與此同時卻也將新型寫作置于更復(fù)雜的社會場域中。
人工智能寫作和人的寫作有哪些不同呢?這些不同對于文學(xué)作品的創(chuàng)作和閱讀會產(chǎn)生影響嗎?又會產(chǎn)生哪些影響呢?這些問題并非只是一種簡單的比較,而是直接關(guān)系著人工智能否替代人的合法性所在。
首先,人工智能寫作不是一種自發(fā)性的寫作,仍然要受到人的操作、控制和指引。說到底,以機器為表現(xiàn)載體的人工智能還是一種物,即便它試圖最大化地模仿、接近人類,但仍然與人之間有著根本性差異。受到操縱的人工智能寫作就必須服從和服務(wù)于特定的寫作意圖,而寫作的主動性、主體性、獨特性自然無法得到保障,而后者卻是文學(xué)最能體現(xiàn)作為主體的人的意志和力量的根本性所在,“每一位作家、詩人都是一個個具體的‘單個人’,但還包括深一層的含義,即指文學(xué)活動作為一種有意識活動必然是個體的活動,因為人類從來就沒有一個意識的總頭腦”“否認(rèn)作家、詩人的個體性,也就否定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自主性和創(chuàng)造性”。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工智能寫作難以形成自己的風(fēng)格,建立自己的獨特性,實現(xiàn)如法國文論家布封所說的“風(fēng)格即人”。
因此,人工智能寫作無需或者說是無法對作品的個人性、獨創(chuàng)性、深刻性、審美性作出允諾,并付諸實踐,“機器的優(yōu)勢只是它只能遠(yuǎn)比人快速與海量地做出各種字詞的拼合,它也許還能根據(jù)人的選擇和評判不斷地改進自己,它也可以嘗試一種‘類型化的寫作’,設(shè)計好大致的情節(jié)、人物進行各種各樣的字詞填充”。面對類型化、模式化的敘事,人工智能寫作通過大數(shù)據(jù)的搜集、整理與歸納,并在此基礎(chǔ)上,通過對構(gòu)成特定敘事類型的若干要素進行分析、辨認(rèn)和重組,從而生產(chǎn)出各種千變?nèi)f化的故事,滿足讀者追求新鮮、刺激、愉悅等的閱讀需求。但這其中的人物、主題、情節(jié)乃至語言,顯然是一種更為高級的拼貼與組合,實質(zhì)上是對人的創(chuàng)作的追隨和模仿。盡管這是一個對技術(shù)有所不敬的說法,但我仍然想說,這種生產(chǎn)機制和線上線下的通俗小說無異。
此外,人工智能寫作既然是由人來操控完成的,那么這個“人”應(yīng)該是誰呢?這個“人”的操控,是否可以隨心所欲、無所顧忌?這會不會演變?yōu)橐粋€新的被人追逐的權(quán)力?在作品完成以后,誰可以擁有對這部作品的歸屬權(quán)?誰又應(yīng)該對這部作品負(fù)責(zé)呢?寫作者的身份不明確,可能會引發(fā)道德、倫理、法律、經(jīng)濟等不同層面的沖突和混亂。
由此展開的一個問題是:假以時日,如果人工智能寫作成為了一種自發(fā)性的寫作時,會不會使文學(xué)寫作陷入失控的境地?在這個時候,還需要文學(xué)嗎?
其次,人工智能寫作的創(chuàng)作源泉顯然不是紛繁復(fù)雜的大千世界和蕓蕓眾生的生命體驗,而是一個封閉的、靜止的數(shù)據(jù)庫。至少目前來看,人工智能寫作還暫時只能是二手寫作,盡管它試圖努力清除自己身上的機器痕跡,最大程度縮小與傳統(tǒng)寫作的差異,混入后者之中。也就是說,人工智能寫作只能是對以往創(chuàng)作的模仿和再造。
日常生活始終處于變動不居的狀態(tài),這也就意味著人們的經(jīng)歷和體驗往往有著特定的時空性。置身其中的個體必須不斷地調(diào)整自我的狀態(tài),適應(yīng)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社會的演進,就是個體在應(yīng)對外界環(huán)境的變化,而作出新的適應(yīng)的過程;環(huán)境一產(chǎn)生變化,所有先前與之契合的思維模式,在新的環(huán)境之中,就可能不再有效。”個體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會產(chǎn)生諸如欣喜、懷舊、不適、懊惱、反感、憎恨等眾多情緒體驗。與個體處于同一語境的作者,能夠及時地捕捉、觀照和回應(yīng)這些復(fù)雜的情緒體驗。很難想象,作為機器的人工智能如何可以體驗這種種真實、微妙、多變的情緒,并巧妙地利用語言文字予以呈現(xiàn)。
以當(dāng)前文壇上廣受關(guān)注的非虛構(gòu)寫作為例,盡管關(guān)于它的定義、內(nèi)涵等仍未取得共識,但我們可以由此看到,一種樸素的、開放的、堅實的文學(xué)觀念正在介入現(xiàn)實并持續(xù)發(fā)生作用。這種寫作方式的生命力顯然不能來自向壁虛構(gòu),而必須從鮮活的社會現(xiàn)實中獲得。寫作者必須實地走訪、調(diào)查、參與甚至融入寫作對象的生活中,才可能最大限度獲得寫作素材,進而展現(xiàn)一種真實的、客觀的現(xiàn)實圖景,描繪身處其中的獨立個體的生活狀況和心靈景象。在這個過程中,寫作者與寫作對象之間的交流對話、情感互動,既是保證寫作內(nèi)容真實性的有效形式,又是作品獲得情感共鳴的重要起點。
再次,人工智能寫作的創(chuàng)作過程顯然缺少了豐富的情感體驗。從唐代詩人盧延讓的《苦吟》“吟安一個字,捻斷數(shù)莖須”到賈島的“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從清代作家曹雪芹創(chuàng)作《紅樓夢》時“批閱十載,增刪五次”到當(dāng)代作家賈平凹創(chuàng)作《秦腔》時先后修改四次、身心俱疲……古往今來的眾多作家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反復(fù)說明了創(chuàng)作是一項艱辛的勞動。從搜集素材到完成構(gòu)思,從安排材料到錘煉文字,從成稿到修改直至定稿,作家們在這一過程中,備受煎熬。在完成史詩般的巨著《白鹿原》后,作家陳忠實如此描述自己的感覺:“是從一個太過深遠(yuǎn)的地道走到洞口,驟然撲來的亮光刺激得我承受不住而發(fā)生暈眩;又如同背負(fù)著一件重物埋頭遠(yuǎn)行,走到盡頭卸下負(fù)載的重物,業(yè)已習(xí)慣的負(fù)重遠(yuǎn)行的生理和心理的平衡被打破了,反而不能承受卸載后的輕松了。”可以說,正是由于作家們的辛苦勞動,才使文學(xué)始終是一項莊嚴(yán)的事業(yè),才使文學(xué)始終有著屬于它自身存在的價值,才能在讀者中間產(chǎn)生共振和共鳴。
人工智能無法體驗到寫作過程中的辛苦,自然也無緣體味其中的甘甜與喜悅。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些甘苦體驗,對于寫作者、對于作品究竟意味著什么呢?是作家完成作品必須經(jīng)受的考驗?還是作家們的自討苦吃?是作品完成過程中自鍍的沉重光環(huán),還是我們?nèi)藶榧又T于作品的附屬之物?當(dāng)人工智能寫作免去了這種種苦辣酸甜的寫作體驗時,是不是就實現(xiàn)了對寫作者的解放,也實現(xiàn)了對文學(xué)的解放?并借此證明,作為人類高級精神活動的文學(xué)寫作同樣也可以享受技術(shù)的蔭庇?
最后,就文學(xué)與社會的關(guān)系而言,人工智能寫作很難承擔(dān)和體現(xiàn)文學(xué)的公共性,使文學(xué)的意義生產(chǎn)功能得到延續(xù)。文學(xué)對社會的參與,事實上關(guān)系著文學(xué)在社會結(jié)構(gòu)中的位置和功能,也關(guān)系著寫作的倫理。“文學(xué)不僅可能改造人們的感性與結(jié)構(gòu),文學(xué)還會某種程度地修正未來生活的藍(lán)圖。”也就是說,文學(xué)從來就不是也不應(yīng)該是純粹的。人工智能則直接過濾、忽視了文學(xué)之外的但并非無足輕重的諸種因素,使寫作的分量輕了不少。但這種“輕”與其說是為文學(xué)減負(fù),不如是在剝奪文學(xué)的權(quán)利、拒絕履行文學(xué)的責(zé)任。
在上文提及的雞和蛋的故事中,錢鍾書的謙虛之詞也并非沒有道理。以作品為中心,的確說到了文學(xué)活動的關(guān)鍵處。說到文學(xué)的各種價值和功能,無疑就直接體現(xiàn)在那些優(yōu)秀的、經(jīng)典的文學(xué)作品上。讀者所關(guān)心和好奇著的作者,正是那些有著良好創(chuàng)作聲譽的作者,而非頂著“作家”之名的任何人。一位勤勉的作家,如果難以產(chǎn)生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這個“作家”的身份顯然是不可靠的。道德評價,并不能代表個人在業(yè)務(wù)上的成就。但是,面對人工智能寫作,如果僅僅以作品的優(yōu)劣來評價寫作主體的話,是否會導(dǎo)致寫作陷入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的窠臼?以計算為主要邏輯的人工智能寫作固然摒除了寫作之外的復(fù)雜因素,少有人情、利益等的羈絆,使寫作成為了一件單純的事情(業(yè)務(wù)?有待加工的產(chǎn)品?)。但這種單純,卻使作品變得冷冰冰了。在這個時候,我們對“作者”的關(guān)心,同時也就是對作為同類的“人”的關(guān)心。
作為社會成員的寫作者,其作品天然地具有社會性。他們既從社會生活中獲得材料,又通過作品回饋社會。這些寫作者,在追求藝術(shù)審美品格、力求突破傳統(tǒng)藩籬的同時,也在以文學(xué)的形式參與社會,既包括對社會的褒揚,更包括對社會的批判和修正。對于文學(xué)的功能、價值和意義,不需要過多地展開論述,這里要強調(diào)的是文學(xué)的這種功能、價值和意義,在人工智能寫作上可以同樣得到體現(xiàn)嗎?如果不能,人工智能寫作的生命力又該如何得到維持呢?
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寫作有其特殊性。人工智能試圖闖入這塊精神高地時,顯然輕視了這一行當(dāng)?shù)纳袷バ院颓f嚴(yán)性。
盡管上述這些不同,已經(jīng)點明了人工智能寫作的諸多不足,但人工智能寫作就真的毫無可取之處了嗎?從歷史發(fā)展過程來看,新的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展和新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出現(xiàn),都以刪繁就簡、提高社會效率為主要目的,或者說為主要動力。人工智能的出現(xiàn),同樣反映出這種趨勢。和人類相比,電子技術(shù)在記憶能力、信息儲存、信息檢索等方面表現(xiàn)出強大的優(yōu)勢。借助大數(shù)據(jù)搜集、整理和分析信息的有利條件,人工智能很大程度上可以減少人們的重復(fù)性勞動,把人們從繁雜瑣碎的事務(wù)中解放出來。同時,人工智能也可以減少人的活動的盲目性,通過最大限度地提供各種數(shù)據(jù)信息,使人們可以更充分地展開分析,作出規(guī)劃。人工智能寫作就得益于這種便利,在對人類創(chuàng)作進行分析和辨別后,完成作品。
從微軟小冰寫詩到新聞智能寫作,人工智能寫作已經(jīng)在寫作中展開更多的嘗試和探索。但由于詩歌的短小精悍,偶得佳作也非沒有可能,因此人工智能的文學(xué)水準(zhǔn)無法得到驗證;至于新聞寫作,本來就是“六個W”的組合,更無什么說服力。因此,人工智能寫作的可取之處,仍有待時間作出證明。
當(dāng)人工智能寫作把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這樣一件需要身心付出的繁瑣工作變成一個由機械按鈕來操作完成的程序時,當(dāng)如同精靈一般的語言文字成為有待加工和組合的元件時,這究竟是對寫作做出的革命性變革呢,還是對寫作的輕視、對人的漠視?在效率優(yōu)先的時代下,文學(xué)又將如何自處呢?文學(xué)之慢,本來就是對技術(shù)之快的抵抗,又如何會甘心被它所“俘虜”呢?
人工智能寫作和人的寫作,不只是一個由誰來寫這樣簡單的問題,也不只是誰優(yōu)誰劣的問題,這背后有著復(fù)雜的思想文化觀念之爭,并再次觸及了寫作的意義、寫作與人的關(guān)系等一系列基礎(chǔ)性問題。
讀者的困惑:與“誰”對話
當(dāng)作家完成一部作品時,僅僅意味著該作品的誕生。只有文本開始被閱讀,它的生命才算被激活,“文學(xué)作品具有結(jié)構(gòu)和意義,其原因在于人們用一種特定的方式來閱讀它,在于這種可能的特性,隱藏在自身之中,被運用于閱讀活動中的敘述原則所現(xiàn)實化了”,這也正是讀者在文學(xué)活動中占據(jù)另一個主體位置的原因所在。
讀者需要文學(xué)。文學(xué)作品可以幫助我們擴大理解生活、進入生活的視野,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塑造我們的情感、態(tài)度和價值觀。文學(xué)作品尤其是小說,在書寫他人日常生活的悲歡離合時,也就讓我們看到了生活的多樣性,從而能夠超越一己之見而看到蕓蕓眾生,并借助他人的眼光認(rèn)識自己。可以說,對文本的閱讀,是讀者與自我、作者、世界展開對話的重要途徑。在這個過程中,讀者才可能借助經(jīng)由語言建構(gòu)的“別處的生活”獲得審美的愉悅、生活的感知、生存的體驗、精神的磨練、思想的砥礪、靈魂的感悟,進而達(dá)成個體對生活、世界的想象性和解。
但這并不意味讀者對文學(xué)不經(jīng)選擇,毫無挑剔。讀者對文學(xué)作品的期待,不僅僅是一個個好看、有趣的故事,而有著更多的寄望。他們醉心于語言文字構(gòu)筑的審美藝術(shù),更關(guān)心故事背后的人和世界。
文學(xué)作品作為精神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實質(zhì)上仍然是個體與個體、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溝通。這些個體同處于生活的漩渦之中,共同地經(jīng)受著時代、社會的變遷,既有表達(dá)自我、問詢時代的需求,又有尋找知音、求得共鳴的欲望。這是作家創(chuàng)作的情感起點,也是讀者閱讀的內(nèi)在動力。正是由于這一點,文學(xué)始終能夠做到“在場”,被人需要,鼓舞人、感動人甚至是改變?nèi)恕.?dāng)人工智能寫作加入到這個過程中,開始成為精神產(chǎn)品的開發(fā)者和提供者時,這種溝通還能有效展開嗎?這種溝通的價值還能得到維持嗎?
由人工智能寫作的文本,可能可以表現(xiàn)出人的種種情感,但卻無法將其灌注于作品中,使之成為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為它們是沒有血肉、沒有內(nèi)心生活、沒有情感反應(yīng)的物質(zhì)之身。在這種情況下,經(jīng)由作品來實現(xiàn)的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不是就要被迫中斷呢?這個時候,文學(xué)存在的根基是不是也就隨之被抽空了?面對人工智能寫作的文本,我們首先從情感上就很難接受,更不知道如何對之作出回應(yīng)。
文學(xué)批評是一種更高難度的文學(xué)閱讀,對守護文學(xué)殿堂、庇護文學(xué)事業(yè)健康發(fā)展,起著重要的瞭望作用,既監(jiān)督和指正各種不良風(fēng)氣,又對文學(xué)的發(fā)展方向作出及時的提醒和規(guī)劃。如果我們把專業(yè)文學(xué)研究者、文學(xué)批評家也當(dāng)作讀者的話,他們將如何從事和展開他們的工作呢?是該漠視,還是該一視同仁地對待?在以往文學(xué)契約的情形下,歷史形成的那些文學(xué)理論和文學(xué)批評方法,還有效嗎?他們的討論、觀點又將如何獲得回應(yīng)呢……可以說,人工智能寫作的發(fā)生和發(fā)展,使得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xué)生產(chǎn)、文學(xué)閱讀和文學(xué)批評都遭遇到了新的問題和挑戰(zhàn)。
溝通是人的一種本能性需求,文學(xué)作品是這種溝通的積極體現(xiàn)和高級形式。因此,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聯(lián)系是永恒的、穩(wěn)固的。如果人工智能寫作無法回應(yīng)和解決這個問題,那么,人工智能寫作自然就無法獲得讀者的青睞。沒有讀者,人工智能的寫作僅僅是為了炫技嗎?
結(jié)語
本文無意也無力對人工智能寫作的未來前景作出預(yù)言,但面對一個新的寫作模式的誕生,抱有懷疑之姿、審視之態(tài),應(yīng)當(dāng)是必要的。對技術(shù)的臣服,意味著作為主體的人對自我的主體性的放棄。顯然,這并非明智之舉。
人工智能寫作的出現(xiàn),也是一個契機,提醒我們重新回想文學(xué)寫作的一些基本事實,溫習(xí)寫作的意義和價值。從本體的角度來講,文學(xué)寫作也是一門古老的手藝。當(dāng)我們在紙質(zhì)媒介上摩挲那些浸染著寫作者情感和血淚的文字時,同時也就是在感受寫作者的寫作和思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獲得的溫暖,正是來自作者的饋贈。這也賦予了文學(xué)以神圣的光芒。
如果說人工智能寫作的發(fā)生有著不可遏制的技術(shù)性誘惑并已成為事實,那么我們所能做的不應(yīng)該只是情緒上的反感、抵觸。撤除了人的自我中心意識,以開放的態(tài)度面對它,或許才是揭開神秘面紗的有效之舉。當(dāng)人工智能寫作提供的文學(xué)經(jīng)驗、生命經(jīng)驗同樣能夠引發(fā)我們的情感共鳴時,我們還有必要拒絕人工智能寫作嗎?“也許可以預(yù)期,與AI寫作相攜而來的技術(shù)條件會在一定程度上剝離諸多強加于寫作個體之上的外在附屬,新的理論可能在舊秩序瓦解的空場上作出界限以內(nèi)的價值承諾。”這種價值承諾無疑會對AI寫作的倫理做出規(guī)約,從而生成新的文學(xué)契約,再度在人與文學(xué)之間建立起新的關(guān)系。
在對新的契約抱有期待和憧憬時,我們不應(yīng)忘記“文學(xué)是人學(xué)”這個樸素而深刻的信念,“一切藝術(shù),當(dāng)然也包括文學(xué)在內(nèi),它的最最基本的推動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類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種熱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如果將次視為文學(xué)存在的根由并不為過的話,那么,人工智能寫作同樣也應(yīng)遵從這個囑托,由此展開它的文學(xué)圖景。
注釋:
[1]可參見學(xué)術(shù)刊物《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10期相關(guān)內(nèi)容。圍繞“人工智能”主題,該刊物刊發(fā)了多篇論文,如陳鐘的《從人工智能本質(zhì)看未來的發(fā)展》、段偉文的《控制的危機與人工智能的未來情境》、王家范的《科技創(chuàng)造必須以人為本》、王飛躍的《新IT與新軸心時代:未來的起源與目標(biāo)》、何懷仁的《何以為人 人將何為——人工智能的未來挑戰(zhàn)》等。
[2]〔美〕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ǒng)[M].酈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4.
[3]出自德國學(xué)者尼可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的《藝術(shù)的媒體》,轉(zhuǎn)引自章國峰.藝術(shù)媒體學(xué):高科技時代的文藝存在形態(tài)[J].外國文學(xué)動態(tài),1997(01):8.
[4]單小曦.紙媒文學(xué)·數(shù)字文學(xué)·文藝學(xué)邊界[J].中州學(xué)刊,2010(2):249.
[5]可參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bc6dd0100ngqy.html.
[6]〔美〕勒內(nèi)·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xué)理論[M].劉象愚等譯,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0:71.
[7]童慶炳主編.文學(xué)理論教程(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17、263.
[8]何懷仁.何以為人 人將何為——人工智能的未來挑戰(zhàn)[J].探索與爭鳴,2017(10):32.
[9]〔美〕凡勃倫.有閑階級論[M].甘平譯,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14:123.
[10]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217.
[11]南帆主編.文學(xué)理論新讀本[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21.
[12]出自美國文論家喬納森·卡勒的《文學(xué)能力》,轉(zhuǎn)引自朱立元主編.當(dāng)代西方文藝?yán)碚摚ǖ谌妫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4:207.
[13]楊俊蕾.機器,技術(shù)與AI寫作的自反性[J].學(xué)術(shù)論壇,2018(2):13.
[14]錢谷融.文學(xué)是人學(xu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