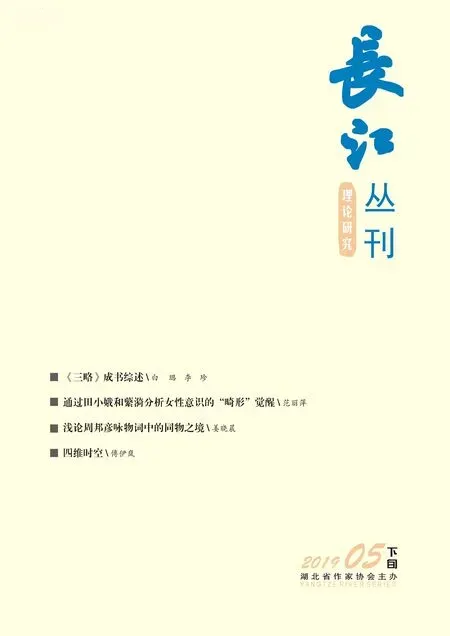淺析漢代儒家的倫理自然觀
■
一直以來,受到《周易》哲學理論思維模式的影響,從人與自然如何相處模式入手來展開對漢代儒家自然觀、倫理觀、道德觀的論述,是一種比較普遍的思路。老子的《道德經》中說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一天人合一自然觀,也是儒家探究天地之間生成、求索天人之間關系的奠基之石。于此基礎上衍生出了西漢的天人感應論以及氣本論。
一、儒家自然觀源自道家但不同于道家
儒家倫理自然觀的原始雛形最早可見于春秋時代,主旨在于天意于民,這是與道家思想不相同之處。雖然春秋時期,各個諸侯國仍以祝史祭祀,以求鬼神用饗、國受其福,但是在天人合一關系上,也逐漸開始了自我的覺醒和理解神之護佑與德之施政之間的關聯:“其適遇淫君…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左傳·昭公·昭公二十年》之外,在曾子記載中曾有所闡述。我們現代所能接觸的《曾子》記載,雖然也是由曾子轉述的孔子之言:“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西漢時期的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則是把儒家人性哲學與天地自然觀融合得最完整、滲透得最出色的劃時代著作,再聯系《左傳》之中大規模對應事例記載的易卦占筮,就大致形成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之論,也就是我們現代一直在流傳的認為儒術來源于儒家承天地、順陰陽的制義之禮的派生依據,自此凝聚而成了儒家最經典的自然倫理大觀。
二、天人一體是漢代儒家自然倫理觀構建的主要內容
董仲舒認為:“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為人者天。于是,依據這一推理之論,在道法自然大觀的基石之上,逐步延展而成了天人合一一體之論,用儒家最經典之論述替代道家自然于法之大道進行完善,極大程度上解釋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將天地萬物之性與人性之間的感應,推理衍生出一種互通互融感應,從而進一步總結出“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的天人合一關系的基礎論斷,本質上還是一種是自然、天象之偽命題,以此來論證孟子的民之為貴,社稷乃次之,君則為輕的理想之想法的正確性,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君不君,則臣不臣”的因與果倫常之理,“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同時入木三分地刻畫揭露了百姓心聲與自然之意之間的互為表里,從而為后世之人明確了“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的奉天之道之邏輯。這一基本道德準則就是所謂的“三綱五常”。
三、天子施仁政是漢朝儒學倫理觀的原則體現
根據“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的衍生理解,漢代儒家之學進一步推理出一個結論,即認為仁是天之性,人受命于天而須以為仁為任:“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在這里需要進一步重申的是:受命于天的人僅限于指的是天子,即天子為政必須施以仁,否則的話就不能承受天命而成為天子,因此《漢書》本傳記載杜欽曰:“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這里的“人之受命于天”既指的是其泛義——人類起源,又具象特定之以即指天子。若泛言人性仁貪之仁,可以人類概念;但如言具體為仁,則必是具象概念,即僅指天子。在人類歷史文化長河之中,孔子之論則側重于權力一面,而董仲舒之言論中則體現了責任的一面,此也是對孔子之言“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的補充;而天下百姓則因為“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于身”、“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所以能否為仁祛貪“在吾所以撫之耳”,即取決于天子為政的引導教化和帶動。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明明白白地指出儒家治道的核心之義是以求人人并育不害的中適,而實現中適的方法是為官在上位者應該以身釋義、達到“我將無我”之境界,以欲求先施、不欲勿施之心認同為民在下者合義之理,作為施行官理、上令的前置條件,如此上下方能篤于同理、悅于同道;所以,在貴一之專、監察之制的保障下,以確保各級、各項法規、政舉與價值觀和中適規范的相助不悖,以及各階層人才拔黜機制的尊德尚賢的前提下,天子率先篤義,以設教立俗、撫勸化民為主,輔以法刑之威,引導百姓遵禮以守義,進而明于中適之理;舉政先審民理之義而正法令之規,凡有不虞必先自反,視民如傷、用申哀恤、務盡平恕,涵養帶動百姓悅于中適之行,進而悟于中適之益,力求化淳而刑措,此之謂天子為政必仁也。脫離了中適而強調天子必仁,則會姑息為民在下者悖義、越常之理,就是屈君以縱臣、枉上以驕下的傾向。這是舜帝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文帝言“天下治亂,在予一人”之本質內涵,也是孔孟要求君王率先垂范而篤于中庸的法理化和形象化延伸。很顯然,先秦兩漢時期援入道家自然觀之目的不在于探索自然,而在于用人倫哲理詮釋自然之道,目的是借天之道來印證儒家哲學理論的正確與否,以有利于儒家治世之道的廣泛普及,則依然歸屬于倫常道理及大自然觀的圍欄之中。因此在對天地自然的認識與摸索上,“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多元開放與和諧互融,以及對未知的戒懼慎獨的理念持續得到一脈相承,生生不息。
四、漢儒倫理自然觀與道家的異與同
從淵源上來看,儒家自然觀雖然從道家處起源,但卻對其進行了重大的改良,首先來說,儒家認為天之道是自然之道的同時,更側重于其為仁道或者是更具備仁的特質與本性;與此同時,天地之道無法自行在人類社會中貫徹行走,因此天子受命于天,是主動順應天道執行天意的唯一責任人,人主能行天之道,則被天賦予統治天下萬民的使命,因此成為真命天子,而所謂“為人者天”、“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人一也”;在儒家倫理自然觀的范疇下,天之子則需兢兢業業地主動去作為、去擔當,以代替上天去管理整個天下、率民以仁、教化萬方。其次,西漢儒家也強調人倫治道領域以仁德為核心的中適之道,并認為這就是天道的體現。總體而言,把道家純任自然的無為之道,改良成主動篤行仁德中庸之道,是儒家之學援道而形成自身自然觀的最本質變化。
除了以上論述援天道而昭的原則以外,天人一體論的核心之義是指起源于春秋儒家承天地、順陰陽的制義之禮,并經過改良全面化而生成的對天地自然異象的解析應對之法,故稱之為“儒術”,這也是有史以來闡述得最為全面的天人互動關系理論。它起源于前人對自然知識的認知,并在此基礎之上,將天地萬物的概念進一步分類細分,其中包含日與月、山與川、陰與陽、四時與五行等等,幾乎涵蓋了自然界的所有領域,并認為在所有方方面面,人類的作為與天道能夠形成一種相互相通之天人感應。在這樣一種理念的引導之下,漢儒除了出仕和教育之外,還涌現出了一批可稱之為科學家的人物,如張衡、蔡倫,都是當世之大儒。但是正由于西漢儒家以倫理觀來解釋天地自然的這種描述過于細節化范圍過于寬廣而又漏洞百出的相互邏輯,往往在歷史實踐中使人們很容易找到它的謬誤,從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質疑之聲,這也是董仲舒埋下的一個隱患之處。于是到了東漢末年時期,世間就已經頻繁出現對儒家之學自然大觀的質疑,而逐漸傾向于向道家學說靠攏的各種嘗試,也就是提倡越名教、任自然、貴無為的魏晉玄學。
注釋:
①陳鼓應.老子注釋及評介[M].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
②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華書局,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