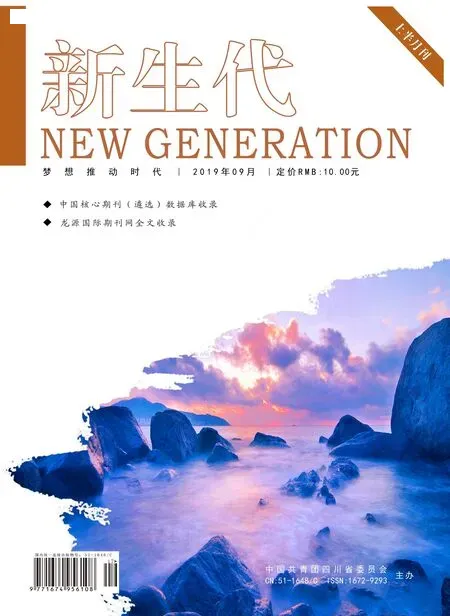宋代理學的特點及其對宋代文化的影響
宋蔚菡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四川省成都市 610072
1 宋代理學概覽
宋代是我國繼戰國之后在哲學發展史上又一個繁盛的時代。理學作為宋代哲學的最高成就,不僅影響了后世中國,還對周圍國家的文化發展和價值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之功。
理學的產生來自于自身的求新求變。從魏晉以來,隨著玄學的發展和佛教的初傳,儒學因為無法解決本源性的問題而受到詬病。而到了唐朝。統治者推崇道教和佛教更讓儒學發展難以為繼。于是,在宋代,儒學家們開始對于傳統儒學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立足自身的基礎上糅合佛教和道教,對自身的理論體系進行了新的詮釋,創立了理學,亦稱道學,在近代也被研究者稱之為新儒學。
2 宋代理學的突出特點
2.1 價值觀念本體化
對于世界的思考,在宋代開始逐漸深入起來,對于世界的本體論發展,雖然理學內部有一些不同的說辭,但是都對于彼岸世界和人格神表示否定。理學將理和氣作為世界的起源,是一種典型的客觀唯心主義。這讓儒家學說填補了自己的一個弱點,從此有了自己的理論基點。也讓后世的理論研究有了基點和著力點。也讓理學有了和佛教及道教抗衡的基本。本體化是體系形成的開始,之前的儒學體系對于類似“什么是天地”“生命的終極意義”上避而不談雖然可以看成是儒家學說的歷史局限性,但是不進行哲學化的改造,他極有可能在后世發展中被佛教或者是道教所取代,不再具有社會主流價值體系的地位。
2.2 思辨性特點
正如概覽部分所言,宋代的理學家們開始逐漸認識到,佛教和道教的壓力不容小覷。而這其中來自于儒學的內因占有很大的比例。儒學在剛開始創立的時候,僅僅是一些教條和倫理框架。孔子自己也幾乎沒有談及到“性和天道”。所以如何論證儒家思想在本體論角度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成為了當時儒學家面對的共同問題。孔子之后的諸多儒學家雖然都給出了自己的論證思路,但是都無法抗衡鼎盛期道教和佛教。這其中,孟子通過他的“四端”學說對于儒家的人性本善進行了論證。荀子通過性偽說對于人性本惡進行了論證。而到了董仲舒這里,已經步入歧途,將儒學當成了神學,發明了陰陽五行。這些論證要么是“不備”(不夠細致和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表述錯誤混亂不堪,如荀子與揚雄)。
如何建構起具有思辨性的儒家體系,理學家們在道教和佛教的思想中汲取了一些養分,在借鑒它們的哲學本體論的基礎上,同時積極尋找在傳統儒學體系中能夠用來構筑理學的傳統儒學零件。比《周易》中的道器觀,孔子學說當的“仁”學,《孟子》與《中庸》中對于“天”和“性”兩個問題的多方面闡述和探討。理學家們利用這些理念重新構建了具有思辨性的新儒學。傳統意義上的道德信條式的儒學經過這一輪改造,徹底脫胎換骨,成為了形而上的哲學理論體系。也成就了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一個高峰。體現了理學家們善于融合再造的哲學智慧。
3 宋代理學對于宋文化的多方位影響
3.1 社會生活的進步
儒學到了宋代之后,有了一個更為跨越式的發展,它不再是象牙塔中的學問,更多的方面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理學作為文人士大夫基本的價值觀念,在有宋一朝不斷落地,到南宋時已經成為影響全國的價值理論,它對于民眾的引導作用是非常明顯的。理學大儒朱熹在他的著作理學《家禮》中就有對于日常生活需要遵守的原則和禮數,這對于當時宋朝的社會文化生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家禮》將日常生活中的原則分成通禮,冠,昏,喪和祭祀五個部分。在充分融合當時社會中的基本生活習俗的基礎上,固化了生活禮儀,不僅對于當時的社會影響深遠,從今天的社會當中,我們依然能夠看到這些禮儀的影子。到了南宋晚期,理學完全成為了中國的正統思想。
提起理學,人們往往想到的第一句話就是“存天理滅人欲”,批判理學的人往往將其兇惡化,成為理學不可饒恕的信條。不可否認這種價值觀對于人性的打壓是非常嚴重的。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將其理解為完全限制作為一個人的自由,這樣的理解就是斷章取義、貽笑大方了。這里的“人欲”主要是指超過基本需求的人的欲望,而不是人的所有欲望,這里也可以認為是天理,其實說白了就是欲望要適度,要是胃口太大,人心不足蛇吞象,最后是害人害己。中國在此之前就已經有了中庸的說法,但是中庸這樣的主觀意識的名詞放在客觀唯心的理商,不得不說是儒學自身的一種進步。而這也就進一步影響到后世社會中,做事不能太過于追求過分的欲望,恰到好處即可。在我們現在看到的宋代官窯出土的瓷器中,宋瓷往往是溫潤如玉,并沒有添加華麗的紋路,和之后的清朝晚期瓷器在風格上有著明顯的不同,凸顯出一種古樸和極簡主義,這不僅是當時宋朝人文士大夫的追求,甚至影響到了遙遠的日本文化。
3.2 教育的興起和社會風氣的維護
宋朝是屬于文人士大夫的黃金時期,而之所以是這樣的局面,除了建國伊始確定的“重文輕武”政策,對于可能出現的軍人奪權或者割據政權的情況,在頂層設計上進行了嚴密設計。另外很大的原因其實來源于整個社會風氣對于知識的尊重和維護。在宋朝之前,天下強調皇帝的治統,而到了宋代之后,國家的統治不僅僅是治統,更重要的還有道統,而所謂道統落實到個體上來看就是文人士大夫的統治,再說的具體一些就是學習過儒家學問的文人士大夫的統治,這是宋代儒學對于社會教育風氣的影響和起點。“道統”和“治統”相結合的政治構建理念深深影響到了宋朝的政治基因,更為宋朝社會注入了重視教育、興辦教育的文化基因。
然而宋朝的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官辦學校的增長速度,為了適應這種教育風氣的日漸旺盛,各種私人辦學力量出現,其最主要的代表就是各種講學書院的發展。書院作為和官學不同的新的社會文化力量,是官學的一種重要補充。而正是這種講學書院,給理學發展提供了完美的發展和傳播平臺。他們轉而抨擊管辦教育的功利性,認為其將治學的目的指向科舉是錯誤的,而是應該為了實現自己的某種報復和理想。也正是因為理學的傳播需要,整個南宋成為了中國書院史上的高峰,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取代了官學,成為當時社會當中最主要的教育機構之一。
書院,唐代的時候就開始出現。在玄宗朝,書院僅僅是官方修書和藏書的地方。而到了宋初,書院的性質產生了重大的變化,成為了宣揚理學的講學之地,在這一階段形成了著名的六大書院,分別是: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潭州的岳麓書院、河南應天府的睢陽書院、河南登豐的嵩陽書院、湖南衡陽的石鼓書院以及江寧茅山書院。肇始于宋初的岳麓書院在1194年得到朱熹的恢復。而在此之前的1179年,朱熹已經恢復了白鹿洞書院。之后朱熹多次在這兩個地方講學,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影響極大。這里也能夠清晰可見理學對于書院建設重大的推動作用。按照史料記載:北宋時期建立的書院僅有140所,而到了南宋,僅僅在江西一地就有書院160余所,按照各省方志的記載,兩宋書院有超過八成建成于南宋,足以證明南宋理學對于書院的推進和影響。
3.3 宋朝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形成
士大夫的稱呼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產生,他們是社會中知識分子和官僚的結合體。更可以說是傳統中國的精神支柱。士大夫的精神有人說就是文以載道。不管如何,到了宋朝,這種精神受到理學的影響不僅僅成為了士大夫階層的精神甚至成為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準則。這其中最著名的理學論斷莫過于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就回到了上文提及到的,學習的本質和追求并非應對科舉,更應該是實現自己開太平的政治理想和家國情懷。不管是崖山海戰的悲壯,還是文天祥的一片磁心,抑或是南宋之后歷朝歷代出現的悲壯之舉,都受到了理學精神的影響,可以說,理學塑造了中國的文人士大夫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整個中國的文化價值觀,是我們中國人心靈家園的原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