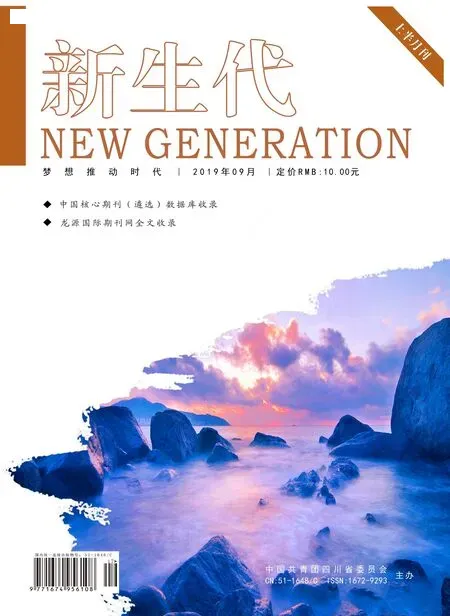《湖心亭看雪》的情懷與境界
譚思琪 湖南師范大學 湖南長沙 410000
張岱,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名維城,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天孫,別號蝶庵居士,晚號六休居士。是晚明時期的文學家、史學家。張岱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末清初這一特殊的時代節點,特殊的時代背景導致張岱人生前后階段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張岱生于官宦之家,祖上都是名士大儒,精通文史哲等各方面的知識。而張岱更是從幼年時期就表現出絕佳的文學天賦和聰明才智,被舅父贊為“今之江淹”。然而,這樣一個天賦異稟的張岱卻機緣巧合之下久不得仕,所以,青年時期的張岱縱情山水、游戲人間,他在《自為墓志銘》中說自己“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青年的張岱是一個怎樣的生活與人生狀態。然而,明王朝滅亡以后,他的人格氣質卻也隨之一變,從他的小品文《湖心亭看雪》中,我們便可窺知他的情懷與境界。
一、明朝遺民的家國情懷
明朝滅亡后,張岱在《石匱書》說自己“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發入山,駴駴為野人【1】”,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張岱的生活狀態隨著國家政權的變更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原先的紈绔子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懷著對故國的熱忱流離失所的文人。《湖心亭看雪》開篇交代時間和地點“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2】”從時間上我們首先能看得到的是張岱對明王朝政權的忠心,這種歸屬感是刻入文人靈魂的,以至于在明朝滅亡之后再去創作,還依舊沿用了明朝的年號。同樣的,張岱在這里執拗的使用明朝的紀年,也是在向世人,包括向清王朝展現一種堅定的姿態,一種舊朝遺民不屈的愛國忠心。
同樣的,西湖這個地點對于張岱來說也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在《西湖夢尋》中,張岱寫道:“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3】”西湖對于張岱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文化意象,在他鮮衣怒馬的前半生中,西湖給他留下了無數美好的印象。可以說某種意義上說,西湖承載的是他的過去,是已經滅亡的明王朝,是他優越尊貴的家庭背景。所以,此時面對國破家亡的現狀,張岱再面對西湖之時,生發出濃烈的故國之思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文人雅士的魏晉情懷
明朝文化專制嚴重,文人不再像前朝那樣敢于發聲,一切文化走向都要以封建統治階級的意向為標準。這就導致了許多文人開始反諸于心,注重心靈的自由和內在人格的修養。再加之理學和心學的影響,反觀自身追求性情成了主流,這儼然和魏晉時期的人格追求不謀而合。張岱一身才華,自然向往魏晉時期的風流名士,他的行為和價值觀也受到了他們的影響,追求的是高于世俗追求的清淡雅致和率性自然。顯然,他對于西湖的欣賞也是基于此而生發出來的。《湖心亭看雪》中,首先我們看到的是張岱選在了“大雪三日”后“獨往湖心亭看雪”,避開了通常選擇的好時節、好天氣,而這樣一種孤高、遠離凡俗的姿態正是他身上魏晉情懷的體現。他曾言西湖是“曲中名妓”【3】,乍看似乎有些唐突,然其用意并不是貶低西湖的審美價值,而是認為世俗大眾的喧鬧是對西湖的褻瀆。所以說,張岱這種文人雅士的瀟灑風度,完全是率性而為的,以自己的適情為依歸,可謂情之所至,即是目的。張岱深得魏晉風韻,心與物化,境由心生,注重審美主體的情感體驗,冰雪覆蓋下的西湖山水都是他性情的外化,渺遠清凈的雪景成為他審美解悟的對象。
而《湖心亭看雪》中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字,“獨”。張岱說自己是“獨往湖心亭看雪”,而通過后文我們可以了解到,張岱似乎并非孤身一人,他還有舟子這般隨從相伴。可是張岱卻選用了一個“獨”字,我想這其中恐怕是詩人孤獨心境的體現,也就是說雖然有仆從,卻沒有和自己志趣相合之人。而魏晉時期對于性情相投的友情也是極為重視的,晉人雖超,未能忘情,所謂“情之所鐘,正在我輩”(王戎語),是哀樂過人,不同流俗。尤以對于朋友之愛,里面富有人格美的傾慕。從這一點上,張岱在《湖心亭看雪》中的確是體現了他對魏晉名士的傾慕以及由此對他本身造成的性情意趣的深刻影響。
三、滄海蜉蝣的人生境界
張岱寫景,渾然一體,在目光的轉換和量詞的選用上凸顯了他靜觀宇宙感于內心的人生境界。“霧凇沆碭,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2】”作者眼中的雪湖首先是一個整體的印象,天、云、山、水混為一體,仿佛天地初生是混沌的境界。這給了讀者一個鮮明的整體印象,視線之內一片白茫茫。而就在這樣虛無蒼涼的背景之中,視線卻突然有了焦點,遠處的一痕長堤,一點湖心亭,這是作者的目光所及,而下句主體忽然一轉,“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這顯然是從一個他者,或者說是從宇宙的視角去看作者。從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作者的心靈已經超脫了肉體的局限,以浩大的宇宙為基點俯視自身,得到了一種“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的境界。人的渺小短暫和自然宇宙的偉大永恒也就驟然間生發了出來。
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曾把人生境界劃分為四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青年的張岱顯然處于前幾個階段,然而,國家和家庭的劇變讓他的人生體悟有了質的飛越,直指最后一重的“天地境界”。他前往湖心亭看雪,乾坤同白,在這白色的世界中,作者的這一點位于茫茫宇宙、皚皚上國之中,是一種回歸,也是一種伸展。回歸的是心靈,是作者在物我一體中所感悟到的自在本心和志趣,是性靈的極大抒發。伸展的是境界,在這樣“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的境遇之下,作者的心靈世界和宇宙混為一體,自宏大的宇宙層面看到了生命的短暫和人生的渺小,從而獲得深層的心靈安慰。
四、孤高純粹的冰雪人格
張岱曾在《西湖七月半》中諷刺了五類意不在賞月之人,足可看出作者對于游賞西湖有種近乎偏執的崇高感。西湖在作者心目中是一種清高的文化意象,一般的俗人看之只能是對其的玷污。所以張岱選擇在夜深人靜之時“獨往湖心亭看雪”。而在游湖中偶遇金陵人士,張岱的反應似乎并非像亭中金陵人士那樣“大喜”。“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從這些字句我們都可以看出,張岱對于湖上偶遇是持一種不甚歡喜的狀態的。并不是說作者遠離人群,不愿意與人交往,而是在張岱眼中,這樣不懂欣賞西湖之人只能是破壞西湖的意境,不足以作為與自己攜游之人。與之相比,作者更情愿獨自飲酒,與西湖相擁,與天地相融.從這一點看來,張岱所擁有的是一種遺世獨立的“冰雪人格”。
王國維《人間詞話》中言“一切景語皆情語”“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以當時張岱所處的社會環境和他的人生際遇際遇來看,對于雪湖近乎偏執的情感正是他心中空寂冷然,對清王朝白眼示之的心境的體現,而基于此則形成了張岱孤獨中帶著憂郁的“冰雪之氣”。可以說,雪湖獨游本身彰顯的便是張岱追求高雅、遺世獨立的人格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