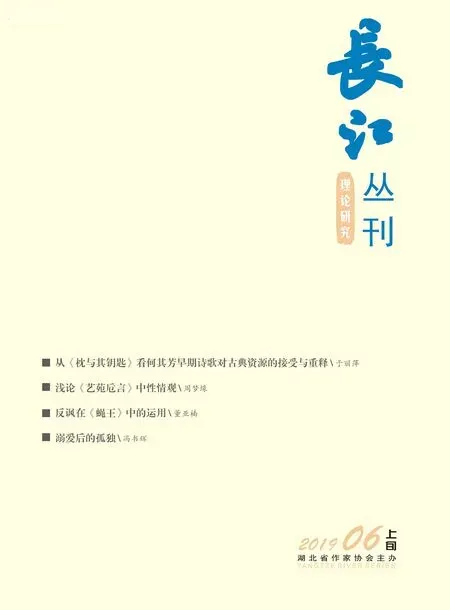概念遷移視域下的中式英語現象研究
■
近年來在關于語言遷移的研究中,“概念遷移”(conceptual transfer)成為這一領域內比較新的理論,其所關注的重點在于語言遷移現象與人的認知/思維之間的關系,屬于二語習得研究領域內的語言相對論研究。筆者對這一課題感興趣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大學英語課堂及考試中,學生時常會暴露明顯的“中式英語”用法,而概念遷移則很好地解釋了中式英語產生的過程。通過對概念遷移理論的理解和剖析,進一步了解中式英語的產生原因及種類,教師才能在課堂上游刃有余地引導學生規避中式英語的表達,從而習得地道的英語。
一、語言遷移中的概念遷移
“概念遷移”最早由Pavelenko于1998年在向美國應用語言學會西雅圖年會遞交的論文《SLA and acculturation: Conceptual transfer in L2 learners narratives》中首次使用。這種研究視角也更關注作為發話者主體的意識層次。“概念”一詞是指對一類基本相同或相似事物的心理表征,它通過各種感官獲得的多個意象(image)、印象(impression)或意象圖式(image schemas)依據對某一特定概念的原型性和代表性構成。在同一篇論文中,作者還介紹了由此而延伸出的另一個概念,即“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指的是發生在人腦中的認知過程,是對集郵概念的激活,是個體參與世界活動的基本方式,具有動態性、互動性、圖式性和想象性等特征。
對于“概念遷移”的研究在西方比較盛行,但是在中國的研究還不是很多。國內的研究自2012年后才開始增多。其中劉永兵和張會平兩位學者除了在引介這一概念之外,還結合中文的語言文化特點提出了“二語學習概念遷移理論框架”。在這個理論框架下,他們主要關注三個維度,即“語言文化概念”、“二語學習過程”和“中介語形式層面的表征”。雖然語言能力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但是語言對于學習者的智力、認知等具有一定的影響性,那么這種已經建立起來的認知,反過來會影響對于新的語言的使用。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語言與文化緊密相連,以語言為描述基礎的文化、文明等,也隨著學習者對母語的掌握而進入學習者的意識深處,這自然也就包含了詞匯、語法、語篇與隱喻等概念系統。這也即是理論框架中所說的語言文化概念。在第二維度中,他們認為二語學習者在一定的條件下能夠激活母語中的概念范疇系統,從而發生遷移現象。這種遷移可能并不只停留在語言的形式層面和意義層面,只有在其到達了認知概念的底層,這樣才能被稱為概念遷移。比如在他們的研究中所舉的例子,漢語的“學習”與英語的“study”、“learn”都可對譯,但對于英語世界來說,兩個詞的意義并不相同。漢語母語者在學習兩個詞匯時,很難短時間內區分清楚兩個詞之間的不同內涵,因此學習者傾向于將漢語“學習”的概念遷移至英語學習之中,在語言表層方面的表現即是study與learn的自由替換。第三個遷移維度體現在中介語形式層面表征之上,包含了詞匯、語法、語篇等層面。
當然,在確認概念遷移的時候,不可隨意將語言遷移現象稱為概念遷移。Scott Jarvis認為,缺乏足夠證據或者使用傳統的語義和結構分析能夠說得通的跨語言影響案例說成是概念遷移。在同一篇論文中,Jarvis指出,傳統的跨語言影響研究關注的是語言系統是如何影響人們去使用另一種語言的,但是這樣的研究目的已經超出了語言相對論(language relativity)與概念遷移的研究范圍。他將“概念遷移”描述為一個連續體(continuum),這個連續體的意義在于傳統的跨語言影響研究和語言相對論研究聯系在一起,其所關注的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涉及不同語言背景的人們在相同條件下對概念意義表達是否不同;二、來自不同語言背景的學習者在目的語使用上的不同定式是否由不同的思維模式造成。觀察與測試的方法很有趣,基本是采用非文字行為(nonverbal behavior)進行檢測,比如觀察不同語言背景下的人在使用目的語與目的語的母語者進行交流或者演講時所使用的語言形式。
二、概念遷移與中式英語的產生
語言的概念遷移大體分為兩種形式,即正遷移和負遷移。例如學生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若中文里的某些特征和概念與英文相對應或相似,那么此時中文作為母語對學習英語起到促進的積極作用,此為正遷移;然而,當學生在使用英語時受到母語的影響,生硬地把中文的句法和語言習慣套用進英語中,對學習英語產生了干擾、阻礙等消極作用,此為負遷移。中式英語就是中文對英語學習者產生負遷移的產物。
中式英語,顧名思義就是不地道的、具有中文特色的英語表達。李文中認為,中式英語就是中國人在使用英語的過程中,由于受到母語文化和習慣的影響和干擾,生搬硬套中文的句法和規則,從而創造出一些不符合英文表達習慣的、畸形的英語。從概念遷移的視角來看,中式英語就是學習者在英語學習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把漢語的形式、意義、甚至是概念直接遷移到英語中,形成符合漢語表達習慣的英語語句。在麗江著名5A級景區玉龍雪山的觀光巴士上,一句溫馨提示“頭手請勿伸出窗外”被翻譯成“Please do not out of the window first hand”,其中的“頭手”竟然被生硬地直譯成典型的中式英語“first hand”。值得注意的是,類似的中式英語現象不僅頻繁出現在各大旅游景點,既誤導外國游客,又破壞中國形象;在大學英語課上也屢次被學生使用,因而引起了筆者的關注。以上例子足以說明漢語思維對英語學習者起到負遷移的作用,這種負遷移直接導致了中式英語的出現。充分了解中式英語的常見類型能夠幫助教師快速尋找對策,從而更好地引導學生規避中式英語的用法、甄別自身英語表達中的錯誤。
三、中式英語的類型
(一)詞匯混搭
由于中英文屬于完全不同的兩種語系,英語學習者在學習的初期階段經常會受到漢語思維的固有影響,出現套用母語知識來進行英語表達的現象。詞匯搭配混亂、不符合英語習慣的用法也時有發生。在一次期末考試中,多數學生把“在網上”表達為in the Internet,使用了錯誤的介詞搭配,正確的用法應該是on the Internet。在中文里,我們有“看電影”、“看書”、“她看起來很幸福”等表達,使用的動詞都是“看”。當學生在翻譯這些短語時,很容易把“看”聯想到watch或look,如look movie、watch book等,這些都是直接把漢語搭配習慣遷移到英語中的結果,正確的用法應該是watch movie,read book和she looks happy。再比如“刷微博”的意思是一直刷新微博頁面,地道的表達可以是“I’m on Weibo”或者“keep updating Weibo pages”。但是由于在中文中“刷微博”和“刷牙”使用的是同一個動詞“刷”,一些同學理所當然地認為“刷微博”就是“brush Weibo”,中式英語由此產生。
(二)句法錯誤
漢語和英語的語法關系也完全不同,漢語語法是由詞序或語法助詞來表示,英語語法則是通過詞綴或單詞內部的形態變化來表示。當英語學習者在使用英語句法遇到困難時,他們就會本能地將中文句法遷移到英語中去。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學英語課堂上,對于句子“我非常喜歡吃冰激凌”,多數學生都會翻譯成I very like eating ice cream。這個翻譯完全是受中文語序的影響,地道的表達應該是I like eating ice cream very much。再比如“我明天要去上海迪士尼”,個別學生會完全按照中文排列習慣把英文翻譯成“I tomorrow will go to Shanghai Disneyland”,正確的句子應該是“I will go to Shanghai Disneyland tomorrow”或“tomorrow I will go to Shanghai Disneyland”。
(三)詞性錯亂
英文中有很多單詞具有一詞多義或不同詞性的情況,這在中文里很少出現,因此英語學習者在初期經常會混淆詞性,把名詞錯當動詞使用,或是把形容詞當副詞使用。比如在作文練習中,很多學生使用了諸如loss my key,I’m worry about等的用法,把名詞loss當成動詞lose使用,把動詞worry當成形容詞worried使用。可見學習者受到母語的影響往往忽略了其中的差別,因此會出現詞性混亂的錯誤。
四、規避中式英語的方法
為了減小母語對英語學習者的影響,把母語的負遷移作用降到最低,筆者認為首先英語學習者應該養成用英語思維思考問題的習慣,讓自己時刻浸潤在英語的原聲語言環境中。多與外國人溝通交流,多聽、多說、多讀、多練。學習一門語言不是閉門造車,只有大量輸入地道的英語表達,才能在遇到中式英語的時候快速識別出錯誤的用法。其次,英語學習者要通過多閱讀英文原版書籍、雜志或英語電影等方式,加深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學習語言的本質其實是學習語言背后的文化。通過對西方文化的學習,進一步加深對英語思維方式的理解和認同,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擺脫中式思維。最后,通過對“概念遷移”的研究,教師在課堂上也要有針對性地把握教學的重點。通過對中國人的認知特點、中英文語言差別的研究,挖掘教材中的相關內容,設計互動教學環節,有意識地引導學生規避中式英語。
五、結語
中式英語在詞匯、句法、詞性等方面的錯誤用法都是母語負遷移的產物,其根本原因在于英語學習者受母語認知概念的影響,在英語中生搬硬套漢語句法規則造成的。為了擺脫中式英語的困擾、掌握地道的英語表達,英語學習者要充分了解中西方文化語言差異、努力營造目的語語言環境,培養英語思維的慣性;與此同時,教師在英語課堂上也要承擔起引導、糾錯的任務,以期達到教學相長、科研反哺教學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