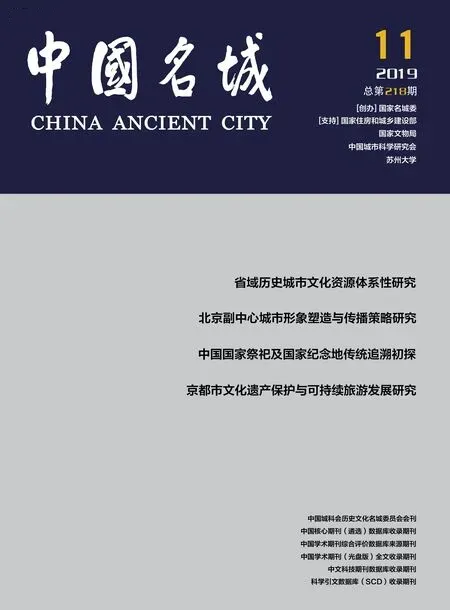街市廣場與寺觀園林:隋唐長安城公共空間的衍化與拓展
郝鵬展
公共空間指一般社會成員均可自由進入并不受約束的進行正常活動的地方場所,是地理學(xué)概念,多用于社會文化地理學(xué)。狹義的公共空間指城市居民日常神生活和社會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間,包括街道、廣場、公園等場地;廣義上講,公共空間不僅僅是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進入空間的人們,以及展現(xiàn)在空間上的廣泛參與、交流與互動。城市公共空間是指城市中在建筑實體之間存在著的開放空間實體,是城市居民進行公共交往,舉行各種活動的開放性場所,其目的是為廣大公眾服務(wù),從根本上說,城市公共空間是市民社會生活的場所,是城市多元文化的載體。
近年來,城市社會學(xué)和城市文化傳播學(xué)的發(fā)展,特別是對城市公共場域的關(guān)注,也促使了歷史城市社會中的城市公共空間的研究。長安城作為當(dāng)時隋唐帝國的首善之區(qū),其城市社會的演變和發(fā)展自然也成為了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注的焦點。如妹尾達彥、金子修一等對唐代長安城禮儀空間構(gòu)建和演變的研究[1];榮新江從王宅到寺觀來探討唐代長安城公共空間的擴大和變遷[2];寧欣從城市經(jīng)濟與社會的角度對唐都城社會結(jié)構(gòu)的研究[3];張曉虹對唐長安城流行文化傳播的地域和等級的關(guān)注[4];還有王靜從社會史角度對唐長安新昌坊變遷的考察[5]等。這些研究使我們對隋唐長安城公共空間演變和社會交往有了更為細致的了解。
本文即在以上這些研究的基礎(chǔ)上,以長安城公共空間為主題進行論述,討論作為象征性和禮儀性為主旨的封閉的城市空間前提下,城市公共空間的衍化和層級結(jié)構(gòu)的形成,同時隨著王朝統(tǒng)治的既成事實和工商業(yè)的發(fā)達,城市空間構(gòu)造的變動和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對城市公共空間變化產(chǎn)生的影響。
1 長安城空間布局和管理制度對城市公共空間的影響和限制
唐長安城是在隋大興城的基礎(chǔ)上繼承而來,其規(guī)劃建設(shè)受到了以《周禮》國都模型為代表的禮制思想和《易經(jīng)》陰陽五行思想以及傳統(tǒng)的天文思想的影響,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和禁苑四部分,除外郭城外的其他三部分作為國家統(tǒng)治中心而有著十分嚴格的控制,并不對普通民眾開放,只有外郭城是所謂的“筑郭以衛(wèi)民”,為普通市民所居之地。但即便是普通市民居住的外郭城,由于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里坊制度,普通的市民也是不能自由出入。長安城的里坊可以分為三類,皇城以南、朱雀大街兩側(cè)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長500-590米、東西寬558-700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較大,南北長為500-590米、東西寬1020-1125米;宮城、皇城兩側(cè)的坊最大,南北長838米、東西寬1115米[6]。按照制度,這些坊是被高高的坊墻包圍著的[7]。
長安城的規(guī)劃和建設(shè)多以禮制為核心,追求對稱性和象征性以鞏固統(tǒng)治正統(tǒng)化并加以嚴格管理,沒有太多考慮城市居民生活對公共空間的需求。
從長安城空間布局來看,唐長安城建立之初,與皇城、宮城的面積相比,外郭城的面積較大。雖然表面上看,市民生活的空間占居了城市的較大面積,但是從實際生活的情況而言,并非如此。外郭城被高高的坊墻分割成了一個個的獨立區(qū)域,坊的四周,環(huán)筑有坊墻,彼此加以分割,從長安城的外觀上看,宛如大城市之中又套筑了許多小城,[8]每個坊之間并不能直接進行溝通和聯(lián)系。唐長安城外郭城的管理是多重制管理,一為行政管理系統(tǒng),由京兆府主管,下屬以朱雀街為分界線的萬年和長安兩縣;一為監(jiān)察治安管理體系,由御史臺和金吾衛(wèi)主管。[9]
坊門由專職門吏掌管,負責(zé)按時開關(guān),“長安城中百坊,坊皆有垣有門,門皆有守卒”[10]。坊有坊正、里正、保長進行管理,所謂“坊有墉,墉有門,捕亡奸偽,無所容足[11]”,街有街使、巡使、街鼓、街鋪、街亭等,“凡城門坊角,有武侯鋪,衛(wèi)士、獷騎分守,大城門百人,大鋪三十人,小城門一十人,小鋪五人”[12]。
在禁夜制度和門籍制度下,城門和坊門都會按時啟閉,“閉門鼓后,開門鼓前,有行者,皆為犯夜”,“違者,籉二十”[13]。每當(dāng)日落,城門、坊門、市門都會關(guān)閉,左右街使就分別率兵士巡街,實行戒嚴和宵禁[14]。沒有按時回到固定坊內(nèi)的市民,就會受到金吾衛(wèi)的盤問,甚至毆打,不能進城的民眾也只能在城外驛站或旅店住宿。
這種較為封閉的城市規(guī)劃理念和管理體系使城市的公共交往受到嚴格的限制,城市公共空間被忽略。隨著大明宮、興慶宮的興建引起城市空間結(jié)構(gòu)的變化,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成為城市發(fā)展的核心,城市象征性的禮儀空間向世俗化和功能化轉(zhuǎn)變的過程中,城市的公共交往空間也在隱性的發(fā)展,客觀上部分城市用地演變成了城市公共空間,形成了中國傳統(tǒng)城市典型的以城市廣場和寺觀園林為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間格局。
2 街市廣場的層級結(jié)構(gòu)與公共空間的形成
城市廣場是來源于西方城市建筑的概念,在嚴格意義上,中國傳統(tǒng)城市并無城市廣場。由于封建王權(quán)意識和禮制秩序等觀念占主導(dǎo)地位,使得宮殿、陵墓、宗廟等類型的建筑在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傳統(tǒng)城市特有的廟宇或殿堂的前廳、交通干道的節(jié)點等類似廣場的空間布局,而作為市民聚集交流的公共空間則相對呈隱性狀態(tài)發(fā)展著。[15]長安城也一樣形成了多處類城市廣場的空間布局,我們姑且稱只為街市廣場。
隋唐長安城的街市廣場可以劃分為兩種性質(zhì),開放性廣場與半開放性廣場。半開放性廣場往往由皇家禮儀主導(dǎo),通過嚴格的禮儀規(guī)范和等級差別,自上而下進行交流和傳播。如承天門、橫街與太極殿組成的半開放性廣場,又如大明宮含元殿、兩厥以及丹鳳門組成的廣場,這一類型廣場往往成為國家大典,重要外事活動的場所,與皇家威儀一致,秩序和規(guī)范嚴格,但參與度和受眾相對狹窄,主要集中在上層統(tǒng)治階層,對于廣大市民的日常交往而言,不能起到太大作用。
相反另外類型的街市廣場,即開放性的廣場,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公共交往的空間。如安福門廣場、延熹門廣場、朱雀門廣場、丹鳳門廣場等,都是圍繞城門、城內(nèi)交通干線、地標(biāo)性建筑等形成的城市結(jié)點,成為了城市公共交往的中心地區(qū)。在封閉的城市空間格局下,這些街市廣場逐漸衍生成為了居民所需求的公共空間,城市的各種節(jié)俗活動、商業(yè)活動,甚至一些政治活動都是圍繞這些城市公共空間展開的。如安福門樓、開遠門安福門街以及安福門橫街形成的安福門T字形廣場,因該地域既處于宮城、皇城和外郭城的節(jié)點,又是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干線,因此安福門廣場成為了宗教活動、節(jié)俗活動的重要空間場所,成為了皇帝、大臣以及普通民眾同時聚集的空間。
在太宗貞觀年間,“三藏自西域回,詔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設(shè)九部樂,迎經(jīng)像入寺,彩車凡千余輛,上御安福門觀之”[16]。這種以政府為主導(dǎo)“迎經(jīng)像”宗教行為,聲勢浩大,參與人數(shù)眾多,從開遠門入城,向東直達安福門外,皇帝在安福門樓上觀看,樓下彩車千輛,萬頭攢動,浩浩蕩蕩行進,這種壯觀的場面充分起到了公眾宣示效果,安福門廣場在這種宗教活動中充分起到了公共空間的作用。
懿宗咸通十四年春的“迎佛骨”活動,“其剪裁為幡為傘,約以萬隊。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士女瞻禮,僧徒道從。上御安福樓親自頂禮,……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各有差。……長安豪家競飾車服,駕肩彌路,四方攜老扶幼來觀者,莫不疏素以待恩福。……通衢間結(jié)彩為樓閣臺殿。或水銀以為池,金玉以為樹。競聚僧徒,廣設(shè)佛像,吹螺擊鈸,燈燭相繼……[17]”,這種寶帳彩棚夾道,士女僧道爭相瞻禮,豪家競飾車服,四方攜老扶幼,錦車載歌載舞的宏大場景,以官方的宗教意志帶動民間參與的活動,使得街道這個公眾開放區(qū)域成為了各個階層民眾的娛樂交往場所,安福門作為重要的城市結(jié)點,加之皇帝親臨觀禮,安福門廣場就成為了這種公共活動的重要空間。(圖1),長安城四次迎佛骨、迎經(jīng)像路線示意圖。
與安福門廣場空間作用相同,作為皇城的正門朱雀門廣場同樣起著城市公共空間的作用。朱雀門廣場處于都城禮儀軸線和都城經(jīng)濟中心軸線(金光門和春明門的東西橫街)交叉點,這里東西長150米、南北寬120米的約1.28公頃的長方形廣場[18]。加上,東西南北側(cè)大街,空間更大。如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斗聲樂[19]”。天門街即為朱雀街。又有唐代宗時,“京兆尹黎幹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舞于龍所”[20]。這種公共活動選擇在朱雀門街舉行,能充分利用朱雀門廣場寬闊的空間和交通要道人流容易聚集的特點,利用公共空間來達到宣示的效果。
其實,不同于安福門廣場的官方行為主導(dǎo),對于朱雀街廣場而言,更多的顯現(xiàn)出市民自發(fā)的組織利用公共空間的情況。如《李娃傳》中描寫的為了商業(yè)競爭,東肆將主人翁鄭生打造成長安城最有名氣的挽歌高手。鄭生就曾在朱雀街廣場與西肆進行比賽,當(dāng)天“士女大和會,聚至數(shù)萬”,“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21]”。
對于此點,日本學(xué)者妹尾達彥先生以李娃傳為中心述唐代后期的長安與傳奇小說時,已經(jīng)有所討論,其認為“要想在天門街尋找能夠展覽葬儀用品、舉行挽歌大賽、且能容納長安城數(shù)以萬計的觀眾的場所,首先應(yīng)想到城內(nèi)街衢中空間最廣的皇城南面一帶的廣場”[22]。關(guān)于在朱雀街廣場上東西兩市的公共空間的商業(yè)活動,除以上李娃傳有描述外,《樂府雜錄》亦有類似記載,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東西兩市利用這個時機“及斗聲樂”,都在朱雀街搭建彩樓,炫耀實力[23]。可見朱雀街廣場已經(jīng)成為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間之一,在人際交流、商業(yè)活動以及禮儀活動中起著重要作用。
3 寺觀園林的演變與公共空間的拓展
長安城除了不同層次市廣場為主的城市公共空間外,也會形成不同層次和級別的以園林為主要特色的隱性的城市公共空間,其對市民交往交流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這種隱性的城市公共空間有以國家行為建設(shè)的曲江等園林區(qū),也有由私宅和官府用地演變而來的寺觀園林,同時也存在一些達官貴人建設(shè)在長安城各處的亭子園林或無人看管閑置成公共娛樂場地的庭院。
私宅向寺觀轉(zhuǎn)變,為城市交往交流提供了許多公共空間,特別是王宅和公主宅第最為突出。隋代王宅數(shù)量不多,但規(guī)模宏大,因“京城南面闊遠,恐竟虛耗,乃使諸子并于南國立第[24]”,諸宅多分布在城內(nèi)西南部無人居住的坊中,如蜀王秀宅院在歸義坊、漢王諒宅院在昌明坊、秦王俊宅院在崇德坊,但由于其不在城市中心,不能和唐代王宅在城市中的地位和功能相比。唐代直到玄宗在城東北角建“十六王宅”之前,大量的王宅和公主宅第不再偏在城南空曠偏僻之地,而是位于宮城較近的坊中,處于城內(nèi)較繁華的地段。[25]如貞觀初晉王宅第占保寧坊一坊之地,甚至如太平公主還不止一處宅第[26]。原有的王宅和公主宅第的主要去向,就是改建為佛寺或道觀。如唐高祖通義坊西南隅舊宅“制度宏敞、以崇神祠,敬增靈祐,宜舍為尼寺,仍以興圣為名[27]”,改為興圣尼寺;保寧坊一坊之地本為唐太宗第九子晉王宅院,“顯慶元年,為太宗追福,立為觀[28]”;崇義坊招福寺為睿宗在藩舊居;[29]安定坊千福寺,本章懷太子宅,咸亨四年(673)舍宅為寺;[30]大業(yè)坊東南隅太平女冠觀,本為徐王元禮宅,后因太平公主出家于此改為觀;[31]開化坊的大薦福寺,本為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賜尚書左仆射蕭瑀為西園,瑀子銳尚襄城公主后為公主宅第,公主薨后又為英王宅。文明元年(684)高宗崩后立為大獻福寺,后改為薦福寺。[32]另有布政坊鎮(zhèn)國公波若寺、崇仁坊景龍觀、長樂坊大安國寺、崇業(yè)坊福唐寺、通義坊九華觀、親仁坊咸宜女冠觀、延福坊玉芝觀、崇業(yè)坊新昌觀、平康坊華封觀、宣陽坊東北隅奉慈觀等都為諸王或公主等私人宅第轉(zhuǎn)為寺觀,據(jù)馬文軍等人的統(tǒng)計私宅或官府用地轉(zhuǎn)變?yōu)樗掠^用地的有28處之多[33]。
私人宅第轉(zhuǎn)變?yōu)樗掠^后,這些城市空間從被包圍的私密空間轉(zhuǎn)變?yōu)樗掠^園林性質(zhì)的公共開放空間,其意義不僅在于主人的更換,更重要的意義在于為城市提供了大量布局精巧、環(huán)境優(yōu)美的向大眾開放的公共空間。如延康坊西南隅的西明寺,“本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宅。大業(yè)中,素子玄感被誅后沒官。武德初為萬春公主宅。貞觀中賜濮恭王泰。泰死后,官市之立寺[34]”,寺院“三百五十步,周圍數(shù)里,左右通衢,腹背廛落。青槐列其外,綠水亙其間,亹亹耽耽,都邑仁祠…廊殿樓臺,飛驚接漢,金鋪藻棟,炫目暉霞[35]”,面積廣闊,環(huán)境優(yōu)美。
又如崇仁坊西南隅長寧公主宅院,“盛加雕飾、朱樓綺閣,一時絕勝。又有山池別院,山谷虧蔽,勢若自然[36]”,甚至唐中宗游覽至此,“留連彌日,賦詩飲宴[37]”,可見其園林景致甚為精美,立為景龍觀后,從封閉的私人空間轉(zhuǎn)變?yōu)閷婇_放的公共空間,以至于“詞人名士,競?cè)胗钨p[38]”。蘇颋曾在詩中描寫道:昔日嘗聞公主第,今時變作列仙家。池傍坐客穿叢筿,樹下游人掃落花。雨雪長凝向函谷,山泉直似到流沙。君還洛邑分明記,此處同來閱歲華。[39]由詩文可見,原本只是聽聞的公主宅第,現(xiàn)今變成了仙家道觀,于是文人學(xué)士可以在其中約會,賞游山水,或者迎賓餞客,還有一些游客穿梭于彎曲的池畔,游園賞花。并且由于“北街當(dāng)皇城之景風(fēng)門,與尚書省選院最近,又與東市相連”,更成為“選人入京城無第宅者,多停憩此[40]”,可見其人流眾多,公共空間性質(zhì)顯著。
這種轉(zhuǎn)變?yōu)槌鞘刑峁┝嗣娣e可觀、景色幽麗的公共空間,這些區(qū)域不但成為公共的政治活動空間和公共的學(xué)術(shù)交流空間,同時也成為了城市大眾文化傳播空間和大眾娛樂空間[41],這些空間的出現(xiàn)成為了封閉的里坊結(jié)構(gòu)和嚴格的宵禁制度約束下城市公共空間交流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作為城市公共空間的寺觀園林,特別在中晚唐時期,成為了士子讀書、聚會、交往、游玩的場所[42]。長安作為科舉士子匯聚的地方,寺觀這種公共空間因為環(huán)境優(yōu)美、清靜幽雅,就成為了許多考生讀書學(xué)習(xí)的首選之地[43]。元和初,白居易就曾和元稹居住在永崇坊的華陽觀準備科舉考試。[44]這里“永崇里巷靜,華陽觀院幽。軒車不到處,滿地槐花秋”[45],正是讀書的好地方。文人也往往選擇寺院聚會,如“元和九年(814)春,予初成名,與同年生期于薦福寺,余與李德垂先至,憩西廂元鑒室。”[46]在坊里制度和夜禁制度下,文人學(xué)士在寺院中聚會,如若錯過坊門關(guān)閉之前回到自己居住的坊里,還可以在寺院中過夜,而不受夜禁制度的限制。白居易在做官后就曾因同友人交往游玩住宿在寺觀,“我與二三子,策名在京師。……沉沉道觀中,心賞期在茲。……置酒西廊下,待月杯行遲。……終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47]可見寺觀為文人甚至市民提供了一個環(huán)境優(yōu)雅、遠離世俗的公共交流空間。
當(dāng)然寺觀里經(jīng)常舉行的俗講和戲場都會吸引大量的市民百姓前往,這種喜聞樂見、簡單易懂的形式,為大眾文化傳播提供了絕好的公共空間。俗講的興盛導(dǎo)致了長安城出現(xiàn)了因俗講而盛名的僧人和寺觀。中晚唐金城坊會昌寺文溆的俗講最為有名,“城中俗講,此法師為第一”[48],“公為聚眾談?wù)f,…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著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diào),以為歌曲”[49],由于其俗講的名氣,甚至敬宗皇帝曾“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溆俗講”[50]。《入唐求法巡禮行紀》中對俗講也有詳細的記載,長安城左右街共有七寺開俗講,左街四處:崇仁坊資圣寺、祤善坊保壽寺、平康坊菩提寺和常樂坊景公寺;右街三處:金城坊會昌寺、懷德坊惠日寺和休祥坊崇福寺,還有道教俗講在崇仁坊玄真觀。[51]這些俗講的地點都集中在長安城較為繁華的中部、北部,客觀上為城市提供了多處公共空間,使封閉的坊里空間重新得到整合。
除了俗講外,唐長安城依托寺觀形成的戲場也是城市公共空間延伸和擴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長安戲場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52]。對于戲場在市民中的影響,最著名的要數(shù)萬壽公主不顧小叔子病危而仍前往慈恩寺戲場觀看表演的例子了[53]。關(guān)于圍繞慈恩寺大雁塔形成的城市公共空間和文化傳播,參見拙文[54]。可見長安城寺觀戲場吸引力之大,市民爭相觀看的公共空間影響力也可見一般。
除了城市廣場和寺觀園林外,長安里坊也有很多環(huán)境優(yōu)美的風(fēng)景小品,如園子、亭子、假山等,這些也成為城市公共空間的補充。這一現(xiàn)象得到了考古的印證,西安西郊中堡村出土的一套住宅模型,除八座房屋建筑外,還有八角亭和四角亭各一座和帶池塘綠地的假山。[55]長安除了有普通住宅的院子外,還有占地面積較大的名園,通常以權(quán)貴命名,如開化坊蕭瑀的西園、大通坊郭子儀園、昭行坊王昕園、新昌坊吏部尚書裴向宅竹園、豐邑坊李晟林園等。[56]在庭院中有許多山亭、池亭、山池、池院、池臺等各種景觀。[57]這些長安的私人景點如果設(shè)在宅第之內(nèi)應(yīng)歸主人所有,但不少景點卻是獨立于宅第而存在,其功能則有所不同。從《逸史》記載了一段關(guān)于在興化坊裴度池亭賣魚的故事[58]來看,名義上屬于宰相的私人池亭已經(jīng)起著公共場地的作用。據(jù)白居易的描述,此池亭景色秀麗,近山傍水,儼然是一作坊內(nèi)的公園。[59]安邑坊西“玉杯地”原為侍中馬燧宅院,唐德宗時入官為奉誠園。院內(nèi)屋木盡拆入內(nèi),一片凋零。從大量詩人作詩憑吊來看,該園也已變?yōu)楣灿螆@。[60]延康坊邠寧節(jié)度使馬璘池亭[61],主人死后入官。貞元后為群臣賜宴場所[62],成為由朝廷支配的坊中御園。
寺院園林空間己成了不分階級,不分貴賤市民同樂的場所,其經(jīng)常舉行俗講、戲場、法會、齋會,還有雜技、舞蹈表演以及設(shè)攤買賣等交易行為,儼然己成為當(dāng)時極為生動的“城市廣場”、“市民廣場”空間,[63]毫無疑問,這些空間結(jié)構(gòu)和屬性的改變,必將成為城市公共空間變遷和拓展的重要步驟,由私人宅院和官府用地演變成的寺觀園林已經(jīng)成為城市公共空間的重要部分。(圖2)
4 結(jié)論
隋唐長安城空間格局以封閉的里坊結(jié)構(gòu)為主,由于象天設(shè)地和繼承傳統(tǒng)的規(guī)劃理念以及夜禁、門籍、坊市等管理制度,作為國家的首都,長安城的空間規(guī)劃并沒有專門營造城市公共空間。
城市公共空間是市民生活、社會流動的必備空間,隨著城市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在封閉的里坊模式下,長安城逐漸自發(fā)構(gòu)建出層級分明、功能突出的城市公共空間體系。
長安城城市公共空間包括由城門、主要道路、地標(biāo)建筑組成的街市廣場,也包括大量的私人宅第和官府用地演化成寺觀園林為主的公共空間,同時還有獨立于宅第之外屬于公共空間性質(zhì)的園林、亭子、山水風(fēng)景小品,這些共同構(gòu)成了長安城特有的城市公共空間。
從公共空間的層次而言,街市廣場集中了皇帝、貴族、官員、文人學(xué)士以及各類市民,成為凝結(jié)社會不同階層的中心點,這類空間也構(gòu)成了城市公共空間中最突出的層級,不同層次的市民在此交往交流,不同特色的城市文化在此吸納融合。由各類私宅和官府用地逐漸演化而來的寺觀風(fēng)景園林成為了文人學(xué)士、市民百姓、宗教人士聚集和交往的據(jù)點,這一層次的公共空間雖沒有第一層次的公共空間那樣聲威浩大,但卻是更多的自發(fā)和自由,成為城市公共空間的第二層次。除此之外,散落在城市不同地點的園林亭子成為了公眾更為自由的交流場地,對以上兩個層次的公共空間起著重要的補充。
這些城市公共空間并不是固定不變的,會隨著城市空間結(jié)構(gòu)本身的變化而發(fā)生改變,同時也會隨著市民生活和城市文化的遷移而逐漸重新整合和拓展。關(guān)于此,由于遷移變化的情況較為復(fù)雜,容另文探討。
這些不同層次,不同特色規(guī)模的公共空間為長安城市民的交往和交流提供了重要舞臺,也為城市提供了生機和活力。以此為契入點,長安城不再是冷冰的里坊建筑和嚴整的街道,而是充滿活力的傳播交流之都市。豐富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社會生活就是在這種公共空間的舞臺上不斷的演繹和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