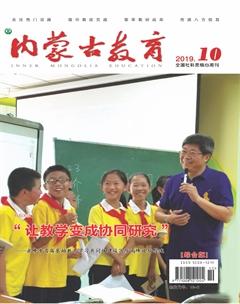怎樣讀懂課堂
叢智芳
2019年8月17日,上海市建平實驗中學程春雨老師,在克什克騰旗上了一節語文課——《背影》。程老師跟學生一起深入閱讀《背影》的時候,我坐在學生身邊,聚精會神地觀察和傾聽,試圖讀懂這節課堂。
先有教師的深度閱讀,才可能有學生的深度閱讀。
張華教授說,視角是世界本身的特性。讀《背影》,把視角定位在“父親”上,是一種視角,也是大多數人閱讀的視角。從這個視角看到的,是一個父親對兒子的愛,與一般父親并無二致,瑣碎而具體。
程春雨老師說,讀《背影》不在于讀“父親”,讀父親讀到父愛就結束了;而在于讀“我”,“我”眼中的父親,才是真實的父親。跟著程春雨老師,我們看到了朱自清的父親,獨一無二的單單屬于他自己的父親。在文本的深處,我們看到了平素看不到的地方,孩子們看到了即使是閱讀十遍,也看不到的東西:
比如,父親的反常——
說定不送,還是去送;
知道托茶房白托,還是囑咐照應;
自己買橘子很費事,還是自己去買。
對一個長大的兒子,對一個北京來往過兩三次的兒子,如此事無巨細,如此不放心,就見到一個前途未卜的父親對兒子的格外疼惜和照顧了。這次分別,是在剛辦完喪事、又要去謀事的家事慘淡之時,不同以往的分別,那盡力的疼惜和照顧里,就多了一層讓人落淚的哀傷了。
比如,兒子的反常——流下淚來,卻不讓父親看到;
趕父親走,卻尋找背影;
兩年不見,卻說什么時候能再見。
不過是尋常的父親的背影,為什么看到落淚,再也看不到了落淚,想起來還是落淚呢?當父與子面對面的時候,父親在兒子眼里是怎樣的呢?“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我心里暗笑他的迂”。背影意味著父與子空間距離的拉開,從買橘子,到消失在人群中不見,到兩年多不見,距離越來越遠,那個背影卻越來越分明,兒子與父親心理的距離越來越近。父親在信中向兒子訴說“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其言也哀,不復當年兒子面前的守護神形象。兩相對比,怎不潸然淚下。如再不見,恐再也見不到矣。
反常的背后,往往是這樣不同尋常的情感。
僅僅從這一個角度的深入,足見教師文本解讀的功力,這是教師深度閱讀的標志。先有教師的深度閱讀,才會有后來學生的深度閱讀。學生深度閱讀的標志,是那些從無到有的問題。
真正的挑戰性問題,是在深度學習中生長出來的。
學習共同體的課堂,設計挑戰性問題,是對所有老師的最大挑戰。對于《背影》這樣的散文,通常從這樣的問題入手:讀了課文你有什么感覺?最打動你的是什么?這是從讀者的感覺出發的閱讀。事實證明,感覺四通八達,因人而異,且常常因浮于淺表,而不能引導學生走向深入。我們也曾設計過這樣的問題:文中四次寫到作者落淚,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請結合相關語段談談你的理解。這是從作者情感出發的閱讀,無疑會把閱讀推向比較深入的部分,現在想來,聚焦是聚焦得很,學生回答問題般的閱讀,依然生硬了很多。
在程春雨老師的課堂上,我清晰地看到挑戰性問題的生長過程。它不是一個,也不是老師設計出來的,而是在深度學習中生長出來的。
沒錯,是生長!
學生大約是讀了很多遍課文了,程老師首先請他們分享一句最關鍵的、感受最深的話。同樣是從感受入手,卻沒止于感受,沒糾纏感受,而是從學生的感受中發現反常的問題,繼而引導學生深入文本,提出自己的問題,然后從問題入手,再次深入文本,解決感興趣的問題。
學生從之前的一點問題都沒有,到現在有了很多的問題,你清晰地看到閱讀的深度:
為什么父親說“他們去不好”,不好在哪里?
為什么詳細寫買橘子的過程呢?
為什么作者說自己“太聰明”了?
為什么他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流淚,也不想讓父親看到自己流淚?
為什么在淚光中,我看到的是父親的背影,而不是給我買橘子的具體情境?
這篇文章與祖母的死有什么關系嗎?
“托也是白托”,為什么要這樣說?
為什么祖母死后,家境變差了?
一個二十歲的小伙子,在短時間里為什么流了兩次淚?……
那個“為什么詳細寫買橘子的過程”的問題,就是我觀察的一個小女孩提出來的。之前交流感受時,她只是靜靜地傾聽,沒有發表什么觀點。等到老師希望每個人能提出一個問題時,她開始再次讀文,讀完一遍課文后,似乎沒有發現什么問題,又開始讀第二遍課文之后,她寫道:為什么要詳細描寫父親給兒子買橘子?并嘗試寫出自己的思考:因為父親很胖,到月臺必須穿過鐵道,必須要跳下去又爬上去。這樣寫更生動更形象。她顯然對問題和答案比較滿意,于是大膽地舉手說了自己的問題。這樣的閱讀,已經明顯帶有主動思考的意味了。
從問題出發的學習,也沒有止于問題的解決。全班交流的時候,在老師的追問中不斷生長出新的問題。
有孩子說:因為父親費很大的事給他買橘子,所以他落淚了。老師追問:你爸爸給你買橘子,你會哭嗎?
有孩子說:等父親的背影在來來往往的人群中消失,作者落淚,是不想讓父親看到。老師追問: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群,再也找不到了,“我”在干什么?
有孩子說:經歷這次分別,“我”改變了對父親的印象。老師追問:“我”內心的變化是什么?
我清清楚楚感受到教師追問的力量。那力量足以把學生以為的“是”,以為問題解決了的感嘆號,變成另外一個問號,越走越遠,一直到文章的深處。
直到下課,學生還有一肚子的問題,一臉疑惑,聽課的老師卻一臉滿足。這才是閱讀該有的樣子啊,課堂只是一個后勁十足的起點,每一個文字都似曾相識,每一個文字又充滿新鮮的誘惑。
從《背影》的觀課說開去。
我對程春雨老師說:“您這樣開放的課,只有教師對學科有深刻的理解,對文本有深度的閱讀,對兒童有真正的理解,才可能達到如此境界。”
他笑了笑說:“大約實踐了有5年的時間。”
上海市浦東教育發展研究院黃建初老師的話,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程春雨老師的執著。他說程老師是不怕失敗的人,他的課堂隨時都可以進去。這是何等的教學勇氣和研究精神!
由此我想到了幾個現象,以及這些現象讓我生出的憂慮和思考。
現象之一:欣喜激動,以為很易。學習共同體課堂的觀察,聚焦一個孩子或者一組孩子。觀察之后教師進行交流。我聽到很多教師的交流,談自己的觀察所得多,談自己的觀察產生的問題少。不少教師是第一次觀察課堂,有不一樣的發現是必然的,但僅一次發現就說確認什么,我覺得是十分可疑的。且不說學生是你不熟悉的,你認為的是,未必是。就是你的觀察,也還在學習過程中,未免隨意和想當然。不滿足于一次觀察,持續進行大量課例觀察的實踐,不只停留于課堂觀察,積極進行課堂實踐,持續反思,才會有令人信服的發現,才會有真正的專業成長。
現象之二:困惑叢生,以為太難。很多老師私下里有很多自己的聲音,比如,沒有小組長,小組怎么能有效交流?沒有問題設計,走到哪里算哪里,不是腳踩西瓜皮嗎?這樣的課能完成教學目標嗎?不得不說,這些問題實實在在困擾著老師。為什么不設小組長?我們可以問為什么要設小組長?從“好學生的視角”看到的同伴,還是平等的關系嗎?學習共同體的課堂,每一個孩子都是平等的關系,要保證每一個孩子的學習權,要相信每一個孩子的發言都是精彩的,教師都俯下身子傾聽學生,還有什么理由再設一個“小老師”呢?為什么要堅持讓學生自己提出問題?因為只有他們自己的問題,才是真實的問題,才是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才可能讓學習真實發生。怎樣界定教學目標?這涉及到怎么理解學習,學習不是惰性知識的灌輸,而是學生經驗和能力的不斷增長。在程老師的課堂上,學生向文本前進的每一步,都是真實地體驗著文字的力量,都在真實增長閱讀的能力,這不是語文的大目標嗎?走出“太好的教學”藩籬,走出“完整的課堂”藩籬,我們才能看到學生真實的學習和真實的成長。
現象之三:似曾相識,以為先行。我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話:跟我的課堂差不多,跟我的教學差不多,我早在多少年前就這樣做了。“差不多”先生的故事一再重演,正是我們教師走馬觀花淺表學習的突出表現。差不多,到底差了多少?差之毫厘,謬之千里。我認為你說的差不多,就是差了一點求真的科學精神,就是差了一點研究的深入精神,就是差了一點學習的謙虛態度。你真的傾聽過學生的聲音嗎?你真的對學科有深刻的理解嗎?你真的對兒童有深刻的理解嗎?你真的對教育對課程有深刻的理解嗎?當真正這樣問的時候,也許,我們會看到自己的差距,并找到前行的方向。
學習共同體的課堂意味著逐漸打破班級授課制。班級授課制的教學,從老師的已知出發,對老師而言,是安全的、安靜的、安心的。學習共同體的課堂,正好相反,從學生的未知出發,對學生而言,要有安全的、安心的、安靜的環境,常常意味著老師從自己的已知走向未知,意味著要把教學變成研究,通過傾聽兒童讀懂兒童,理解兒童的理解和不理解。這對教師形成了巨大的挑戰,挑戰自己的未知領域,比如兒童,比如問題,更大的未知領域,比如學科理解,比如傾聽能力,比如串聯能力等。只有勇于接受這種挑戰并身體力行的老師,才可能像程春雨老師一樣,走到教學的自由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