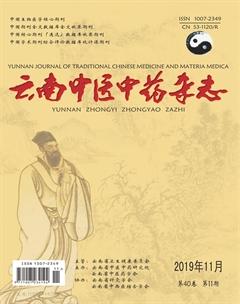基于《黃帝內經》脈瘀致眩理論探討高血壓血瘀體質關系及論治
徐麗麗 姜鈞文 李越
摘要:《靈樞》第十卷記載“脈不通則血不流”脈道不通,血流不暢,瘀血阻脈,脈不舒張亦無收縮,這一理論恰恰與現代醫學中高血壓病息息相關。在古代醫學中,高血壓病并無明確提出,多散見于“眩暈”、“頭痛”等疾病,其眩暈一詞始于《素問·至真大要論 》,它指出“諸風掉弦,皆屬于肝。”后代醫家受到廣泛的影響,金·劉完素又提出“風火”立論,元·朱丹溪提出“無痰不做眩”,明·張介賓指出“無虛不做眩”。而對古代著名醫家的總結,以上醫家認為多因風、痰、虛因素所致,而吾認為不論何因素,疾病發展中皆能致瘀,不論是否是單純的血瘀體質,最終所致脈瘀致眩。“瘀”貫穿于其高血壓的全過程。筆者對血瘀體質與高血壓的關系及論治進行了全面探討。
關鍵詞:高血壓;眩暈;脈瘀;血瘀體質
中圖分類號:R544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7-2349(2019)11-0018-04[FL(K8mm]
體質(Constitution)是中醫理論概念與西醫無關。“體”,指身體,“質”為性質、本質。所謂體質,就是機體因為臟腑、經絡、氣血、陰陽的盛衰偏頗而形成的素質特征[1]。血瘀體質:指絡、脈不通,血流不暢、瘀血內阻,或阻滯經絡的體質狀態,多于面、皮、舌、脈象的表現形式出現。所以辨別出體質分型有助于解讀疾病的發生和發展,為其后診治提供依據[2]。
高血壓(Hypertension)是一種發病率高但控制率低的心血管系統疾病,目前,95%以上的高血壓患者為原發性高血壓。原發性高血壓確切的病因病機尚未完全探明[3],臨床研究發現多與肥胖、睡眠過少、精神緊張、吸煙、長期高鹽高脂飲食甚至包括遺傳等因素有關,但尚未得到證實,缺乏證據[4]。在臨床表現上,體循環動脈壓升高為主[5]。血壓的存在,是為了保持血液正常的流動速度,血液正常的流動,是為了把血液中的各種養分及時的輸送給全身的細胞,提供細胞的養分,保持細胞的活力,維持生命的正常運轉,反過來,若長期血液的流動速度減慢了可誘發及促進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嚴重的腦血管意外、心肌梗死等病的形成,合并一種或多種并發癥是最終導致多臟器功能衰竭而死亡的原因,這也是臨床高血壓最危險的地方所在[6]。此時應用中醫辨證理論論治高血壓優勢更加顯著。在古代醫學中,高血壓病并無明確提出,多散見于“眩暈”、“頭痛”等疾病[7]。本文再豐富從“脈瘀致眩”的中醫理論,對血瘀體質進行探討,同時對方劑療效進行分析。為治療血瘀體質類型的高血壓提供充分的理論依據。
1血瘀體質是高血壓的病理基礎
在《黃帝內經》中就有認識:“脈不通則血不流”[8],《素問· 陰陽二十五人》“凝澀者……決而乃行”。楊仁齋在《仁齋直指方論》中首倡“瘀滯不行,皆能眩暈”[9]。如王清任在 《醫林改錯》 中指出:“元氣既虛……必停留而瘀”[10]。古代醫家都闡述著血行不暢或由血流瘀滯而導致血瘀,因而血瘀證與脈的功能受損的發生有密切相關,現代醫學與脈的功能受損也有密切的關系,脈的功能受損符合現代醫學血管內皮細胞的損傷,符合其病理生理學的認知,而利用血管內皮細胞損傷與脈道受損,瘀血內阻及導致瘀血體質的研究,闡述血瘀體質與高血壓的關系。血管內皮細胞(Cell endothelium)它是用來保護血管內外的一個屏障,讓血液順暢的運送到各個組織和臟器對此起到決定性的調節作用而去參與機體更多的生理功能[11]。如果血管內皮細胞損傷(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VEC)機體應激表達缺血、損傷狀態,刺激內皮(ECS)、平滑肌(SMC)等細胞分泌調節單核細胞通過趨化脂多糖(LPS)將THP-1細胞誘導為泡沫細胞的巨噬細胞,將巨噬細胞通過理化反應轉化為泡沫細胞,呈泡沫樣。細胞因子和促進斑塊破裂,血瘀通過內皮易于到達皮下間隙,釋放各種促炎性物質[12]。如C應蛋(C-reactiveprot ein,CRP)、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細胞介素 6(interleukin-6,IL-6)是高血壓病理生理過程中的重要炎性細胞介質等[13],同時,微小RNA(MicrooR-NA,miRNA)也參與細胞內皮損傷,如內皮中miR-NA-126可促進細胞內皮完整性及去探討與血管內皮的關系還有在探索[14],綜上促使早期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它的形成使管腔內膜不斷增厚,腔內變硬,血流阻力不斷增大,病理性惡性循環,動脈硬化進而導致血壓升高[15]。因此,減少巨噬細胞的浸潤可能減弱動脈粥樣硬化的發展和進展。
2“瘀”貫穿高血壓形成的全過程
由內經提出眩暈一詞起,歷代醫家就不斷總結、探究,最終總結出其因氣血虧虛、痰濁凝滯、肝腎陰虛致肝陽偏亢、化風生熱等原因所致,而這些原因在疾病的發展中皆能致血流不暢而導致瘀血阻脈凝滯,因此各種致病因素都可導致“脈瘀”,其具有廣泛性[16]。如《證治準繩》曰:“氣耗而血凝”,“夫氣陽也……氣弱而血死”,結合明·張仲景提出的“陽動而散,故化氣,陰靜而凝,故成形”[17]。可將世間萬物都以陰陽劃分,有行其性喜靜者為陰,無形其性喜動者為陽,則氣為陽,血為陰,動靜結合,氣推血則行,相反,陰陽失調,氣虛或血虛,氣血不暢則血瘀。因此不能供養頭竅,腦失所養故見眩暈。通過陰陽失調學說,可以解釋,肝腎陰虛,陰不涵陽,肝木失榮,肝陽升動太過所致的上實下虛證,致氣血逆亂,正常的氣血不能在脈道進行,可致血溢,氣不能固血,也可致血瘀,氣少不能行血,瘀滯經脈,其致眩暈。也可氣滯成郁日久傷肝化火,風陽上擾,熬傷津血致瘀,導致肝火上炎的實證眩暈。《素問》中提到“陽氣者……折壽而不彰”陽氣不足者氣也不足,氣虛不能行血,血流速度在脈道中減慢致瘀,陽氣其作用溫煦血液,陽氣不足則血寒,凝滯脈道致瘀。[18]如曾張山雷說:“痰涎積于……血必滯。”脈道受痰凝中阻,氣血凝滯,痰濁內生,影響三焦,痰瘀阻脈而致眩暈[19],現代醫學認為中醫的血瘀概念不僅僅是內皮細胞損傷(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VEC)的一個基礎,血瘀與血液中各種有形成分升高息息相關,血瘀使血管內血細胞聚集增加,引起血液流變學異常(hemorheology),使全血粘度升高,血液黏稠度改變,使病灶隨嚴重程度在細胞內外有不同脂質[20]。使之血脂(blood fat)也增高,脂紋形成,富含膽固醇酯的脂質核心和膽固醇結晶,動脈壁增厚,質地變硬,血管變窄,血流速度變慢但壓力增大,從而導致惡性循環[21]。血瘀日久可形成高血糖(Hyperglycemia)狀態,形成高糖利尿造成血液濃縮而黏稠血流緩慢循環障礙這一現象貫穿本病的始終[22],除此之外,如血漿中各種蛋白(如:FIB、globulin)升高,也包括代謝功能紊亂及微循環障礙有關[23]。高血壓的發生與這些病理因素的改變密不可分有著直接的影響。
3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祛瘀法”論治高血壓
目前,95%以上的高血壓患者為原發性高血壓。原發性高血壓確切的病因病機尚未完全探明,臨床研究發現多與肥胖、睡眠過少、精神緊張、吸煙、長期高鹽高脂飲食甚至包括遺傳等因素有關,但尚未得到證實,缺乏證據。所以從中醫上論證高血壓“瘀能致眩”更能受到廣泛關注。在古代醫學中,高血壓病多散見于“眩暈”、“頭痛”等疾病,無論是痰凝還是氣滯,無論是陽亢還是氣血虧虛,不管是什么病理因素,血瘀貫穿高血壓的全過程。所以在治療時,分清主次,要強調活血的運用。可見高血壓中醫證型正逐漸向血瘀證方向發展。在《內經》首次已提出治療時要“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平和”[24]。東·張仲景提出了蓄血論論治法,以桃核承氣湯為代表方,逐瘀瀉熱之功效,治療下焦蓄血證[25],通脈活血,恰好符合“脈不通而血不流”治療高血壓。這也給后世醫家帶來了深厚的影響,隨張仲景的影響之后,王清任提出了“補氣活血”、“逐瘀活血”兩大法則,補氣活血、通腑祛瘀等法的具體運用[26],而后代醫家在不同程度上也通過益氣、化痰、泄火、通絡等方劑配伍活血化瘀中藥也取到滿意療效。
31“活血”散瘀血瘀證不僅僅是病理因素,它也是其病因之一,我們經常會在后世醫家經驗中歸納總結,用于臨床,血府逐瘀湯、桃仁紅花煎、復方活血湯等劑用來活血化瘀,散瘀止痛,都得到了顯著的臨床療效。在丁宇煒[27]用血府逐瘀湯加減151例療效的實驗中,以天麻鉤藤飲作為對照,通過辨證分型取151例血瘀的高血壓患者并采用隨機分組,去觀察2組血壓的變化情況,結果提示臨床癥狀總積分值治療后改善60%-89%,臨床癥狀明顯緩解,差異有顯著性意義,其實驗室檢查有所改善。臨床理化顯示血瘀證導致的高血壓,主要因血黏度增高為主,而血府逐瘀湯恰恰降低了其血黏度,進而擴張血管降低血壓。在張志恒[28]研究中通過對血府逐瘀湯合用西藥的中西醫結合法治療高血壓也有明顯的效果。
32“補氣”散瘀氣虛血瘀證是其中的一個病理因素之一,此證候的高血壓患者也不占少數,從古至今都得到了廣泛的探討及應用,以氣血兼顧,陰陽并補的原則通過實踐應用了加減補陽還五湯、當歸補血湯等方劑。方堃[29]在當歸補血湯對腎性高血壓 36 例血漿內皮素(ET)的實踐中,發現降低血漿 ET 和 MAP可阻止血管進一步減少管腔內膜的增厚,進而減少腔內變硬,血流阻力減小,血壓降低從而來緩解高血壓引起的腎功能不全。脈暢則血自流,通過補氣活血法,使脈道通常。應用方劑中剛好黃芪通過與當歸配伍有此作用。這恰好解釋了“脈不通而血不流”,證明脈瘀致眩這一理論,又通過辨證,主次兼夾之分,合理應用藥物得到高血壓病的治療,在論證高血壓氣虛血瘀存在細胞凋亡時,胡小琴[30]應用補陽還五湯含藥血清干預細胞模型,證明氣虛血瘀證的高血壓患者引起的細胞凋亡應用此藥有很好的效果,并進一步去加以探索。
33“祛痰”散瘀李東恒在《蘭室秘藏·頭痛》中云“足太陰痰厥頭痛……獨不為風所動也。”認為其病機脾胃失司,故生痰聚內所致,而風痰上擾證的半夏白術天麻湯其功效為息風定驚、健脾祛痰代表方劑[31],由于“津血同源”津血均為脾胃所化生,往往痰凝則血停,痰血互結,故化痰時也有兼顧散瘀。在此方的基礎上李芳[32]聯合血府逐瘀湯佐治通過對內皮功能的影響而治療,觀察治療前后對照組血壓及影響血壓內皮細胞的血清的NO、ET-1濃度、內皮素—1的變化。結果發現實驗組有效率 917% 明顯高于對照組的 733%,可以看出,通過正確辨證后我們可以得到很好的療效。
34“泄火”散瘀《素問》中首次提到致眩,“諸風掉眩,皆屬于肝”可以看出其眩暈與五臟中的肝息息相關,其原因在于陰陽不能制約,肝腎陰虛,肝陽上亢生化風所致[33],大多以陰陽并補、肝腎并補、清虛熱并活血為主,通過后代醫家總結,應用天麻鉤藤飲、鎮肝熄風湯等方祛內風泄實火,三黃湯、竹葉石膏湯清虛火。“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所以在平肝熄風的同時加上補血、行血的藥一點都不為過[34]。《雜病證治新義》中提到“天麻鉤藤欽”方劑,佐以蓋母草、牛膝等活血化瘀之品即含此意[35]。
4小結
綜上所述,從“脈瘀致眩”論治高血壓病已取得一定的進展,“致瘀”即各種致病因素導致,具有廣泛性,血瘀體質患者在治療高血壓有很多優勢,但其辨證論治最為重要。要正確判斷出眩暈的病因及血瘀是處于眩暈的主證還是次證,上述皆為《內經》:“脈不通則血不流”的具體例證。本文結合“脈瘀致眩”理論系統從高血壓病血瘀體質的角度闡釋其病因、病機、治療原則、[HJ3mm]治法、療效所取得的成果,從而進一步豐富醫家前期研究的科學內涵,并為后期研究奠定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
[1]血壓變異與高血壓病患者中醫體質分類的關系[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03,23(2):88-90
[2]楊俊華,張虹,巫心培急性心肌梗塞與急性心肌梗塞合并高血壓病舌象、脈象辨證分型的比較[J].天津中醫藥,1998(2):64-65
[3]曾昭文,陳永魁,羅成輝青年高血壓患者98例臨床特點分析[J].中國當代醫藥,2011,18(32):177-178
[4]黎芬芬,文彬,李福英,等活血化瘀法在肝硬化腹水中的應用[J].遼寧中醫雜志,2015(5):964-965
[5]龐磊,姚春穎,林玲高鹽飲食對大鼠高血壓腎病進展的影響[J].中西醫結合心血管病電子雜志,2016,4(21):21-22
[6]張敏,袁玲系統健康教育在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護理中的應用[J].河北中醫,2009,31(10):1574-1575
[7]唐黎群,袁國榮,潘智敏潘智敏教授治療積癥學術經驗整理——高血壓病與積證理論發揮[J].中華中醫藥學刊,2012(6):1317-1318
[8]于少麗王清任瘀血證治淺析[J].中國中醫藥雜志,2008(7):45-46
[9]段吾磊,劉丹,譚元生從中醫因瘀致眩思想論高血壓及其并發癥的防治[J].中西醫結合心腦血管病雜志,2017,15(10):1259-1260
[10]蔣佩瑄淺談血瘀病臨床見解[C].中華名中醫論壇暨發揮中西醫優勢防治腫瘤高峰論壇2011
[11]呂鵬飛,梁玉龍血管內皮細胞功能損傷及保護措施中西醫研究概況[J].河北中醫,2014(1):139-141
[12]丹皮酚對脂多糖誘導損傷的與平滑肌細胞共培養的大鼠血管內皮細胞黏附功能的影響[J].中國中藥雜志,2014,39(6):1058-1063
[13]鄭璐玉,楊玲玲,李玲孺,等液相芯片技術檢測痰濕體質人群TNF-α、IL-6、CRP及MCP-1的表達研究[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13,33(7):920-923
[14]程文,高建平,張征宇微小RNA與腫瘤相關性研究[J].醫學研究生學報,2011,24(2):203-207
[15]羅燕娜正常血壓高值者肱動脈血流介導性舒張功能與早期動脈硬化相關性研究[J].吉林醫學,2016(1):131-132
[16]李紅蓉,秘紅英,孫穎,等基于脈絡學說對動脈粥樣硬化病因病機的認識[J].中醫雜志,2017,58(16):1359-1363
[17]孫曉光,彭越,石琳葉天士“陽化內風”理論對仲景學說的繼承和發展[J].吉林中醫藥,2011,31(11):1043-1044
[18]常富業,王永炎絡病辨證淺析[J].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3,26(6):9-11
[19]鄧悅,常立萍,齊鋒,等高血壓病從“風痰瘀絡”論治的思考[J].中華中醫藥學刊,2011(4):750-751
[20]朱志會,李玉文,尚沛津,等β3-乳香酸對血瘀證大鼠血液流變學和血管內皮功能的影響[J].現代生物醫學進展,2017,17(20):3806-3810
[21]郭莉群,楊解人,孔祥,等芝麻素對腎性高血壓伴高血脂大鼠血脂及動脈粥樣硬化形成的影響[J].中國中醫藥科技,2009,16(3):197-199
[22]Antonio Perez,Sergio Jansen-Chaparro,Ignasi Saigi,等.Glucocorticoid-induced hyperglycemia(糖皮質激素誘導的高血糖)[J].Journal of Diabetes,2014,6(1):9-20
[23]桑莉,莊軍老年冠心病患者血漿脂蛋白(a)、載脂蛋白B/AI比值及纖維蛋白原(FIB)水平的變化[J].中國傷殘醫學,2014(21):111-113
[24]許智紅老年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用藥依從性的調查研究[J].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2016,17(96):513-514
[25]劉蘭林試論外感病蓄血證的源流及辨治[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01,7(6):64-66
[26]田虎,王素改試論王清任活血化瘀法及其成就[J].天津中醫藥大學學報,2006,25(4):204-206
[27]丁宇煒,徐瑛血府逐瘀湯治療高血壓病151例療效觀察[J].新中醫,2001(11):38-39
[28]張志恒血府逐瘀湯聯合西藥治療原發性高血壓40例[J].河南中醫,2015,35(6):1412-1414
[29]方堃,胡長綬當歸補血湯對腎性高血壓36例血漿內皮素的影響[J].實用中醫內科雜志,2003,17(1):21-21
[30]胡小勤,曾學文,岑衛健,等補陽還五湯與高血壓病氣虛血瘀證“方證相關”的蛋白質組學研究[J].科學技術與工程,2012,12(27):6883-6888
[31]薛瑜峰,薛佳茜,朱翠玲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從肝脾論治[J].河南中醫,2014,34(8):1486-1487
[32]李芳,李霞半夏白術天麻湯聯合血府逐瘀湯佐治高血壓病的療效及對內皮功能的影響[J].廣東醫學,2014(6):936-937
[33]段成功“諸風掉眩,皆屬于肝”的臨床運用[J].中國中醫急癥,2015,24(1):18-19
[34]佚名“治風先治血”應用于中風先兆的探討[J].中醫藥臨床雜志,2018,30(08):29-31
[35]黃金,劉瑜天麻鉤藤飲治療急性中風肝陽上亢證研究進展[J].光明中醫,2011,26(4):856-857
(收稿日期:2019-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