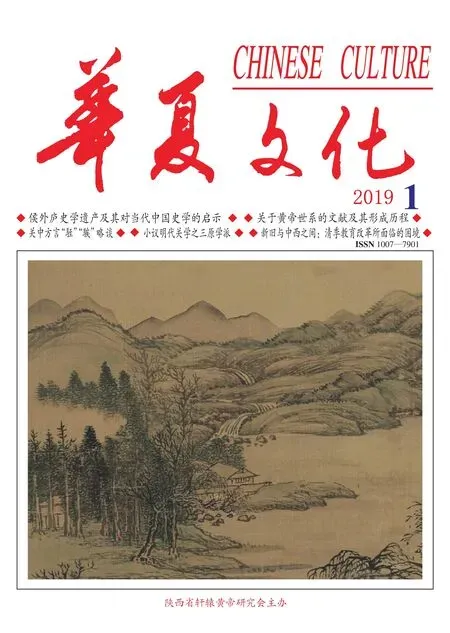論莊子與惠施“天地一體”觀的區別
□趙 田
在《莊子·天下篇》中,關于惠施的“道”,可以一言以概之:“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莊子也有類似的言論,《齊物論》一篇中有“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若單從字面意思上來看,似乎莊子與惠施都秉持“萬物一體”的物我觀,所不同之處只在于惠施在此處強調了“泛愛萬物”,那么莊子對于萬物,是否也有這種“泛愛”的情感呢?莊子與惠施所言的“天地一體”的內涵是否一致呢?以《〈莊子·天下篇〉注疏四種》(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為參考,顧實、高亨、錢基博、馬敘倫四位學者對此的注釋可以分為兩種,一是二者并無差別,一是二者差在“泛愛”。
一、 《〈莊子·天下篇〉注疏四種》一書中的觀點
錢基博認為這是“道家者言之究竟義”。老莊對此都有過相關表述,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老子之言“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齊物論》:“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秋水》:“以道觀之,何貴何賤?……萬物一齊,孰短孰長!”此莊子之言“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可見錢基博并不認為老莊與惠施的觀點是有所差別的。高亨對惠施“泛愛萬物,天地一體”的解釋是從完全不同的角度出發的:“古持有天圓地方之說,或曰:“惠施持天地俱圓之說。以為天如圓盂,而覆于上,地如圓磨,而承于下。天之周涯,地之周垠,本相接連,而成一體,故曰‘天地一體’。或曰:“惠施認為天地為雞卵,天如雞卵之白,地如雞卵之黃,本自成一體,故曰‘天地一體’。”這種解釋是基于惠施看待萬物的獨特方式而作出的,但并未與老莊的相關論述作出比較。馬敘倫在這里所采取的是章炳麟和胡適兩位學者的注解。章炳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物之所有。萬物畢同畢異,此物之所無,皆大同也。故天地一體。一體,故泛愛萬物也。惠施之言,無時、無方、無形、無礙。萬物幾幾皆如矣。”胡適:“上說九事,都可證明天地一體之根本觀念。以宇宙是一體,故欲泛愛萬物。”(張豐乾:《〈莊子·天下篇〉注疏四種》,華夏出版社2009年,第305頁)從以上三位學者的解釋中可以看出,他們皆認為惠施“泛愛萬物,天地一體”的觀點和莊子“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并無差別。
但顧實認為,“泛愛”正是莊子與惠施的不同之處所在。惠施泛愛太過,這一點不可不察。對此,顧實所做的解釋如下:“此同心物之異,而為歷物之意之結論也。”這是說“泛愛萬物,天地一體”這句話是對惠施“歷物十事”中前九個命題的總結,是“合同異”之后得出來的結論。在《莊子》一書中,相類似的言論還有不少。《秋水篇》曰:“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這是說人只是物中一物,并無任何優越之處。《達生篇》曰:“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則陽篇》曰:“天地者,形之大也。”即便是天地,也是物中一物,只是大小上有所差別罷了。《齊物論篇》亦曰:“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接下來,顧實先生以《莊子》一書中的特定篇目為例,說明道家不尚泛愛。例如《天道篇》老子曰:“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在宥篇》曰:“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顧實先生認為惠施所言的“泛愛萬物,天地一體。”與莊周“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涉及到的,是“泛愛”的問題。惠施“泛愛”太多,而莊周并不尚“泛愛”。這不免涉及到二人的“天地一體”觀內涵是否一致的問題。
二、惠施: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從《莊子·天下》中所載的“歷物十事”可以看出,惠施擅長邏輯分析,注重對事物名相的辨析。其“合同異”命題就是惠施論證“天地一體”的證明:“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按照惠施的看法,同異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為“小同異”一種為“大同異”。“小同異”是從世俗或常識的角度而言的,是說具體的事物之間存在異同之處。此物與彼物,或同或異;“大同異”是說萬物畢同畢異。從天地一體來看,萬物只是一物,這就是“畢同”,從萬物的差別來看,萬物各是一物,這就是“畢異”,“畢同”“畢異”意為萬物既莫不相同又莫不相異,這就是“大同異”。從惠施“大同異”的觀點來看,他是從萬物之名上取消了萬物之間的同異之別,因此,事物之間的彼此之分都是相對的,所以“天地一體”也就順理成章了。
那么“泛愛”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到目前為止,關于惠施“泛愛萬物”命題的理解存在以下五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該命題具有倫理性質,并且源于墨家的兼愛,如胡適等;第二種:該命題具有倫理性質,但并非源自墨家的兼愛,而是源自黃老,如郭沫若等;第三種:該命題不具有倫理性質,“愛”字只能作 “愛好”、“喜歡”解;第四種:馮友蘭認為該命題沒有實際意義,可能只是用來加強 “天地一體”的語氣;第五種:該命題在惠施那里確實具有倫理性質,但泛愛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惠施這里,“泛愛”只是果,而“天地一體”才是因。惠施通過辨析名理,要達到的,并不是“泛愛萬物”,而是“天地一體”。
三、莊子: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
《齊物論》:“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從此物看,對方為“彼”;然而從彼物自己一方看,它即是“此”。也就是說,萬物之間并無絕對的彼此之分,在未落入對待的情況下,它們實際是“齊同”“齊一”的。人們之所以會認為萬物之間存在種種差別,是因為人將自己的認知強加給了萬物:“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秋水》)但如果人們要是從“道”或“全”的觀點看問題,就可以獲得“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的大智慧,從而不再為“小成”之見所困擾和煩惱。在《齊物論》中,莊子通過“齊是非”“齊同異”“齊物我”“齊生死”,最終達到了“齊萬物為一”的境界,這個“一”就是一于“道”。既然萬物為一,那么所謂的是非同異問題,當然就歸于無形,被消解殆盡了。
除此之外,莊子從生成論的角度說明了“天地一體”何以可能。在《知北游》中有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這是從生成論上肯定了萬物皆為一氣流行而生,為“萬物與我為一”提供了質料保證。
四、二者的區別
從兩人論證“天地一體”的思路和方法來看,惠施“泛愛萬物,天地一體”的結論是從前面九個命題中得出來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合同異”,萬事萬物畢同畢異,并無絕對意義上的差別,因此可以說“天地一體”。既然“天地一體”,“泛愛萬物”也就順理成章了。這是從對事物名理上無止境的辨析中得出來的,是通過自身的雄辯之才將萬物化為一體,至于“泛愛”,則是在“天地一體”的基礎上順勢衍化出來的。與惠施不同,莊子是從萬物的生成方式上來表述“齊物論”的。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是將主體與客體化為一體,取消了主客對立,主客二分。這與惠施通過雄辯之才齊同萬物是截然不同的。莊子所說的 “萬物”,并不需要“我”這個主體去對其進行理論上的探究分析,也就是說,萬物無須落入人的對待中來獲得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我”與天地萬物是齊等共處的,而不是外在于它們而存在。從對待萬物的方式來看,在惠施那里,是通過自身的雄辯之才來消弭萬物之間的差異性,也就是“合同異”;而在莊子心中,則是要取消主體的偏執與成心,完全從“道”的立場出發,也就是“以道觀物”,在洞察萬物表面的性質是有差別的前提之下回歸到物質的本性,自始至終所秉承的就是這種天地萬物一體的“齊物”狀態,這正與惠施的“天地一體”的理論殊途同歸。 只不過,莊子建立了完整的思想體系,通過“虛靜”“坐忘”“吾喪我”等方法,不僅消除物與物之間的界限,也消除了物我之間的界限,從而得到精神的“絕對自由”。而惠施雖然通過論證達到了“天地一體”,卻沒有將之與自身實踐相結合,反而為外物所累,困于名實。 因此也有學者指出,惠施之“合同異”只是在“名”的層次上而言,非實際事物之間差異的同異之“實”。 而莊子所“齊”的不僅僅是“名”,更是齊萬物之“實”。(參見趙炎峰:《論莊子與惠施哲學思想的差異》,載《中州學刊》2011年第3期)由此可見,惠施落腳于“物”,莊子落腳于“道”。莊子說:“道無終始,物有死生”。這就表明,惠子聚焦的“物”不及莊子秉承之“道”,因“物”有死生,而“道”則永存,“道”是本,“物”是末。 因此,莊子說“外物不可必”,評價惠施“弱于德,強于物”,“逐萬物而不反”,是舍本逐末,誤入歧途。
不僅是論證的方法和對待萬物的態度有所差別,二者所持的心境也是不一樣的,“泛愛萬物,天地一體”所表現出來的,是惠施對于萬物之名的辨析之才,而《齊物論》中“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所體現出來的,則是莊子物我兩忘,“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天下篇》)的悟道境界。一個累于物,一個是脫于物,一個是究極物理,一個是超然物外。雖然兩人都講“天地一體”,甚至惠施還提出了“泛愛萬物”的說法,但是兩人的物我觀所體現出來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