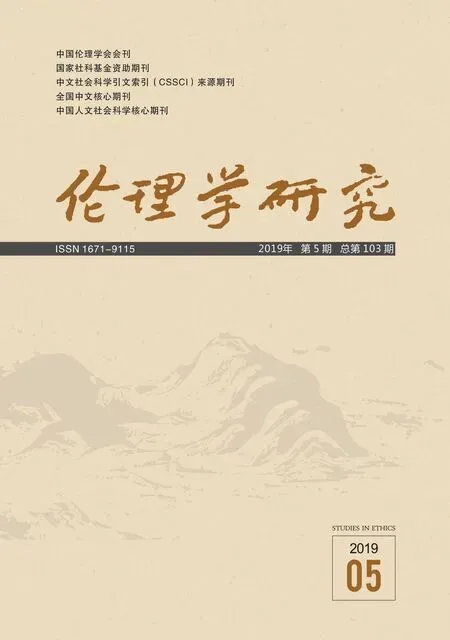身體的自由:體育的生命倫理審視
郭恒濤,劉欣然
在生命倫理的主體形態中,體育是人身體自由的表現形式,是自我存在的行為展示,是全面發展的實踐要求,是生命意義自我實現的根本途徑。生命存在為體育涌現,體育思想為生命喝彩。在生命倫理的價值維系中,體育是一個重要的存在環節,突出表現了人的生命強力、勇力、活力和潛力,是自覺生命生存活動的一個方面。正因為體育活動的存在,使得生命遠離虛弱、病態和無力,找尋到健壯、強大和有力的生命感知,體育成為自然生命積極且活躍的主動因素。體育在人的生命活動中具有重要作用,將生命第一性的生理自然,通過身體運動保存著肌肉的力量、韌帶的牢固、血管的彈性、關節的靈活、骨骼的堅韌,使生命機能保持在一種高效且實用的運轉范圍內,促進人生命活力存在幸福感的達成,體育本身就是融入倫理境界的生命行動。
體育是人所獨有的存在方式,將生命活動保持在一種自然恒定狀態,使生命不至于在快速社會進程中,發生不適應或者靜態倒退,使動物性的生理基礎,建構起自然生命的保護裝置。因此,體育并非只是簡單的身體運動姿勢、形態或軌跡,而是生命存在不可缺少的行為基礎,是保障生命順利前行的主導方式,是動物性的生存活動和文化性的社會活動的統一。“在人生美好和善良事物中”[1](P60),體育活動本身就是向善的行動,是面向生命倫理和諧有序的善。在體育的主體認識中,我們有必要了解人主體存活的狀況,以及在生理、生物、生存、生活、生產和生命等形態中的體育主體性,以便建立生命哲學對于體育的主體關懷。生命倫理對人的關懷在體育中創建生活的空間、編織意義的網聯、形成互動的結構,生命活躍的永動機制在體育中建立起來。人主體存在的確認,體育具有完整的話語權,是對存在實體的驗明、存在狀態的首肯、存在空間的給予和存在意義的詮釋,體育在生命倫理中獲得思維的形上空間。
一、人的生理自在:生命倫理的體育身體屬性
自在,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存在狀態。自在的無束縛、無限制和無規定,反倒成為了有的先決條件,自在為有提供了普遍性的理念,康德在“自在之物”中建立了一種理論根基。黑格爾在邏輯理論中認為:“最初的有,是自在地被規定的,所以,它過渡到實有。”[2](P68)有與無的對立是因為其自在之基,是自在之所以存在的先天因素,是對有規定性事物的本質直觀。自在一定意味著有什么東西存在,而這種自在就成為哲學反復思考的理論基點。人的自在,尤其是人的生理自在,是作為動物性身體而存在的根據,身體中所意涵的主體價值,是生命本真存在意義的內容所在。身體成為了一個隱秘的所在,并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關注焦點。
這樣,人們就開始發現身體,維塞留斯在《人體構造》中對身體進行探索,身體成為解剖研究的主題。置于手術刀下的身體,開始被肢解并碎片化,身體的完整意義在對死亡的焦慮和驚恐中,被分割成為頭顱、手臂、身軀、腿腳、內臟、肌肉和血管,一具冰冷的尸體和一些廢棄的組織器官,就成為失去人主體意義的身體。身體就此受到了冷落與排擠,仿佛變得無足輕重,身體縈繞在死亡的恐懼之中。隨后,笛卡爾的沉思中,“我最先想到的是我有臉、手、胳臂,和肢體的整個機械結構,可以被看作是一具尸體,我稱之為身體”[3](P13)。從此,身體被賦予機械結構的標簽,與靈魂成為人的對立兩面。人的身體與人本身,在本體論層面上發生了斷裂與分離,人存在著兩個自我,身體被拋棄變成為一種殘余。身體趨向于一種單一的動物性肉體,不再是一種主體的標志和象征,反倒成為靈魂的累贅和主體的對立面。“人的概念的收縮,導致一種模棱兩可的身體觀念的產生,即我們曾經提到過的,它將身體比作‘個人化要素’,主體的邊界。”[4](P81)身體明確地區分著個體的人,從而導致身體變成為一個個形骸和軀殼,身體的本質被虛無化,身體成為主體的依附品。
人是體育的主體,身體是人的基礎,只有將身體放置在合理的位置,生命主體的價值才能得到凸顯,體育形式的內在性才能得到詮釋。“體育起源于身體實踐,是人類活動的一種獨特經歷,是源于身體內部的躁動和情緒。”[5]體育因身體而存在,為身體而呼喊,體育的功效和作用,不僅反映在身體的生理基礎之中,還反映在生命倫理的文化內涵之內,體育創造著人類的社會生活。在身體屬性之中,體育是一種外在的能力給養,給生命主體更多的動力源泉,讓身體始終處于一個良好的運行狀態之中;在體育倫理之中,身體不僅是一臺精密運轉的儀器,而且還是生命主體唯一能夠依靠的堅實基礎,是賦予生命倫理意義的物質平臺。體育與身體不是二元論的差別,而是一元論的整體,是在本體論中詮釋的概念,和在認識論中解釋的對象,是親密無間的朋友與伙伴。“在倫理意義上,當體育改造出健康美麗的身體,表明人性的善。”[6]在人生命倫理的情狀中,是不能忘記體育所引導出的身體屬性,體育是在身體中逐漸訓練和培育出的自在行動,是與身體內在生理相關聯的因素,并且拓展到外在的文化范疇之中。體育是人生命倫理的自在狀態,并在于身體的對話與述說中,倒向人主體性的生命基礎中,體育面向著生命善的無限可能性。
二、人的生物自知:生命倫理的體育存在基礎
自知,表明自己知道或自我明了,是自明自曉的反映,從中表現出一種人生智慧。《老子》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是對普遍認識的反觀,同時,古希臘德爾菲神廟也有箴言“認識你自己”,自知成為立志進取的人生定律。人在世間事物中認識自我,表明人能夠自知自省,能夠對自身進行審視和評價,能夠辨明是非對錯,知曉善惡分明,明了利害得失,自知成為一種理性的凝聚。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人是有理性的動物”,這樣人的生物屬性得到凸顯,人本身就是世間萬物中的一種生物。我知道我是動物。生物屬性成為人的某種標簽而無法替代,雖然哲學思考當中將心靈放置在無限高尚的位置,但是,人的動物屬性卻是不可抹殺的真理。“一切生物所具有的生長能力和動物所具有的顯然是自發性的運動能力,看來都是神秘而不可測的。動物的運動不像天體的運動那樣簡單而有規律。”[7](P40)動物的生命成長過程,即有機生命體在世界之中,同時,又抽身于世界之外,在整個物質流轉過程中,顯示出個體的獨立性來。動物能運動,需要物質交換,會有能量需求,需要將外在元素為己所用,動物的本體感知體現在內在性之中。可是,動物是有起點和終點的生命過程,誰都逃不過時間之箭的追逐,只不過“對于動物來說,時間空無一物,毫無意義。只有當我們作為人存在時,物才在時間中存在”[8](P36)。這樣,我們不可避免地將時間當成是稀有之物,珍惜時間才能贏得生命,于是,人將自我的生存作為優先條件進行看待。如何能讓生命存活得更長久,成為人類的一個永恒話題被辨識。
“盡管動物從觀察中學到了很多知識,但是它們的知識也有一大部分得于自然的創造。這些知識的比例遠遠超過它們在平常情況下所具有的才能”[9](P103)。體育的存在基礎,以動物性的生命活力為依托,并在生存過程中營造出野性活躍的氛圍,讓人類的動物性本能得以宣泄和舒緩。人存在于世界之中,與世界接觸的是生物屬性,是動物性肉身的真實感受,這一感受來自于生命自然的原始涌動,是生存最為實在的體驗。人生命倫理需要保持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就必須了解自身的生存處境,生命的活躍需要得到釋放,就必須覓得文化上的生存空間,而體育正是這一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體育讓人的動物性施放,在運動場中嬉戲打鬧、追逐競比、游戲休閑、團結協作、激情表演、熱烈喊叫,人類活躍蹦跳就如同在遠古自然的場景之中,人類天性中的生物本真在體育中得到保存。“體育是肯定人類身體動物性的行為方式和文化結果”[10]。在體育中,人能明確感知自身的生物性,心跳呼吸、肌肉酸痛、大汗淋漓和生命自信,都是在體育中獲得的即時體驗,體育讓人感知到生物的人的強大、力量與勇氣。
人的生物自知,是生命倫理主動尋求的自然回歸,讓社會性的生活、文化性的生存和歷史性的生命,能夠主動意識到人類自身的生物屬性,使人類在試圖充當主體的路途中,不忘記自身的自然本性。在體育中,“生命倫理成為了人性一種顯現方式”[11],因此,體育成為一種哲學反抗,是在揚棄社會文化背景之下的生命尋回,從而獲得豐富的、持久的且穩定的主體尊重,生命主體的生物屬性被永久地標記下來。體育是在外部的動態行為途徑中,發掘主體自身的內在本真,將人的生物自知作為安身立命之本,并充分地圍繞著生命涌動的動物性,而努力追求的文化實踐形式。因此,在對人的生物自問中,可以回答“知道人是誰,所以才體育”,體育成為人獲取主體性生命的途徑之一。自知的主體是對自我的充分了解,體育中生命主體同樣也基于此種理念,對人的關注,對生命的保護,對生物的自識,是體育活動長久開展的基礎,體育成為人的某種能力,為人的生存發展服務,并對倫理屬性進行著價值闡說。
三、人的生存自我:生命倫理的體育本性解釋
自我,是對自己存在狀態的認知和體驗,同時,也是對生命主體地位的評價與反饋,以推動自我實現的滿足與嘗試。“人對他自己的自我不是中立的或漠然置之的。愛和知識、價值判斷和事實描述,在確定自我認識時不可分割。”[12](P8)自我總是會被置于中心主義立場之中,自我實際成為對人本性的召喚。人之所以尋求自我,就是希望探求人的現實命運和未來處境,以及人所擁有的知識和能力,這一切都與人的存在本質息息相關,因此,自我是需要進行認識和理解的概念中心。“我們所擁有的僅是一次次的體驗,而這個自我——被認為是個人全部經驗的領受者——卻從不以經驗形式出現。”[13](P6)活著就是自我保存,就能夠參與自然競爭,就有機會成為奮斗的勝利者,因此,生命主體存在變得尤為可貴。“朝向自我保存或自我肯定的努力,使一事物成為其所是。”[14](P13)自我保存是真實的本性使然,是內在力量的主動行為,這與人類生存的基礎性密切相關,生存成為生命理性的必然選擇。
生存不僅是個體生命的存活,還應該是種群的不斷延續,在某些層面上還要尋求超越,因此,人類為了生存發展而繁衍生息、總結經驗、累積知識、建造居所、訂立制度、創建文明,在生存的基礎之中,人類創造著整個世界。“人總是保持著他的開放性和適應性,但他也得為了完善和確定性而不斷地奮斗。因此,他用以努力去理解自身存在的各種概念,的確對其存在的自我實現有著一種決定性的力量。”[15](P9)人關于他自身的各種理性塑造,都是基于生存的各種觀念之中,生存使人類對于自我解釋變成為一種習慣,成為知識運用的理論基地。人的自我生存是自然本性,而人的生存自我則是理性反思,是需要加以探明的存在概念。
體育是人類生命主體存在的有益補充。人生命倫理的存在,時刻需要與虛無、頹廢和消亡作斗爭,一刻的松懈或怠慢,都可能導致生存的終結,因此,生存的活力需要及時進行補充。體育正是肉體生存的醫療站,將多余物質消耗,將剩余能量轉換,將身體毒素排遣,這都需要生命主體在體育中進行實時的鍛造,才能獲得生存的自我關懷。同時,體育也是肉體生存的充電站,力量的持續積累、活力的有序放大、勇氣的不斷集聚需要在體育中進行艱苦的訓練,才能獲得生存的自我理解。再次,體育還是肉體生存的游樂場,游戲中的追逐打鬧、表演中的開心愉悅、休閑中的情緒釋放,也需要在體育中進行本體的感知,才能獲得生存的自我陶醉。當生存成為人生命倫理的一個永恒話題時,體育是不能回避的談資,體育是肯定自我、證明生命存在的有力證據,能體育者必定是生命主體的存在者。“善待和敬畏生命,構成了底線生命倫理”[16]。人的生存自我是生命倫理發展的一個階段,體育正好能夠證明這個階段的真實有效性,并強化生存自我的主體地位。體育主體的生存自我,是自我實現的關鍵環節,推動了生命主體認識向生命本體的靠攏,使自我意識不局限在思想層面,而關注到人生命倫理自我的自然存在和發展。人類生存在體育的滋養中,獲得一種自我能力的超越優勢,從而使得生命主體活力變得更為精彩。生存自我的基礎性是體育關注的焦點,正因為生命倫理存在的重要原則,才使得體育為生存發展而服務,幫助人類生命走向自我成熟的理性路途。
四、人的生活自覺:生命倫理的體育文化關懷
自覺,即內在自我的認識與發現,是自我察覺和創造自我的主動意識。自覺不僅反映在意識層面,同時也貫徹到行動之中,是在改造自然過程中所形成的基本人性,表現在自我存在、發展和延續的內在本質中。自覺是人自我確立、認識和創造的思想總結。“思想是一種結果,是被產生出來的,思想同時是生命力、自身產生其自身的活動力”[17](P58),其本質是一種自覺活動,貫穿于時代精神之中。自覺在于維護人的生命主體地位,使生活導向美好的人生愿望中,讓未知的生活在既定的規則中得到不斷的延續,以保證人普遍自我的獨立完整性。“‘活的意義’就在這個人生世事中,要在這個人生世事中去尋求。‘活’在這里便是掙扎、奮斗、斗爭和這種奮力斗爭的成果和勝利。”[18](P17)活的意義成為人性構建的一個方面,成為人生命倫理的生存本體,為人生意義、生活狀態訂立存在標準。
究竟人為什么生活?這是一個自覺意識的問題,人“生活著”就是最好的回答。當生活變成一個普遍定律時,“任何接觸到或進入人類生活穩定關系中的東西,都立刻帶有了一種作為人類存在境況的性質”[19](P3)。人的生活處境,以及存在狀態成為考察的焦點,生活的本意就是為了維護人的持續存在和發展,將人更好地存活作為首要目標去實現,“生命圓滿”[20]就是人生活的本意與初衷。生活在于生命存活或活動,因此,“活”成為了關鍵,而“活”一定不再靜止之中,卻能夠在運動中顯現出價值。體育就是生活的自覺形式,是生命主體運動的存在現象,體育為人“活著”或者“活得更好”而努力。生活中不一定要體育的參與,但是,想要活得更好,活得有尊嚴,活出人生的精彩,體育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因此,參與體育的人總是活得那么有滋有味。
體育在生活中就存在兩面性,它不僅適合個體行為,同時也是群體活動,因此,體育不是孤立的個體事件,而是種群的存在集合,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進入公共領域,以尋求更為廣闊的存在空間。“在公共領域中,各不相同的、復雜的社會群體注定要發生相互的聯系……原來的個人規約模式和新的交往模式共同存在,這種共存正適合一種陌生人之間度過的生活。”[21](P20)公共領域造就了這樣一個存在空間,而體育本身就具備這一空間,它存在于社會生活之內,為人類生命活動而服務。
體育就是生活本身。生活中如果沒有體育的參與,就如同沒有藝術的滋養一般,那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何在?因此,人應當將體育變成,如吃飯、穿衣、睡覺一樣自覺,體育才真正地在人之中“活”著,并顯現出它獨特的價值來。體育是人生命倫理的自覺表現,將人的命運與生活所需結合在一起,以增強適應自然并改造自然的能力。體育進入生活是一種必要選擇,因為,物質化的生活,只感受紙醉金迷、饕餮盛宴和奢侈豪華的腐朽享受;精神化的生活,只體驗虛無縹緲、空洞無知和海市蜃樓的思想寄托,所以,唯有體育讓物質消耗,讓精神富足,使生活獲得更多且長久的主體觀照。
在人的生活自覺中,體育是一種主動力量,是對生命主體的行動和保護,因為,文明化的生活所帶來的毒性,需要尋求解藥的幫助,而體育正好通過能量的消耗、體液的代謝、情緒的釋放,將身體毒素排出,使人的生命重獲新生。“體育倫理與生命精神之契合”[22],生活中的自覺,體育參與其中。人的生活在于自我的選擇中,人并不是命運的旁觀者,反而是主體的締造者,因此,自覺參與體育是對生活狀態的把握,是對生命主體的尊重。
五、人的存在自由:生命倫理的體育本質實現
自由,是主體的無約束和無束縛的狀態,自由意味著解放和實現,是人生命倫理發展的最高階段。人的自我實現,自由是人之為人的體現。蘭斯頓·休斯有這樣一首詩《像自由這樣的字》:“有些字像自由,說出來甜蜜動聽美妙無雙,在我心靈的深處,自由無時不在盡情地歌唱……”自由是一個高頻詞匯,成為人們獲取生命主體發展的理想境界。自由規定著自我,是行動的方向指引,因此,“整個人性的最根本本性就是自由”[23](P40)。人要獲得主體性并實現自我,自由是終極的價值導向,自由成為自我規定的奠基。可是究其自由本身,自由是什么?卻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自由好似一個迷霧,供人們述說和解釋著。可是在人的知識體系中,自由可以這樣理解:“在認識論中,自由是指對必然的認識;在本體論中,自由是指人的存在的本質”[24](P77);在倫理學中,自由是善的選擇和體現。自由不僅是絕對理念,同時,也是絕對精神,是對人主體性的本質描述。“人的自由使人的存在是獨立自主的存在,能自己作出決斷的存在。”[25](P12)人本身是有局限性的生命主體,而自由則正好為人的存在設定目標,使人的活動具有超越的可能性,人才能獲得獨立自主的存在感。
人的存在以生命存活的形式出現,自由成為對生命狀態的描述,人的生命倫理自由是主體的向往和追求。在黑格爾[26](P458)看來“生命的理念卻是自為的,既從那個事先建立并進行制約的客觀性得以自由,又從這種主觀性的關系得以自由”。生命主體是絕對的存在實體,是普遍理念所支撐的概念,生命主體具有現實的存在性,確立起這個世界的存在形態和樣貌。人的生命源自于動物,卻又賦予了更多的存在價值,人作為具有超越意識的生命存在體,人在創造世界和自我的同時創建文明。在人生命倫理自由中,體育是一種自由的展示,是人生命能力強大且自信的表現,人作為能動的存在物,生命特征的展示需要實時進行。
體育就成為生命主體自由的選擇,成為標記生命行為的文化因素,在人類社會中存在并發展。可是,在現實生活中,否定生命之自由的狀態時有發生,“人的生存在自由這個問題上陷入了困境:自由地選擇非自由”[27](P281)。就如同,文明生活倒向于智能化,即:人體力付出的減少,人是非常樂于傾向這種生活,但是,隨之而來的靜態生活則會導致肥胖的增加,人的肌肉能力得不到有效保持和強化,生命主體自由的存在感就會衰減。于是,體育成為這種選擇的唯一解藥,它讓人生命倫理獲得強健、美感和充盈,人的生命自由在體育中得到發展。
人的生命倫理自由不僅表現存在,更希望獲得超越、贏得挑戰,而體育在本質內涵中具有此種基因,是實現生命自由的途徑。在本質存在中,體育是證明人生命自由的文化形式,生命在身體運動狀態中獲得存在感,體驗動物性存在者的自然本質;在主體需要中,體育是滿足人生命自由的原始動力,生命在于運動,自由在于釋放,體育時刻準備著為生命自由尋找釋放的舞臺;在自我實現中,體育是追求人生命自由的存在方式,探索與求知、進取與超越、獲勝與比拼,都是體育努力營造的文化氛圍,以實現生命主體的精神卓越;在價值選擇中,體育是衡量人生命自由的外在尺度,個體的付出、群體的責任、社會的貢獻、勞動的創造,都是體育對于生命價值的豐富內容,讓生命主體創造更多的精彩。“善的無限性是生命倫理的實踐目的”[28]。體育是對人生命自由的一種保持、實現和提升,它不僅與人是實踐關系、生活關系更是生存關系,是在本質中規定了人是運動的存在者,是活躍力量的經營者,是自由生命的創造者。人的生命自由是類存在的本質特性,而體育在人的生命自由意識中,由實踐上升到認識,是由體育與人的關系所決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說“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體育就是人生命自由的本質活動。體育不僅是人的存在方式、行為手段和文化內容,更是人通往生命自由路途中的實踐保障,是人自我實現的本質途徑。
六、結語
“在新時代的體育倫理關涉中”[29],體育是人生命行為的主動形式,是生命活動能力創設的保存機制,將“生生之流”的生命存在形式,主動自發地放置在體育之中,讓生命行為保持原初的存在狀態。“在現今受到異化活動侵襲中”[30],體育能實現人生命倫理自我的生成和創造,是對人本質的顯現,同時也是向世界宣告“像人一樣的活著”。因為,動物無法體育,只是本能的身體運動,而人會體育并且創造體育,所以,體育被貼上“人性存在物”的標簽,人之為人存在,體育是有力的證據。體育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對自我的塑造、完善和超越,是回到自然并與自然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的實踐過程,人與體育是本質的相互證明。對于人類來說,體育已經超越了動物本能的生理需要,而成為人的一種存在方式,來保護人的生命本身。在人生命倫理中,體育正是對抗靜態生活的文明解藥。在人的生成中,體育是保護身體潛能的主動形式,因此,我們要用自醒的態度去認識體育,讓體育成為人主體存在的證明。
[注 釋]
[1]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注釋導讀本)[M].鄧安慶,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黑格爾.邏輯學:上卷[M].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3]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M].徐陶,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4]大衛·勒布雷東.人類身體史和現代性[M].王圓圓,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
[5]劉欣然,范婕.從身體哲學中尋找體育運動的哲學線索[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3(1).
[6]顧善光,周學榮.體育與人性——倫理視閾下身體危機的實質追問[J].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17(3).
[7]羅素.人類的知識——其范圍與限度[M].張金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8]汪民安.生產(第三輯):動物性[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9]休謨.人類理智研究[M].王江偉,編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103.
[10]劉欣然,周財有.體育運動中人類身體行為的哲學解讀[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0(9).
[11]張舜清.論荀子思想中的生命倫理意蘊及其獨特意義[J].孔子研究,2018(5).
[12]赫舍爾.人是誰[M].隗仁蓮,安希孟,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
[13]尼古拉斯·費恩.哲學:對最古老問題的最新解答[M].許世鵬,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14]蒂利希.存在的勇氣[M].成窮,王作虹,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
[15]蘭德曼.哲學人類學(2 版)[M].閻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
[16]操奇.底線生命倫理證成的可能性:生命間性論[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4(4).
[17]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M].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18]李澤厚.人類學歷史本體論[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19]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M].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0]許真,費利群.狄爾泰生命哲學對當代中國德育轉型的啟示[J].齊魯學刊,2018(1).
[21]理查德·桑內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繼宏,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22]劉森,丁素文.體育倫理與生命精神之契合[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5).
[23]斯蒂芬·霍爾蓋特.黑格爾導論:自由、真理與歷史[M].丁三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24]錢善剛.本體之思與人的存在——李澤厚哲學思想研究[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
[25]黃裕生.真理與自由——康德哲學的存在論闡釋[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26]黑格爾.邏輯學:下卷[M].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458.
[27]謝文郁.自由與生存: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觀追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8]李譜曼.善的無限性與生命倫理的實踐目的[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1).
[29]張麗娟.新時代體育倫理的當代關涉:難題與出路[J].體育與科學,2018(1).
[30]劉欣然.異化的拯救:體育與人主體性的現實困頓與本體超越——基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視角[J].體育成人教育學刊,20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