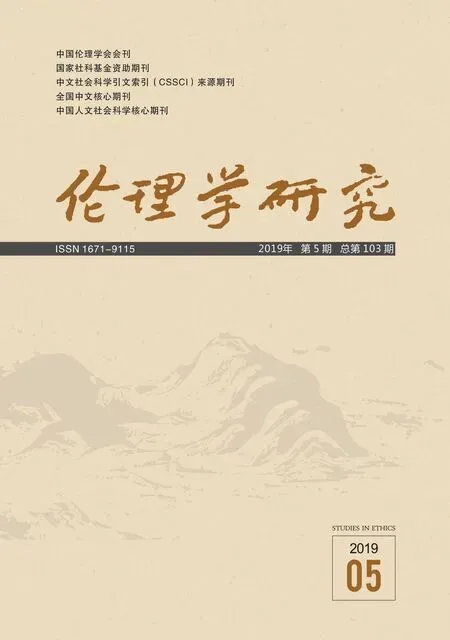道德增強與反增強的博弈與反思
陳萬球,周心怡
道德作為實踐理性精神,是人類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亦是人類自我完善主要方式之一。本世紀初以來,在歐美哲學倫理學界出現了一場關于能否進行“生物醫學道德增強”的論爭。爭論大致上可以分為增強自由主義和反增強保守主義。兩派理論上的爭鋒,演繹出21 世紀初人類道德發展的一幅嶄新圖景,具有重要的倫理意義。
一、道德增強派的倫理觀
增強派主張道德增強可以作為解決當前人類道德災難的必要強制手段,使人們生活在一個和平的世界中,以實現理想的道德社會,其中以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賽沃萊思庫(Julian Savulescu)、佩爾森(Ingmar Persson)、拉基奇(Vojin Ra-)和卡特(Sarah Carter)等人為代表。
1.道格拉斯:成為更好的自己
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是牛津實踐倫理中心與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學院的研究學者,也是研究道德增強的開啟人之一。他的貢獻在于以一個全新的視角定義了道德增強,并提出了應用理由。
道格拉斯早在2008 年提出了“生物醫學道德增強”,即通過適當的生物干預手段調節道德情緒。他認為一個人在道德動機上獲得了比原來更好的自己便可稱為“道德增強”[1]。從手段看,道德增強是以改善道德動機為切入點。大多數人在道德上都有明顯的提升空間,人們往往有不好的或不是最好的道德動機,但人們可以直接增強自身壞的或不是最優的道德動機[2]。被增強者在增強后,可獲得更好的道德動機。從結果看,道德增強可以使主體的道德能力和道德情操得到提升。通過道德增強,個體可以擁有更好的道德動機和道德情感,從而推導出個體實踐能獲得更多預期的或超預期的好結果。
道格拉斯提出道德增強也可是一種非道德的“減少”,即通過減少個體的反道德動機從而降低個體的反道德行為以在道德上成為更好的自己。這種“減少即增強”的論調是由于對道德“善”的定義和程度沒有一個具體統一的標準。比如,決定道德最好動機的是道德推理,還是道德情緒,還是兩者共同影響?如果道德推理和道德情緒共同作用于道德動機,那么兩者具體的影響占比分配是多少?以及道德“善”對不同的人或不同的角色來說存在不同的要求,就像法官應該更注重法律推理,而愛人之間則會更注重情感。
道格拉斯認為:應用增強道德的理由是,在道德動機上提升自己會得到盡可能多的道德行為及其產生的好結果,或增強對他人利益的關注[3]。
從客觀需求出發,一些社會危機,如貧困、氣候變化、戰爭等會隨著人類傷害能力的增加而增長,個體在應用道德增強技術提升自身道德水平之后,會表現出較少的偏見、攻擊、污染等情緒和行為,并能夠更多地與疾病和貧困進行斗爭,以及成為更好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因而道德增強的應用能夠有效地減少反道德或錯誤的行為,防止社會重大危機和威脅的出現,人類也會更多并僅僅是出于善良的道德動機進行社會實踐。
從主觀需求而言,道德增強則是一種對自我內在屬性的提升和一種自我完善的行為,說應用道德增強提升道德水準這一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善行”,并且保留無意義的不良道德動機不符合自我改善的意圖以及對道德提升要求。雖然道德增強的應用還存在一些爭議,如道德增強會提高被增強者的道德地位從而傷害未增強者。但從宏觀角度出發,道格拉斯認為道德增強并不一定會增加人類總體的所受傷害[4]。只要在能夠確保其技術相對安全的情況之下,沒有反對實現道德增強這一目標的理由。
2.賽沃萊思庫與佩爾森:急需發展更好的社會道德
賽沃萊思庫(Julian Savulescu)與佩爾森(Ingmar Persson)同為牛津實踐倫理中心的學者,其代表作有《道德增強,自由和上帝機器》《道德生物增強,自由和理性》等。兩位學者與道格拉斯一同稱之為道德增強理論的鼻祖,且一致認為人類迫切需要尋求任何手段在道德上得到改善以承擔正確使用現代技術的責任,其中便包括道德增強技術,進一步為應用道德增強技術尋找合理依據。
賽沃萊思庫與佩爾森認同道格拉斯對道德增強的涵義,并從兩個方面豐富了道德增強的內涵:其一,道德增強是為彌補現代社會中存在的落后的道德心理與先進的科學技術之間巨大差異的技術。人類過去長期生活在一個相對狹小而緊密相連的社會中,以往不發達的科學技術也只能影響最直接或較小的接觸范圍。人們延續至今的道德心理則是從這種有限的環境中發展而出的,其道德心理的考慮與思量也是短淺的,即僅限關注于周圍或眼前的人和事。如今,科學技術通過飛速發展已發生了多次量與質的飛躍,其影響范圍也已擴展至全球和遙遠的未來,已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條件,但人類的道德心理在整個技術和社會進化過程中始終保持著基本不變[5]。這種巨大的差異將導致人類在實踐生活中無法完全匹配現有的科學技術,從而科學技術的使用將可能嚴重破壞人類社會及其發展。例如,科學技術不合理的應用會導致惡劣的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等。其二,道德增強是一項需要社會全面且強制性實施的技術。道德水平較低的個體不會自愿、自主地進行道德增強,他們認為道德增強對自我而言是增加了一種負擔,并且非道德心理很容易對他人隱藏,但非道德心理很可能會對社會造成災難性的“人禍”。譬如,道德水平較低的個體或少數族群應用大規模毀滅性的核或生物武器爭奪日漸減少的自然資源或發動恐怖性質的戰爭。據此可知,道德增強不僅僅是單獨個體完善的追求,更是整體社會生存的需求。
同時,賽沃萊思庫與佩爾森提出人類迫切需要道德增強的訴求。他們認為由非道德心理所產生的傷害具有相對容易性,即“造成巨大傷害相對容易,比在同等程度上受益要容易得多”[6]。以殺戮和拯救為例,我們能夠在短時間內輕易地剝奪數條生命,卻無法在同樣條件下同樣輕松地拯救同等數量的瀕死個體。即便拯救死亡和剝奪生命一樣容易,我們的獲益也不會同我們通過傷害手段侵犯他人的程度一樣大。因為當我們殺害一個人時,我們可能消除了一個人生存條件中的任意一條,但被害者則是損失了所有未來可能的美好;而當我們拯救一個人時,我們不能對被救者未來所擁有的一切美好而邀功,畢竟拯救他的生命只是他擁有未來美好生活所必需的無數條件之一。
根據對道德增強的界定,傷害的相對容易性可以從兩方面進行避免。一是縮小道德心理與科學技術之間的差異。提升人類的實踐能力必須通過加速增強道德素質來縮小或平衡道德心理和科學技術之間的差異,把人類的道德關切擴大至自身的熟人圈之外,包括那些在未來可能有進一步接觸的人,否則人類文明將處于危險之中。二是預防和防止非道德個體和少數族群實施毀滅性行動。在傷害的相對容易性論點之下,就可成功假設少數不道德個體可以通過使用核或生物武器等先進的技術手段消滅地球上一切有知覺的生命,而我們無法也不能扭轉其毀滅的破壞性,以至于造成了終極傷害。相反,確保有價值的生命永遠存在這一終極利益則無法得到保障。那么道德增強一定要成為“普遍存在”且“強制實施”的技術,以提升全人類認知和非認知的道德,控制先進科學技術的部署和使用,將終極傷害發生的概率盡可能地減小[7]。
3.拉基奇:激勵自主的善良
拉基奇所倡導的道德增強,除了確保有效的安全性外,也保障個人自主選擇的權利。由于自由受到限制而被迫做出合乎道德行為的人,我們不能稱之為道德的人,因為自由意志是道德的基礎[8]。這似乎與賽沃萊思庫和佩爾森兩人強制進行道德增強的觀點相左,但他們卻也提出強制的道德增強不會限制自由,因為完全的自由意志與道德增強具有對立性。拉基奇則認為我們可以擁有完全的自由意志且不會限制道德生物增強的有效性。總而言之,我們能夠在不喪失自由的情況下,以有效的方式進行道德增強。另一方面,即便自由意志受到道德增強的影響,自由也將永遠是人類行為道德與否的判斷標準。人類擁有自主選擇是否應用道德增強技術在道德上得到增強的權利。只要我們是自愿的,我們便是自由的,是否進行道德增強依據是否自由來決定。有效的道德增強技術,只會改變或轉變我們的行動動機,但是我們的自由不會因此受到限制。換言之,自愿通過生物醫藥的手段提升道德,也能夠使我們表現得更加道德化的同時保持自由。
拉基奇指出成為一位道德行為者最大的困難在于,所做的事情與應該做的事情之間的差距。道德行為者不應糾纏于如何更好地理解道德知識,而應著手于如何加強自身的道德行為。道德增強的核心在于行為,而不是認知。盡管認知增強能夠幫助提升道德,可歸根結底,道德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讓人們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拉基奇認為解決這一難題的設想是“激勵善良”[9]。激勵善良不僅僅是國家政策層面的刺激與鼓勵,如提供各式福利等,而是更加著重于讓人們認識到善良是有助于他們獲得關于自我利益上更多的快樂。
“激勵善良”能夠由外至內促進人們自愿進行道德增強。一方面,將道德增強的獲益方由外部整體轉向到內部自我。“激勵善良”是為了讓我們相信道德的行為活動符合我們自身的利益,而不再是犧牲自我的舒適而降低或消除“終極傷害”發生的概率。另一方面,道德增強能夠通過外部技術解決自我內心痛苦。在我們理解道德與幸福相依存的關系后,我們渴望在道德上成為更好的自我。不過在目標實現的過程中,我們也可能會由于意志薄弱或缺乏足夠動機,導致無法達到或完成合乎道德行為的痛苦。此時,我們就有理由自愿運用道德增強補充道德意志和動機的軟弱之處,以消除無法完成目標無力感,從而采取更恰當或更道德的方式行動。
4.卡特:實現真正的自我
卡特(Sarah Carter)是曼徹斯特大學法學院社會倫理與政策中心的研究者,他增補了支持道德增強的論述,歸納總結了道德增強應用的間接與直接好處,并對道德增強的激勵措施進行反駁。
道德增強技術雖然在醫學上還存有疑慮,但卡特卻認同道德增強技術將會解決同情心缺失的問題,并給予被增強者間接和直接的好處[10]。
道德增強能夠使我們間接受益。道德增強與認知、記憶等方面的增強不同,并不能立即給被增強個體帶來直接的好處。但如果一個人作為社會的一部分提升自身道德水平,從而提升社會整體發展水平,那么這種對社會顯而易見的好處就可稱為道德增強的間接好處,即通過生物醫學的道德增強縮小人與人之間的差距,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只是缺乏同情心的人仍會覺得道德增強是一種負擔。由此可知,不管是道德檢測,還是道德增強技術的應用,目標人群的接受程度都可能不是很高。
道德增強的直接好處是:通過提升同情心水平減少不道德行為,從而減少參與可能導致對自身特別不利后果的活動。比如,會減少可能受到罰款、監禁等法律制裁的行為,或者避免成為類似群體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但是人們應用道德增強提升自身之時,不太能看到自己的獲益,接受道德增強程度也就不高,特別是認為缺乏同情心使得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更輕松的那些人。例如,在商業、醫藥、金融甚至犯罪等行業中生存的人,同情心的缺失似乎更是一種優勢,能夠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或是獲得更好的職業發展。他們對于冒著失去這一優勢的風險,而去提高對個人沒有明顯獲益的道德水平,這種可能性似乎很低。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道德增強對個人的直接益處。
卡特堅持道德增強對人們有間接與直接的好處,但是他也承認人們一直缺乏參與技術應用的情況。為了解決道德增強缺乏參與的問題,卡特提出了一種“實現真正的自我”營銷方案來增加人們對應用道德增強的參與度,從而取消具有嚴重爭議性的激勵措施[11]。
公眾對任何激勵自愿提升道德的提議可能漠不關心,甚至會引發道德憤怒。但當道德增強被描述為一種“實現”或“促成”更好自我的狀態時,人們不再會提出可能改變本我特質的疑慮,減輕對失去身份的擔憂。所以,“實現”或“促成”的營銷方案將減少冷漠的回應和避開道德的憤怒,而是讓更多的人自愿獲得一種擁有更好道德水平的愿望。
綜上所述,增強派從概念上進行闡述,認為道德增強是一項通過生物醫學科技增強人道德水平的技術,并在承認道德認知增強的作用外,更傾向于使用道德增強技術加強道德情感;從有效性進行論述,道德增強的發展和應用能夠完善個體的不足,并保障社會穩定且持續的發展。因為行善的動機能直接受到道德情感的影響,道德的知行合一才是道德水平的提升,畢竟知善不一定行善;從合理性角度分析,道德增強與自由意志、社會公平等問題不相沖突,甚至能夠擴寬自由與公平的上升空間;從實施方式進行考慮,道德增強可以通過各種激勵手段或實現自我的宣傳推廣吸引更多的人主動了解并自主接受,使道德增強達到預期的使用率。
二、反道德增強派的倫理觀
反增強派重視對技術后果的評估,對道德增強表示恐懼和不安,警惕人們防止將道德當作可以無限塑造的東西,其代表人物有哈里斯(John Harris)、芬頓(Elizabeth Fenton)、阿加(Nicholas Agar)、坦尼森(Michael N.Tennison)、馬塞洛(Araujo Marcelo)等人。
1.哈里斯:否定了善惡對稱性與行善可性能
哈里斯(John Harris)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兼大衛勛爵聯盟生物倫理學教授。他認為道格拉斯、賽沃萊思庫與佩爾森所提出的局限于生物醫藥手段的道德增強無法真正實現道德素質的提升,并對它們進行了反駁。在他看來,道德增強否定了行善與作惡的對稱性。哈里斯提出人類的行善能力與作惡能力具有對稱性[12]。相反,增強派則是推崇其“不對稱性”,而這也正是道德增強的核心吸引點,即能夠讓行善在短時間內變得同作惡一般“容易”。而當“不對稱”轉變為“對稱”時,對待道德增強也應轉變為不提倡的態度。盡管行善與作惡的對稱性可能會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出現特定方向的傾斜,但這種傾斜與反增強派所認為的作惡能力強于行善能力的觀念也存在實質上的差別。并且,行善與作惡的對稱性也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方面,如果作惡的全部負面結果能夠歸因于作惡者,那么行善的全部正向結果也可歸為行善者。增強派提出一位駕駛車輛于人口密集地區的司機能在短時間內傷害甚至殺害數量眾多的路人。但是在同一時間內,哈里斯認為一個人也可以通過阻止另一個打算實施大規模侵害他人利益的罪犯成為與罪犯作惡能力相對應的行善英雄。另一方面,作惡的全部負面結果不能只歸功于作惡者,而是需將作惡結果的影響力分攤部分至外部環境的條件之中。例如,開車撞死大量無辜路人的案例,必須要有結實的汽車、提供加油的加油站、平坦的道路以及大量的人群等等條件和因素才有可能形成。
哈里斯以米爾頓《失樂園》中“平穩的站立,當然也有墮落的自由(Suffcient to have stood,though free to fall)”[13]為依據,提出道德增強限制了自由意志,從而可能使我們只知行善卻不知為何行善。當我們應用道德增強或啟用“上帝機器”而放棄墮落的自由之時,人們也就喪失了自主選擇是否行善的權力,行善將毫無價值[14]。美德不存在于必須做的事中,美德體現在邏輯的選擇之中,自由的消失必然導致美德的消散,甚至導致道德的淪喪。其一,道德是綜合考慮下最優的選擇,而不僅是其行動中包含有良好的動機或親社會屬性。其二,行善不簡單是作惡的對立面,而是基于邏輯推理的選擇。作為通過自然的選擇進化至今的人類,并且具有維持社會運轉至今的社會秩序,可以說我們都有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人類既擁有自由,也具有大量的公平與正義;既要努力知善,也要盡力行善。
而在知善與行善間的區域是人類可以完全且自由地進行行動[15]。因此我們依舊可以通過傳統的道德教育,教育人們善惡對錯,避免對他人造成傷害或給他人帶去痛苦[16]。換言之,通過學習和吸收道德知識,來獲得以尊重他人的方式去體會他人感受的利他主義和移情能力。道德知識也能像其他所有科學知識一樣能夠得到提升,確保了習得道德知識的可行性。在接受可靠的認知增強之前,我們應致力于盡快增強自身的道德知識能力和水平,從而使自身的道德獲得增強,以便更好地幫助人們了解善行,了解可能有助于善的東西,并達到個人或整體所期望的自我防衛能力。例如,減少鄉村白癡的數量和種類。而世界可能面臨的巨大威脅也不僅僅源于不道德,還可能是由于自然環境的巨變、愚蠢或粗心大意的疏忽等各種情況所引起。
2.芬頓:認知增強破解道德增強的內在矛盾
芬頓(Elizabeth Fenton)是哈佛大學倫理與健康項目的研究學者。他揭示了賽沃萊思庫與佩爾森所提出的道德增強在很大程度上嚴重低估了重大科學進步的益處,由此會引發道德增強的兩難境地——增強會滅亡,不增強也會滅亡,并提出非傳統認知增強能夠替代道德增強以擺脫發展困局。他的觀點主要在《增強失敗的危險:對佩爾森和賽沃萊思庫的回應》中體現。
芬頓認為賽沃萊思庫與佩爾森所提出的道德增強具有內部矛盾性。道德增強的發展需要科學技術的發展,但科學技術的發展可能增大出現“終極危機”的風險。一方面,賽沃萊思庫與佩爾森覺得人類社會急需道德增強提高整體道德水平,這也就意味著需要科學技術的大力發展,推動道德增強的成熟與應用;另一方面,他們卻提出在當前較高的科技發展程度之下,擁有較低的道德水平的人類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只會增加世界毀滅的危險,避免這一情況的發生似乎需要減緩或停止科學技術的研究與發展[17]。
簡言之,科技進步似乎是一把“雙刃劍”,既能發展我們,也能毀滅我們,但這并不是芬頓所反對的地方。芬頓批駁賽沃萊思庫與佩爾森的道德增強發展和應用的前提,即高估了道德增強應用的有效性和道德缺陷附加的風險性。首先,科技進步的益處不能被人類毀滅的風險性抵消。當人類處于由自然或非自然條件造成的惡劣環境之下,唯有科技的發展才能使我們擺脫逆境。其次,人類能夠承擔獲得科技發展利益的風險。芬頓承認道德的缺乏確實能造成重大災害,但引起毀滅性災難的發生概率卻極小,并且毀滅性的災害不總是道德缺乏所帶來的,也可能是自然原因所引發的。同時,道德增強的應用也不能確保毀滅性災害的消失。
芬頓認為道德增強的可替代性,即非傳統的認知增強能夠替代道德增強。非傳統認知增強是指通過一系列生物醫學的手段加強人類的認知能力[18]。因為非傳統的認知增強既能夠避免人類陷入技術進步的兩難困境,也能夠推進道德素質的整體提升。芬頓批判賽沃萊思庫與佩爾森嚴重低估了非傳統認知增強的價值,并從兩方面進行理解:一是非傳統的認知增強與科技發展相輔相成。非傳統的認知增強能夠通過生物醫藥方式快速增加人類的認知能力,從而加快科技進展的步伐。科技的突破性研究也能增加非傳統認知增強技術的成熟,幫助人類擺脫生存困境的威脅。二是認知增強也是道德增強的先決條件。非傳統認知增強更能提高我們對道德的理解,讓我們獲得更多的道德動機,以達到“知善行善”的境界。
3.阿加:失衡的道德情感與無益的道德地位
阿加(Nicholas Agar)是新西蘭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哲學博士。他否認賽沃萊思庫與佩爾森關于道德增強技術能夠防止“終極傷害”發生的觀點,而主張道德增強是危險的,認定傾向于增強道德情感的道德增強必然會導致社會道德滑坡的狀況。
道德增強可能會導致道德惡化的原因之一,是因為道德增強對道德思維過度不平衡的影響。人類的道德推理和判斷依賴于個體的心智能力,并最終影響人類的道德行為,因而情感反應的變化通常伴隨著道德推理的改變[19]。只是道德增強對道德情感“過度”干預,雖然被增強的個體能擁有更強烈的共情能力,但共情能力的增強不一定會導致好的結果。道德增強可分為橫向增強和縱向增強兩種:橫向增強是指被增強者能夠與更廣泛的群體產生情感共鳴;縱向增強則是意味著加深被增強者對某一事物的同情心[20]。以催產素為例,催產素的應用確實會增強個體對群體內人員的同情心,但過量使用催產素進行道德增強則會深化縱向增強的程度,加大個體對群體外人員的排斥心理,這很容易導致被增強者超越人類道德的規范,破壞理性和情感的平衡狀態,進而造成道德滑坡。
正確的道德判斷是在感性的共情能力和理性的道德推理之間達到了一種特殊的平衡。道德增強的成功運用不能避開對人類理性的加強,道德增強的失敗嘗試則可能導致道德災難的結果。當我們權衡與我們毫無關系的陌生人和與我們有著親緣關系或聯系緊密的人群利益時,我們會發現我們很可能會更傾向于與我們更為親近的人,而不平衡的道德增強可能會加劇這一情況的傾斜程度,我們甚至可能犧牲陌生人來換取親緣關系人群的利益。
阿加極力批判人類在道德上需要特殊援助的觀點。他指出道德增強會使被增強者的道德地位提升,甚至高于原本最高位的人格地位[21]。一旦擁有更高道德地位的被增強者產生了需求,則必然會優先于未增強者的需要,這意味著未增強者更有可能在極端緊急的情況下被迫做出犧牲。然而類似于“終極傷害”的極端情況似乎并不常見,未增強者犧牲的數量也就相當之小,但無法避免道德地位較高的被增強者利用道德地位較低的未增強者以換取更多的利益。畢竟資源的分配一般是優先滿足地位較高之人,再分發給地位低下之人。
同時,阿加通過對人的非關系屬性和關系屬性的分析得出,人人都擁有最高的道德地位,并且不能通過犧牲他人來換取利益[22]。據此,可將此細分為三層含義:其一,被增強者所得到的任何利益,在道德上不能補償未增強者所付出的代價;其二,被增強者道德地位的提升也表示將未增強者驅逐出最高道德地位的位置;其三,未增強者的道德地位降級使他們為被增強者提供重大利益的犧牲看似具有合理性。因為,道德上允許犧牲道德地位為零的事物為有知覺的人提供利益,如犧牲有知覺的非人類為人類創造福利,那么道德上似乎也就允許犧牲未增強者使被增強者獲益。如果被增強者是合理的,那么被增強者的價值可以高于未增強者的價值,這將嚴重違背人人平等的人格地位。
綜上,反增強派反對道德增強的應用,提倡認知增強的手段加強道德素質。認為道德增強實施存在多種困難和難題。首先,道德增強技術成功實施存在錯誤的內部邏輯。反增強派否認了道德增強的發展可能基于善惡的不對稱性,并指出增強派存在著科技和認知發展的矛盾性。其次,道德增強的實施標準具有模糊性。道德增強所增強的質與量沒有明確標準,而技術的過度使用也會引發一系列問題,如自由、公平、安全和人格等相關難題。由此,反增強派提出道德增強的替代方案——認知增強。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斷應該更多地依賴于理性認知,不管是傳統認知增強和非傳統認知增強都可有效提升道德素質,避免道德增強帶來的困境或災難。反增強派的觀點沒有明確分為強反對派和弱反對派。不過反增強派的觀點能夠較好地辯駁強增強派的思想。反增強派提出一種較強硬的反對意見,指責道德增強技術是一種絕對意義上令人反感的手段,因為它具有與某些意圖或目標結合的非自然性,卻不針對人為的治療和自我教育[23]。但是反增強派卻對弱增強派理論的反駁較弱。
三、道德增強與反增強論爭的倫理意義
道德增強之辯有利于反思技術與道德的關系,拓展理論倫理學的視野,進一步豐富規范倫理學的內容,發展美德的相容性以及完整性,拓展應用倫理學的方法,促進技術與道德的協調發展。
1.豐富規范倫理學的內容
從規范倫理學看,道德增強的主要問題是:從規范倫理學的利益沖突視角出發,道德增強與自由意志似乎具有地位高低的爭議;從規范倫理學的道德難題角度出發,道德增強與公平公正似乎存在對立關系;從規范倫理學的差異性出發,道德增強與標準規則不具有統一性。然則不管哪種類型的規范倫理學問題,我們都可運用“利益同一性”——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具有同等性的原則解決。由此可解答出上述三個問題:一是道德增強的應用應確保個體保有足夠的自由意志。可以通過道德增強去除超過保證自身生存所必需的非道德情感、動機和行為,而不是濫用“自由”的名義滿足一己私利而傷害他人的利益。道德增強不應是一種類似于“上帝機器”的技術——忽略個體與之設定有所偏差的思考、違背個人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而應是保證個體在自由思考的同時更貼近高水平的道德修養。二是道德增強也需要在保證社會原有公平狀態下進行實施。道德的要求中就包含了公平,道德水平得到提升,公平意識也會隨之提升。可是當道德增強被巨大的市場財富或極端的個人權利所操控,一部分被權利和財富所引誘的人便會忽視他人利益,違反公平原則導致道德增強與社會公平相對立,進一步擴大“馬太效應”。因而道德增強需要政府和民眾強有力的監管,并對其進行普遍而廣泛的推廣活動,大大降低技術獲得的門檻。三是道德增強可以加強不同倫理學之間統一的道德基礎。不同的倫理學準則都應在堅守自由和公平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仁愛要求。道德規范不僅僅只局限于維持人類正常的社會生活,還需要增加更多面向所有人的仁愛之情。那么即便不同的倫理學之間存在差別,但其底線則是大致相同的,即不傷害、自由、公平和仁愛,不同社會或群體間的倫理學也就不會產生本質上的對立,獲得普遍化的全球道德增強倫理。
2.發展美德倫理的相容性
道德增強能發展美德的相容性以及完整性。一方面,道德增強既能夠增加美德間的相容性,也能夠減少價值與美德間的分裂。道德增強能夠幫助個體突破原本個性的局限,使個體更容易孕育和發展出更多的美德,實現各美德間真正的相容。同時,道德增強能夠幫助個體擺脫特定生活形式價值的限制,拋棄選擇一種美德就必須放棄另一種美德,創造出滋長更多美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道德增強能夠實現真實完整的自我。美德倫理學中“真實的自我”強調自我前后一致的同一性,反對個體的同質性。道德增強促進個體幸福生活目標的達成。每個人都以幸福生活為奮斗目標,雖然各自對幸福生活的規劃各有不同,不過道德增強只是發揮個人內在的道德潛能,幫助每個人實現他們不同的幸福規劃。道德增強提升個體對美德在具體場景中獨特的理解。在每個千差萬別的情景中,道德增強能夠協助個體理解不同的場景,將個體利己與利他的心態調整至場景所需的最佳狀態,也就能夠保留并凸顯個體的同一性。道德增強同樣能夠發展美德形成所需的教育與習慣。道德增強能夠提升美德教育的成效。道德增強能促使被增強者從道德情感和道德認知兩方面得到提升,因此不論是美德教育者,還是美德習得者都能從情與理視角增加對道德知識的認同與接受程度。道德增強能夠提升美德教育的啟發性。啟發式美德教育更多側重于培養個體的自主性,即道德方面的自律性與自覺性。美德的習得不僅是依靠他律性的社會規范與輿論監督,更需要自身時刻的約束與謹慎的權衡。道德增強可以幫助被增強者達到“獨善其身”的美德境界。道德增強促使個體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習慣能使我們對正確行為的道德情感更為敏銳[24]。道德增強能夠進一步將美德生活化,促使人們在實際生活中更多地感受并注重道德,進而在習慣的力量上更加認同與道德原則相符之事,更加厭惡與道德對立的邪惡之事。
3.拓展應用倫理學的方法
個體在道德增強的實踐中需要有正確的倫理指引。首先,需充分利用個體的知情同意權。在醫療實踐中,知情同意權是個體最基本的權利之一。但根據中國醫療實踐中,知情同意權具有獨特的“權威主義”和“家庭主義”特色[25]。不涉及生命和死亡的道德增強,醫護人員能與成年的道德增強受施者直接溝通。而對未成年人的增強,除了尊重本人的意愿之外,也必須征求其監護人的同意。其次,需明確道德增強的應用是對個體“真實自我”的實現,即個體不應將道德增強作為一種超越他人或自身能力的工具,而是應視為“自我意愿”達成的補充方式。據此,從結果主義出發,可分為兩層含義進行分析:一方面,道德能力精準評估的高難度促使“個體超越”的無意義。因此,個體如果使用道德增強的目標如以“超越他人,多享資源”為核心,則道德這一技術毫無意義可言。另一方面,“真實自我”的實現能夠更好地促進個體道德增強的意愿。道德增強應用的目的與個體一直期盼著美德造就的幸福生活一致,并不會造成個體自我人格分裂的擔憂,而是對自我的增益。再次,需明晰道德增強是個體在傳統道德增強之下的有益補充。個體為了發展更高水平的道德心理,可使用道德增強突破自己原有的自然限度,但為了保持人類的社會性,以及為了避免傳統方式能夠達到預期目標卻仍用技術方式進行替換的不必要的技術實施風險,從而不直接放棄道德增強的傳統方式而通過技術手段進行全面的突破和改變。
四、結語
生物醫學道德增強之辯源自增強派與反增強派基于道德理念上的迥異,從某種意義上說,增強派和反增強派激烈的辯論,實質是高新技術發展條件下道德自然主義與道德非自然主義的理論爭鋒的翻版[26]。增強派遵循著道德自然主義原則,指出道德的產生基于人類的生理基礎,生物醫學道德增強的可能性與發展性也是以人類自然的物質性為基礎,從而改變人類與道德相關的生理條件便能改變人的道德情感與道德行為。然而,當增強派走入極端道德自然主義時,道德便開始“物化”只依賴于人的自然物質性,卻忽略了文化、宗教、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因素。反增強派則偏向道德非自然主義的立場,相信道德源于最佳的自由邏輯推理,而不是來自具有自然特征的客觀存在。不過,反增強派也可能步入道德非自然主義的謬論之中,道德及其價值都是虛無的。而這一爭論可以通過傳統與非傳統道德增強方式的融合而完成:雙方相輔相成,將生物醫學道德增強技術作為傳統道德增強的一個補充方式,既能以傳統方式限制人類技術化的程度以降低道德增強技術的風險,又能用技術手段增加傳統教化方法的效能,最終獲得應用道德增強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