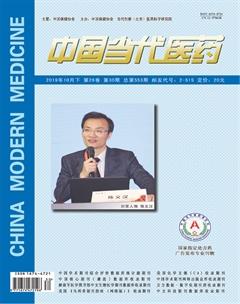李合國教授辨治口臭經驗總結
王坡 李合國
[摘要]口臭是一種常見的臨床疾病,表現為口中散發臭氣,多為他人聞到,患病率較高,發病人數多,嚴重影響人們正常的人際交往、情感交流及身心健康發展。關于口臭的病機,歷代醫家各有不同的闡述,目前歸納大致可分為四類:胃熱熾盛證、食滯胃腸證、肝氣犯胃證和肝胃郁熱證。口臭多與消化系統疾病有關,臨床上發現口臭的病機多與脾胃肝膽濕熱、脾胃虛弱、寒熱錯雜等相關,并在治療的過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李合國教授長期從事消化系統疾病的治療,對口臭治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總結李合國辨證論治口臭的經驗,以期為臨床上治療口臭提供思路方法及參考。
[關鍵詞]口臭;幽門螺桿菌;李合國
[中圖分類號] R276.8?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9)10(c)-0126-03
[Abstract] Bad breath is a common clinical diseas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mell of odor in the mouth and mostly smelled by others, the prevalence rate is high, and the number of cases is high,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people′s norm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Regarding the pathogenesis of bad breath, the doctor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hav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At present, the induction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stomach heat stagnation syndrome, food stagnation gastrointestinal syndrome, liver qi stagnation stomach and liver and stomach stagnation syndrome. Most of the bad breath is related to digestive diseases. Clinically, the pathogenesis of bad breath is related to spleen, stomach liver and gallbladder damp heat, spleen and stomach weakness, cold and heat miscellaneous,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Professor LI He-guo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treatment of digestive diseases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the treatment of bad breath.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LI He-guo′s experience in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bad breath,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bad breath.
[Key words] Bad breath; Helicobacter pylori; LI He-guo
口臭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及正常的人際交往,因口為脾之竅,口臭病機多考慮胃火或食積所致,多從清胃火、瀉濁通腑立法出藥。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胃火熾盛導致的口臭少見,臨床上多見肝膽濕熱、脾胃濕熱證,因五臟六腑氣機不調,郁而化熱,皆可導致口臭,非獨脾胃也,而脾胃肝膽濕熱,濕與熱結,纏綿難愈,又與口臭癥狀長期持續暗合。李合國教授,全國名老中醫學術繼承人,師承首屆國醫大師李振華教授,跟師全國名老中醫北京李乾構教授、全國名老中醫河南李發枝教授學習。臨床上擅長治療內科常見病,中西醫結合治療疑難雜癥,對消化系統的診治,充分發揮中西醫結合的優勢,取得顯著療效,尤其對口臭的治療。中西醫結合治療,一般治療為2周,治療后后期不宜復發。
1口臭的危害
口臭是指從口腔或其他充滿空氣的空腔中如鼻、鼻竇、咽所散發的臭氣。現代醫學認為口臭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口腔內厭氧菌生長,從而產生揮發性硫化物而引起的。根據其發病特點和臨床表現,可歸屬于中醫“口穢”“濁氣”等范疇。世界各國流行病學調查顯示,相當比例的人患有口臭,患病率為14%~83%[1]。口臭患者在焦慮、抑郁、社交回避和苦惱方面的心理狀況明顯較非口臭人群差,嚴重影響其心理健康。潔舌、潔牙等物理治療,雖然短期內可改善口臭狀況,但長期療效不盡如人意;藥物治療方面,多使用抗生素,抗生素雖會抑制一部分菌群的生長,但另一部分菌群大量繁殖,菌群失調,以致人體患病[2]。
2口臭的產生機制
口腔氣味的來源主要是口腔細菌分解氨基酸的代謝產物,這些代謝產物包括多種化合物,如吲哚、糞臭素、二元胺類(尸胺、腐胺)以及揮發性硫化物(VSCs)。目前研究較多的主要是VSCs,VSCs包括硫化氫、甲硫醇、二甲基硫醇、二甲基二硫醇等。與口腔臭味有關的是前三種,因為它們都含有能發揮活性作用的巰基(-SH),其在低濃度就能發出強烈臭味。而二甲基二硫醇由于沒有巰基,與口臭的產生基本無關。VSCs作為口腔臭味的主要成分,由牙周袋內的或舌苔內的G-厭氧菌產生[3]。
3口臭的歷史沿革
中醫學對口臭記述頗早,又名出氣臭、口氣臭、口氣穢惡、息臭等,認為口臭是五臟六腑功能失調的結果,其中關鍵在于脾胃功能失調。《諸病源候論·口臭候》認為口臭是由于五臟六腑氣機不調,氣壅胸膈,郁而化熱,上沖于口,導致口臭。《景岳全書》認為口臭多由胃火或心脾虛火所致,提出清胃熱、補心脾的治法。脾胃位居中土,是人體氣機的樞紐,脾升胃降,使得氣機上下協調平衡,若脾胃不和,脾不升,胃不降,中焦氣機不調,濁氣上泛脾竅,以致口臭[4]。
4李合國教授中西醫方法治療口臭
口臭是一種自我感覺或他覺的癥狀,致病因素多種多樣。口臭可分為生理性口臭和病理性口臭,對于生理性口臭不僅與進食刺激性氣味的食物,如大蒜、蔥等有關,而且與饑餓及女性生理周期有較大的聯系。病理性口臭大致可以分為口源性和非口源性兩種。非口源性口臭主要由患者系統性疾病所致,各系統均存在致病因素,主要有呼吸系統(鼻竇炎、鼻炎、下呼吸道感染等)、消化系統(胃炎、腸炎、肝臟疾病及消化系統癌癥亦可以導致),一些全身疾病,如糖尿病也可導致非口源性口臭。口源性口臭占病理性口臭的一部分,口腔中舌乳頭的解剖生理結構為細菌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溫床,其巨大的表面積存貯了食物殘渣,從而滋生大量的細菌,主要是厭氧產硫菌分解形成VSCs從而形成口臭[5]。
對于非口源性口臭多考慮幽門螺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目前對于Hp導致的口臭原因尚不十分清楚,Hp是引起上消化道各種病變的重要病因之一,當存在該菌感染時,胃腸消化吸收的功能及胃動力可能受到損害,可能導致食物殘渣在胃腸中潴留時間過長,經胃腸道內其他細菌腐敗分解產生各種有臭味的氣體。同時相關研究發現,Hp感染可誘導相關基因,如胱硫醚-γ-裂解酶(cystathioniner-lyase,CSE)、胱硫醚-合成酶(CBS)等基因以及編碼炎性因子:白介素(interleukin,IL),如IL-1、IL-6和IL-8基因的高表達,使得機體自身產生的H2S大量增加,引起口臭[6]。
對于口臭患者的治療,首先排除口源性口臭,治療多從非口源性口臭入手治療,建議患者通過C13或C14呼氣試驗檢測Hp,若結果為陽性,考慮Hp感染,進行四聯殺菌治療,治療周期為14 d,停藥1個月后復查C13或Cadb呼氣試驗,若復查結果為陰性,則為殺菌成功,若復查結果仍為陽性,可更換四聯殺菌方案中的抗生素,進行再次殺菌。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是Hp高感染區[7],因此清除Hp方案被高度重視,在第五次全國Hp感染處理共識報告中推薦鉍劑四聯作為主要的經驗治療根除Hp方案(推薦7種方案)[8],其中阿莫西林和克拉霉素的鉍劑四聯方案,具有較高的Hp根除率,安全性高、依從性好[9],因此殺菌方案抗生素的組合首選阿莫西林和克拉霉素。由于抗生素在去除Hp感染過程中的普遍使用[10],耐藥菌株也在逐年增加,阿莫西林(0%~5%)、四環素(0%~5%)和呋喃唑酮(0%~3%)的耐藥率尚較低[11];對于首次清除Hp失敗后,可選取耐藥率較低的抗生素進行組合。對于對青霉素過敏的患者,可選擇呋喃唑酮和四環素或呋喃唑酮和左氧氟沙星。當然對于兒童Hp感染,首選質子泵抑制劑(PPI)+克拉霉素+阿莫西林,療程為10 d或14 d,青霉素過敏者可選擇甲硝唑[12]。如果患兒為過敏體質,則慎用殺菌方案或先給予1周殺菌方案,并囑咐其如果出現過敏,應立即停藥。
目前傳統清除Hp的三聯療法根除率正在逐年降低,鉍劑四聯療法(鉍劑和PPI聯合兩種抗生素)是我國根除Hp的一線治療方案,雖然其療效顯著,但仍存在諸多問題。由于鉍劑可引起黑色絨毛狀舌苔,、糞便灰黑、腎功能損傷以及鉍性腦病;抑酸劑可引起皮疹、皮膚瘙癢、外周神經炎以及肝臟轉氨酶的一過性升高,大量長期服用抗生素可引起胃腸道菌群失調,進而發生腹部不適,常見腹痛、腹脹、腹瀉、食欲減退、口臭等不良反應,從而導致患者服藥的依從性減弱,治療效果不佳[13]。
中醫治療口臭,以辨證論治為基本原則,因證遣方,依方選藥,故證型不同,治療亦不同,現將臨床上常見的證型歸納如下。
4.1脾胃濕熱型
口苦口臭,大便不成型,納呆,口黏,渴不多飲,腹部脹滿,舌偏紅或暗紅,苔黃厚膩,方選三仁湯加減。
4.2寒熱錯雜型
口臭口干,復發性口腔潰瘍(1年發作次數>3次),大便不成型,胃脘部痞滿不適,舌淡,苔薄白,齒痕舌,方選甘草瀉心湯加減。
4.3肝膽濕熱型
口苦口臭,厭油膩,脅肋部不適,小便黃,大便不調,陰囊部潮濕,脈弦數,方選龍膽瀉肝湯加減。
4.4少陽郁熱型
口臭口苦,咽干口渴,自覺眼昏,脈弦,舌淡紅苔薄白,方選小柴胡湯加減。
4.5脾約型
口臭,大便干結,或靠藥物排解大便,小便正常,脈細弱,方選麻子仁丸加減。
5驗案舉例
段某,男,63歲,主訴:口苦口臭、口干1年余。
既往史:高血壓,160/100 mmHg,口服杜仲平壓片,控制差,腦梗死,脂肪肝。2018年6月22日初診:偶有反酸、燒心,納可,大便不成型,日1~2次,舌暗紅苔黃厚膩,脈弦細。
輔助檢查:C13呼氣試驗 DOB 23.7。
西醫診斷:Hp相關性胃炎;中醫診斷:口臭。
證型:脾胃濕熱證;治法:清利濕熱、宣暢氣機。
西藥治療:阿莫西林1000 mg,2次/d;雷貝拉唑鈉腸溶片20 mg,2次/d;克拉霉素緩釋片0.5 g,2次/d;枸櫞酸鉍鉀1.08 g,2次/d。服用14 d,雷貝拉唑鈉腸溶片、枸櫞酸鉍鉀餐前服用;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緩釋片餐后服用。
中藥治療:薏苡仁30 g,杏仁10 g,蔻仁10 g,淡竹葉15 g,厚樸20 g,川木通10 g,滑石30 g,清半夏12 g,海螵蛸30 g,浙貝母15 g,龍膽10 g,14付,水煎服,日1付,早晚餐后半小時后服用。
二診:反酸燒心消失,口干口苦減輕,仍口臭,二便調,繼服上方14付。
三診:口臭口苦消失,復查C13呼氣試驗DOB 2.9。
按:Hp感染患者中醫證型以脾胃濕熱證為常見[14-15],濕性黏膩,病程長;西藥四聯殺菌治療Hp感染確有一定的效果,但抗生素的廣泛使用容易產生耐藥,而且還會引起胃腸道及中樞神經系統的不良反應;中西醫配合既能清除Hp,又能減少抗生素所導致的不良反應。
綜上所述,對于口臭患者,李合國教授首先詢問其有無口腔疾患,排除口腔疾患,詢問患者口臭是自己感覺還是他人聞到,以排除精神因素,考慮Hp感染,建議患者做C13呼氣試驗,若陽性,治療口臭選用四聯殺菌方案,其中抗生素選用阿莫西林、呋喃唑酮、四環素等耐藥率比較低的抗生素[16],以防產生耐藥,致使殺菌失敗。中醫方面治療口臭,臨床上以脾胃濕熱證型為多見,濕性黏滯,不易去除,常采用三仁湯加減。三仁湯為《溫病條辨》重要方藥,具有清熱利濕、宣暢濕濁之功效,方用苦杏仁宣通上焦肺氣,使氣化有助于濕化;豆蔻開發中焦濕滯,化濁宜中;薏苡仁益脾滲濕,使濕熱從下而去;法半夏、厚樸除濕消痞,行氣散滿;通草、滑石、淡竹葉清利濕熱。諸藥合用,共成宣上、暢中、滲下之功[17],配合芳香化濕之品,如廣藿香、佩蘭等。預防脾胃濕熱的發生必須改變不良的生活方式,注意顧護脾胃,做到飲食有節,盡量不吃辛辣厚味之品,如韭菜、大蒜等,杜絕濕熱之源。在服藥的同時忌生冷辛辣油膩,避寒涼,尤其是水果,若要食用,水果可以燙熟了以后再服用,避免助濕(中醫認為水果多屬寒涼之品),皆因寒涼生冷易傷脾胃陽氣,致運化無權。辛辣之品易致病邪化熱,形成濕熱之證。
[參考文獻]
[1]詹婧彧,陳曦,馮希平.口臭的流行特征及其有關因素[J].口腔材料器械雜志,2013,22(4):215-218.
[2]李龍英,董雷飛,周素芳.吳文堯教授辯治口臭醫案2則[J].中西醫結合心血管雜志,2019,6(27):184-185.
[3]馬駿馳.口臭的研究現狀[J].廣東牙病防治,2002,10(2):149-150.
[4]崔淑華.運脾湯治療口臭52例臨床觀察[J].河北中醫,2007,29(9):792-793.
[5]刁輝明.探討口源性口臭的產生原因與治療方法[J].中國醫藥指南,2012,10(32):163-164.
[6]張羽,陳曦,馮希平.口臭與幽門螺桿菌感染的關系——病例對照研究[J].口腔醫學,2016,36(7):607-611.
[7]謝川,呂農華.中國幽門螺桿菌感染的現狀[J].疾病監測,2018,33(4):272-275.
[8]劉文忠,謝勇,陸紅,等.第五次全國幽門螺桿菌感染處理共識報告[J].胃腸病學,2017,22(6):346-360.
[9]郭濤,王強,吳晰,等.阿莫西林和克拉霉素的鉍劑四聯方案作為初次根除幽門螺桿菌治療的1年隨訪結果[J].中國醫學科學院學報,2019,41(1):75-79.
[10]丁曉蕊,賈興芳,劉成霞.幽門螺桿菌對抗生素的耐藥機制進展研究[J].中外醫療,2018,37(20):193-195,198.
[11]劉文忠.努力提高幽門螺桿菌根除率(一)[J].胃腸病學,2016,21(8):450-454.
[12]胡馨月,李莉.兒童根除幽門螺桿菌感染[J].內蒙古醫科大學學報,2018,40(S1):256-259.
[13]薛百釗,李志婷,郜宏,等.中醫藥在幽門螺桿菌根除治療中的作用研究進展[J].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2018, 18(45):87-89.
[14]劉建平,趙源,郎曉猛,等.幽門螺桿菌相關性慢性胃炎中醫證型分布研究[J].湖南中醫雜志,2017,33(9):12-13.
[15]趙剛,馮媛媛,劉宣,等.慢性胃炎中醫證型分布及幽門螺桿菌感染情況分析[J].上海中醫藥雜志,2017,51(6):21-23.
[16]李世通,楊兵.幽門螺桿菌流行病學及耐藥性研究現狀[J].臨床醫藥實踐,2016,25(1):53-55.
[17]高建忠,于曉強,王平.三仁湯方證臨證解讀[J].世界中西醫結合雜志,2016,11(7):1002-1006.
(收稿日期:2019-03-18? 本文編輯:任秀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