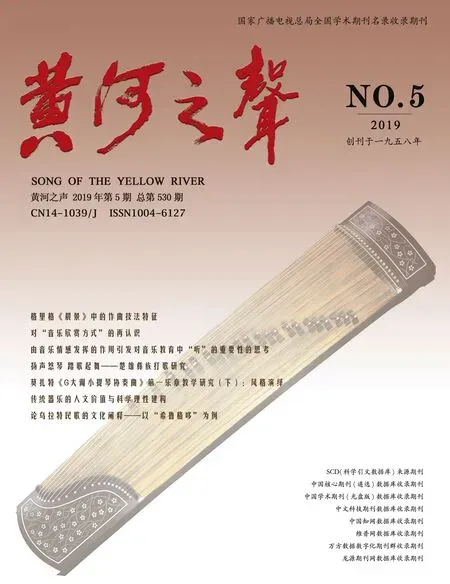逃不出的“宿命論”
——《菲岱里奧》思想寓意評析
孫濟方
(河南大學,河南 開封 475001)
貝多芬與同代的兩位巨匠海頓和莫扎特相比,他的偉大向來不是以數量取勝。九部交響曲雖不及海頓的零頭之多,但每首皆可稱傳世精品。而在一生少有觸及的歌劇領域,《菲岱里奧》是貝多芬的唯一遺產,也是從歌劇領域透入貝多芬內心世界的獨木橋,從歷史或審美角度來看,價值意義無疑都是巨大的。說起這部由讓·尼可萊·布伊利原作,約瑟夫·索恩萊特納改編腳本;偉大的貝多芬譜曲;閃耀著人文主義關懷的作品,就不得不提的是它那如同法國大革命一般命運多舛的誕生之路。從1805年歌劇的首演開始,直至1814年貝多芬的最后一次修改,期間三次大改,光是流傳下來的序曲就有四首之多。如果說這部作品的內容、形式均隱含了典型的貝多芬性格的話,而依筆者看,作品的創作之路,與傳統的“貝式”印象可謂相去甚遠,傾聽意見、反復修改這在貝多芬的其他作品中是少有的情況,但這也從側面反映了貝多芬對這部“獨苗”的悉心呵護。
眾所周知,1802年貝多芬執筆寫下了著名的“海利根施塔遺書”,學界大多以此為界,將從1802年到1814的貝多芬的創作生涯,歸入到第二時期。在此期間貝多芬褪去了在波恩和初來維也納的青澀,以及早期作品中滲透的“海頓式的娛樂精神”,思想境界達到了新的層面,雖然與晚期《第九交響曲》和《莊嚴彌撒》所傳達出對宗教、人性等多方面深邃洞見不能相比,但該時期無疑是最能代表貝多芬的一段時期,堅定、狂熱的英雄崇拜;永不放棄的命運抗爭,如《第二十三鋼琴奏鳴曲“熱情”》、《“皇帝”協奏曲》、《第三交響曲“英雄”》以及《第五交響曲“命運”》,無一不是貝多芬標簽式的作品。而這份情感也驅動著貝多芬在歌劇領域創作中,自然而然的選擇了當時最應景以及符合其特質的一類題材--“拯救歌劇”。
關于“拯救歌劇”(rescue opera)的“語義場”因篇幅不再贅述,僅作簡要釋義。“拯救歌劇”,源自于18世紀后半葉法國大革命興起前后,隨著革命的節日慶典而發展,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本身脫胎于喜歌劇“opérascomique”,所以在形式上與其相類似,帶說白;以簡短的詠嘆調和重唱、合唱構筑整體。而在內容上無一外乎,均為嚴肅題材并且在人物和情節設計上形成了某種定式:一心救人卻屢遭挫折的男女主角;深陷牢獄政治犯;大團圓式的正義勝利與自由謳歌;盡管思維有些程式化,但也是這種題材的精髓所在,貝多芬的《菲岱里奧》自然也不例外。
美國音樂學家雷伊·M·朗耶爾曾在其發表于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文章中提到:“從之后150年的優勢地位來看,拯救歌劇可以被看作僅有一個作品--《菲岱里奧》--得以幸存的歌劇死水。”由此可見,《菲岱里奧》是整體評價不高的拯救歌劇少有為后人所認可的作品,這不僅得益于被貝多芬的音樂功底,更有深刻的思想底蘊作為支撐。然而,拯救題材為其不僅帶來了成功,也往往成為被批判的劍鋒所指。因為在許多學者的眼中,“拯救歌劇”僅為一時應景之需且很快便被歷史洪流摧垮的“歷史棄兒”,《菲岱里奧》的偉大源自于貝多芬,而局限性則歸因于題材。對此,筆者以為有待商榷。《菲岱里奧》展現了一種非現實性且不應提倡,這類弊端也并非拯救歌劇所固有的一種理想化寓意。
“理想”(ideal)本身是一個雙性單詞,有褒義的完美和貶義的不切實際之意,所以,過頭的理想便是空想,是保羅·亨利·朗口中的矯揉造作的“浪漫主義”,《菲岱里奧》依筆者來看,既完美又過于理想化,整部作品所散發出的“宿命論”主旨,是整部歌劇局限性的“癥結”所在。
首先,過于直白的邪不勝正的“宿命論”。對于這部歌劇情節的印象,某些人也許為萊奧諾拉光輝、勇敢的女性形象所折服,也許會動容于弗洛雷斯坦的不公正待遇,又或許被獄守羅可最后時刻迸發的正義之心所感化;但這些無疑都是屬于正面人物的凱歌。有正就有惡,推動戲劇情節發展的核心動力是矛盾。
皮扎羅是劇中最核心的反面人物,這類人物往往在劇中前半部分應當具有壓倒性的權勢和威懾感,是摧垮一切正義的惡勢力的代名詞。但令人唏噓的是,這個惡棍卻沒有獲得他理所應當的地位。極度的惡從出場開始似乎就是個“弱勢群體”,除了他那一段低沉的詠嘆調訴說自己暗地里的種種罪行外,其他所有的情節安排似乎都是作者為避免極端的“惡”變得無比強大而設置的枷鎖,例如他要殺死弗洛雷斯坦卻不自己動手,身為監獄中的最高領導卻要買通自己的獄卒;又或者在行經敗露在審判前要做最后一搏時,從手中掏出的是刀,而萊奧諾拉卻掏出了槍;此外,最令人不解的是,大臣的視察消息,在整部作品中起到的雙面作用。從皮扎羅第一次聽到消息開始,他開始對弗洛雷斯坦動了殺心,之后愈發迫切,索人性命的欲望在之后成為了劇情的主要推動力。正義與邪惡爭分奪秒對于生命的角逐成為了主旋律,皮扎羅要趕在大臣來臨前殺死弗洛雷斯坦以免惡行敗露,而萊奧諾拉為了拯救丈夫,則加緊了對獄卒羅可的說服。由此可見,這個消息對于正邪兩方來說都是懸在其頭上的“達摩克里斯懸劍”,哪一方先落下,就會遭受命運的審判。而這樣一種外力限制,對哪一方更為有利,筆者以為顯然是后者。如此就好比為一部電影提前寫好結局一樣,從它出現的那一秒開始,已經為惡人選擇好了歸宿,而且還給出了時間。如此設置,導致了惡勢力過于孱弱,以至于正邪交鋒的緊張感在劇中體現不足,直到尾聲大合唱前,皮扎羅與萊奧諾拉夫婦在地牢中的當面對質,才稍有流露。《菲岱里奧》的劇本的實際情節與看似驚心動魄的拯救主題是十分不符的。
其次,上帝的給予大于個人的努力。對于這部作品,我們肯定這部歌劇塑造的女性英雄形象是如此傳神,萊奧諾拉可以說是那個時代最為成功女性角色都不為過。但我們也必須要承認,當自由即將一錘定音的時刻,主角們的命運卻被作者自然而然的交于了超自然力量。這股力量正如最后一幕大團圓中大臣的歌詞一樣:“上帝賜予了他真正的公義(Gerecht ,o Gott ,istdeinGericht)”。對此筆者不禁要反問,這來之不易的自由,功勞究竟當歸何人?是仁慈上帝的恩典,還是以女性英雄所代指的源于人類自身對自由、民族的那股熱切渴望。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尤其是當聯想起法國偉大的革命者丹東的遭遇時,更令人心頭為之一顫。偉大的革命家被自己組建的法庭送上斷頭臺,那時那地上帝并未展現恩澤,英雄也沒有獲救,悲劇只在英雄面對昔日好友羅伯斯庇爾那一聲義正言辭:“下一個就是你”后劃上了句號,這是何等的凄涼啊!
就這一現象,國內學者也曾做出過解釋,上海師范大學魏巍曾在其碩士論文《探究拯救歌劇〈菲岱里奧〉》指出;“貝多芬要反對的是中擁有權力的小專制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國王貴族階層,反之他將拯救的希望寄托在后者身上,給予他們開明正直的身份…但終歸,成功的拯救是自上而下的,正因為此打破專制的精神內涵被模糊削弱了。”對此,筆者表示贊同,但深覺更應站在高于階級性的層面,進一步窺探其中奧妙。根據康德的自由觀念,假如一個行動是自由的,必然遵循“在發生的時刻,該行動及其對立面都必須為主體掌控。”也就是說,如其所言,歌劇中每一位角色的命運都掌握于自身,他們有著多樣的選擇。但是,這畢竟是一部戲劇,源于人類意識領域,而非自然自在物。在有劇本的情況下,給予角色“選擇”便成為了作品中啟蒙精神的體現,這理應更多隱含于劇情設置。而在上文對該劇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劇中人物大多別無選擇。惡人,從頭至尾都如同一個被急于送上斷頭臺的死刑犯。過分要求在既定規律下,結局的一致性,追求說理性,而忽視了劇情中矛盾的塑造。這難道不是浸染了與啟蒙精神相背離的宗教“宿命論”的后果嗎?
當然,當我們試圖理解一段歷史,考究一部作品時,我們需要的不僅是當代的表象,更要立足歷史意識。無疑,《菲岱里奧》所傳達的思想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意義是巨大的,雖然單憑我們今日眼光來看,片面性是存在的,但不能全盤否定。達爾豪斯曾在《音樂史學原理》針對“雙語理論”中提到:“確實有可能在避免自相矛盾的前提下,讓歷史知識服務于審美體驗,或者以同樣的方式,將審美經驗作為歷史探索的出發點。”所以,一部作品思想上的歷史局限性,并非有礙于對其的審美評價。況且以歷史價值視之,這部作品某些直截了當的詮釋方式,更適應于當時的政治環境以及群眾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