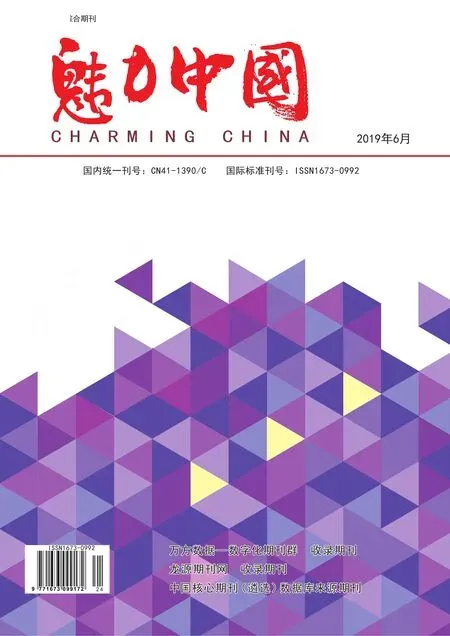精準扶貧視角下多元協同治理困境研究
劉亞平
(中共重慶市榮昌區委黨校,重慶 榮昌 402460)
一、精準扶貧中多元治理存在的問題
(一)多元協調困境
多方力量都參與到精準脫貧中,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強大的幫扶力量,但是各方幫扶資源對幫扶對象實施中,卻存在著多元協調困境。
1.扶貧力量沒形成合力。貧困群眾的扶貧力量是九龍治水,有負責產業扶貧的,有負責科技扶貧的。各個單位下派幫扶人員前,并未進行協調和溝通。實際幫扶過程中,也缺少一個有力的組織把各方幫扶力量統籌起來共同發力。就出現了今天科技特派員下村進行家畜家禽飼養技術的傳授,明天區縣的工作人員下村為貧困群眾講授經濟作物的種植技術,或者送食用油、大米等物質幫扶,這種幫扶的組織性不高,反而讓貧困群眾認為扶貧人員是走形式、走過場的,幫扶效果不高。
2.扶貧精力能否持續問題。現在鄉村空心化程度的加深,精英群體逐漸離開鄉村來到城市生活,導致村兩委班子普遍存在干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眼界不高,但是面對艱巨的貧困治理任務,村組干部出現了精神懈怠,覺得在任務重、待遇低,工作做不好就通報批評的情況下,產生了心理上的動搖,覺得當干部還如做一個平頭百姓,但絕大部分扶貧政策實施、扶貧項目等需要村兩委去組織落實。這些因素都影響著村干部在精準脫貧中精力能否持續發力,影響著基層在脫貧攻堅中的戰斗力的發揮,村組干部不能發揮領頭雁作用,增加了扶貧治理的阻力。
3.貧困群眾“巨嬰”式貧困。習近平指出,“貧困群眾既是脫貧攻堅的對象,更是脫貧致富的主體”①。貧困群眾是需要幫扶的對象,但是也是能夠持續穩定脫貧的主力軍,他們自己的貧困需要通過自己內在動力的驅使下,逐步在幫扶力量、資源的協助下實現穩定性的脫貧。習近平明確強調,“擺脫貧困首要并不是擺脫物質的貧困,而是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②。但是,在實際精準扶貧中,廣大貧困群眾存在著自我發展動力不足和對實現脫貧的信心不足的問題,沒有意識到脫貧是自己的事情,反而認為脫貧是干部、是政府的事情,把自己當做脫貧的看客,“干部埋頭干,群眾圍觀看”的現象仍然存在。產生這樣現象的原因,一是幫扶力量的幫扶意識存在偏差。在幫扶開始階段,幫扶力量沒有意識到脫貧中誰才是真正的主體,對自己角色不能由管理向治理轉變,扮演著大掌柜、大家長的角色,僅僅認為從物質上幫扶、走走形式就能完成任務,造成了單向的輸出式的幫扶,讓貧困群眾對幫扶干部產生了依賴性;二是一些貧困戶確實存在“等、靠、要“”思想,即便有勞動能力,好吃懶做,掙一個花倆,脫貧志氣不振。甚至有隱瞞財富、刻意塑造貧窮的傾向,見到扶貧干部就哭訴自己窮、多病又沒錢,把貧窮作為一種得到物質支持的籌碼,造成了一種越幫越窮的窘境。
(二)幫扶能力不足困境
精準扶貧中,鄧有才提出,精準脫貧要立足于治理,借力于治理,以治理為基礎推動和實施。治理為精準脫貧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臺,為精準脫貧提供了制度規范③。多方面的制度保障確保了精準扶貧的資源得以合理的利用,但是基于多方力量各自的優勢領域不同,制度功能未能充分加以運用。比如制度使用方面,國家、各級地方政府對精準扶貧做了大量的制度頂層設計,這些制度涉及教育、醫療、民政、產業等各個方面,涉及面廣又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在缺乏專業指導情況下,參與幫扶人員、被幫扶對象都難以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把握這些制度,部分貧困治理主體感到無從下手。
(三)扶貧幫扶效果困境
1.幫扶滿意度和幫扶成效不相當。對扶貧工作成效的民意調查中,貧困群眾對幫扶的滿意度較低,與幫扶實際效果不相符。幫扶滿意度作為被幫扶對象對幫扶對象的工作的一種主觀評價,貧困群眾基于怕脫貧的心理,希望幫扶對象繼續給予各種資源優勢,于是產生了“用腳投票”心理,即使幫扶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貧困群眾依然能說出不滿意的地方。群眾對幫扶成效不滿意的話,多是從幫扶領導干部的角度進行懲處,沒有實際可以約束貧困群眾的機制,讓貧困群眾如實的表明幫扶的滿意程度。
2.當前脫貧和穩定脫貧的矛盾。目前,較多已經脫貧的貧困群眾,政策性脫貧的指數很高,存在著政策性幫扶一旦撤出,就會再次返貧的困境。一方面是,部分地區干部為了完成脫貧任務,在幫扶中仍存在敷衍了事現象,沒有針對貧困戶的實際情況精準幫扶,多是采用政策兜底的方式,提高貧困群眾的年均收入,貧困群眾的年均收入達到脫貧指標時就宣布脫貧。這種脫貧是位于臨界點的短期脫貧,脫貧不具備穩定性,這種輸血式的幫扶方式,容易導致貧困戶的福利依賴或政策依賴,客觀上影響了貧困戶脫貧內發動力的生成。另一方面,幫扶干部對精準扶貧的方法不多,沒有發揮主觀能動性,讓不同原因致貧的貧困群眾找到脫貧的路子,除了依靠政策性的扶貧,在就業幫扶、產業幫扶、金融扶持、集體經濟上脫貧力量薄弱。盡管有的幫扶對象也有走出去的思路,但在扶貧經驗借鑒上多是照搬照抄,沒有靈活的與當地情況相結合,短暫的增收后陷入持續增收困境。
二、精準扶貧中多元協同治理的出路
(一)轉變貧困治理理念
1.營造良好的鄉村文化氛圍。為了有效化解精準扶貧實施過程中貧困群體、臨界貧困群體等產生的新的社會矛盾,在貧困村開展“矛盾調解”活動,組織群眾工作相關人員聯合各幫扶力量,深入貧困群眾召開大會,現場解答群眾疑問,調解群眾之間的矛盾,引導群眾樹立感恩、包容、互助的精神,摒棄自私自利的狹隘觀念,塑造積極向上的良好風氣。
2.塑造共建共享的理念。在貧困治理活動中,不僅涉及到貧困戶,也關系到非貧困戶的利益。精準到戶的幫扶措施中,通過以工代賑、勞務補助、公益勞動等激勵機制,充分調動貧困戶自身的積極性、主動性,引導貧困戶在政策支持下自己動手、主動參與④;對于非貧困戶的參與激勵,主要通過共同利益、長遠利益、整體利益加以誘導。在精準幫扶貧困戶的過程中,同步謀劃全體村民的致富事業,致富在僅僅局限于貧困戶,謀劃的是今后的公共建設、產業發展,關乎每個村民的利益。
(二)提升外部幫扶能力
1.基層黨建促扶貧。給錢給物不如建個好支部。多元化的治理結構中基層黨組織是最核心的部分,加強基層組織建設,選好領頭雁、配好配強班子成員,深入實施黨建扶貧,廣泛開展城鄉黨組織結對共建活動,通過共建提升基層黨組織建設水平,并為扶貧治理帶去新資源,貢獻新能量。
2.用法治規矩扶貧。基層貧困治理也需要建立相應的制度,以規范貧困治理主體的行為。需要由包辦管理向法治治理轉變,建立制度化的村規民約、民主治理、信息公開等制度化,約束扶貧治理的隨意性。
(三)增強貧困主體脫貧的獨立性
“扶貧必扶智,治貧先治愚。貧窮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頭腦空空,怕的是知識匱乏、精神委頓。脫貧致富不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腦袋”⑤。提高貧困戶的自我發展能力,是解決貧困問題的核心所在。首先要精神脫貧,在思想上讓貧困戶擺脫等靠要的思想,樹立能夠堅決脫貧的意識,在幫扶資源的幫扶下,通過技能培訓等具備能夠脫貧的能力,并將這種能力在實踐中轉化為家庭經濟收入,這樣才能實現穩定脫貧和致富。其次實踐上來講,加大教育扶貧,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建設農民培訓中心,著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為新型農業、養殖業等方面的技能能手進行評選和給予獎勵,擴大自我脫貧的宣傳,激發貧困群眾的技能學習熱情。最后,幫扶外部資源上來講,各幫扶單位要對有勞動能力能就業脫貧的貧困群眾,推薦就業崗位,鼓勵有能力的貧困戶統籌使用產業發展資金和扶貧小額貸款,實現自身技能能夠與產業發展的無縫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