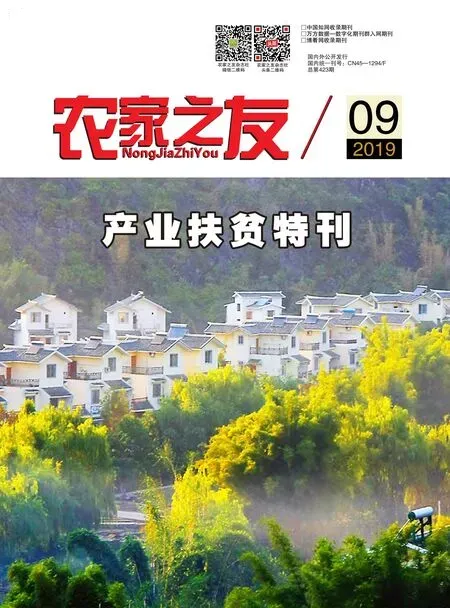興安:“廣西吐魯番”的新三樣
本刊記者 劉光琳 通訊員 劉玉蘭 陳雙艷 黃薇
在歷史上,興安是響當當的名字,因為靈渠,也因為湘江戰役。
在地理上,興安是叫得上號的地方,因為貓兒山,也因為它是兩條中國著名河流——漓江和湘江發的源地。
因地處“湘桂走廊”要沖,交通便捷,區位優勢明顯,農業資源豐富,是廣西農業大縣。有桂北糧倉、銀杏之鄉之稱。在發展扶貧產業過各中,因地制宜,發展高山特色蔬菜種植、養殖、風電旅游開發等特色產業,譜寫出一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振興的現代“田園牧歌”。
菜:扶貧辣椒“漫山紅”
興安縣高尚鎮有一個叫“鳳凰”的村委。一說起它,很多人總是聯想起“閉塞落后”,因為該村離鎮上較遠,出入需要翻山越嶺,是一個比較偏遠的山村,且貧困人口相對集中,全村601戶農戶,貧困戶建檔立卡132戶;這里的自然條件比較惡劣,下雨天容易形成山洪,連續晴天又容易形成旱災。
正所謂越原始越生態,鳳凰村的平均海拔600多米,晝夜溫差較大,植被茂盛,氧氣充足,土質水質好。這里種出的蔬菜富含微量元素硒,品質佳,口感好,是高端蔬菜的理想種植基地。但是進村道路極為陡峭,交通不便,這里的農副產品很難走出大山。2016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實現了村屯道路硬化,完成了進村道路“最后一公里”建設。

辣椒產業已成為鳳凰村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一大支柱產業。
沿著彎曲的山路,翻過幾座山,就到了鳳凰村,在村委我們見到了駐村第一書記李凝。李凝是農學專業畢業并且在農業系統工作多年。李凝駐村鳳凰村后,通過實地考察和市場調研,認為發展種植辣椒、日本甜柿、紫玉山藥、甜玉米等特色產業比較適合當地發展。
大北村是鳳凰村委的一個自然村,村子在群山環繞中。全村400來人,有15戶貧困戶。當地的沙土比較適宜辣椒的種植,高海拔種出的辣椒果實好,亮度高。且辣椒管護成本低,收獲期長,2月下種,5月就能收獲,收獲期一直持續到11月。鳳凰村采取“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戶+貧困戶”的模式發展種植辣椒,同時針對合作社在外銷平臺上的短板與局限,鳳凰村委決定引進專做辣椒生意的桂林程千眾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恰好該公司負責人秦福順就是興安本地人,在外做了20多年辣椒生意,他積累了豐富的人脈和資源。僅鮮椒專賣店就有10多個,分布在長沙、廣州和重慶等地,365天每天都要保證有充足的鮮椒供應。

“訂單農業”讓社員不再發愁,有利于辣椒品質的提升。

2018年9月,有著種出高質量辣椒的理想和帶動鄉親致富的信念秦福順回到家鄉,12月和村合作社達成簽約意向,投資100多萬元用于當地辣椒的種植。秦福順在大北村承包了近200畝山地種植辣椒,考慮到鳳凰村比較窮,秦福順主動墊資200多萬元解決當地農民前期的投資問題。在他的指導下,全村近60戶村民種植辣椒750畝,其中,貧困戶有20多戶。200畝的辣椒管護需要人手,貧困戶成為公司優先考慮的對象,在公司30多個長期負責管護的人中,貧困群眾占了一大半。
村支書梁定富把全家的地都種上了辣椒。望著地里綠油油的辣椒,他說,以前種玉米或花生,每年每畝收入最多1000多元,現在種了辣椒,單是合同的保底價每畝至少可以達到5000元。
目前,鳳凰村共種植辣椒630畝,有中椒6號、長辣7號和紅霸米椒三個品種。公司為合作社提供種子、農藥、化肥、技術等,為社員設定最低保護價1.2元/斤,今年的行情比較好,保護價也根據市場相應提高,達到每斤1.8-2.4元。“我們的辣椒不愁銷,單紅霸米椒一個品種,每天都可以賣60萬斤,供不應求。”秦福順說。
一畝地辣椒產量7000-8000斤,每斤按1.8元計算,一畝地最少能有1.2萬元的收入,扣除4000元左右的成本,每畝純收入最少有8000元。這種“訂單農業”讓社員不再為銷售發愁,從而能夠更專注于辣椒的種植,有利于辣椒的品質的提升,產量的保障。
進入八月以來,辣椒銷售進入旺季,每天從鳳凰村采摘外運銷售到全國各地的辣椒達15萬公斤,預計今年全村辣椒產值近1000萬元。這些辣椒從田間地頭采摘完畢立即通過物流直供超市、飯店,遠銷長沙、重慶、昆明、貴州、杭州等地。
公司還聘請合作社成員對收購的辣椒進行分揀、裝箱,每天工作8個小時,包接送,包三餐,工資日結,每天90元。“我幫老板打工,每個月有2500元工資,自己還種了2畝辣椒,老板提供前期的種子和化肥農藥錢,還幫銷售,今年有望脫貧。”貧困戶唐德生一邊將辣椒打包裝車一邊高興地說。像唐德生一樣在公司務工的貧困戶還有30多個。
在車旁與村民們一起忙著辣椒卸載、挑選、分裝貧困戶蔣德宏就也是其中一個,今年開春以來一直在該公司務工,從事整地、育種、植株、抹芽、打藥等工作,每月工資收入兩千元。此外,蔣德宏自己也種植了一畝辣椒,預計年收入達7000元。眼看今年年收入將近2萬元,蔣德宏喜不自勝。貧困戶胡玉良從去年開始種植了近3畝辣椒,大大增加了他的收入,并在年底實現了脫貧。得益于政策上的優惠和技術上的指導,今年的辣椒已經賣出1萬多元。
72歲的蔣周玉之前也零散種植辣椒,自己挑到市場上賣,每斤只能賣到五六毛。如今,在合作社和公司的幫助指導下,他一個人就種植了5畝辣椒。“自己種辣椒沒有規劃,還經常賣不出去,現在是只要認真種,根本不愁賣。”
如今,辣椒產業已成為了當地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一大支柱產業,種植辣椒帶動20戶貧困戶走上脫貧致富路。
“明年我打算在高尚鳳凰、靈龍兩個村擴種3000畝,要種就要達到‘漫山紅’。”望著豐收的辣椒,秦福順自信滿滿。
“統一供種、統一種植、統一供肥、統一收購”,合作社和企業的攜手,不僅使辣椒種植實現了集約化、專業化、規模化、標準化,而且讓當地村民真正實現增收,幫助貧困戶真脫貧、不返貧、能致富。
菇:“菇爺”撬動一鎮
離開了鳳凰村,縣產業扶貧辦的小陳說帶我們去興安湘漓鎮拜訪一位“菇爺”,“姑爺?”見我們疑惑的表情,小黃笑了,對,“菇爺”,專門研究種蘑菇16年的“菇爺”,哦,原來是此“菇爺”非彼“姑爺”。
從興安縣城驅車3公里,就到了湘漓菇緣家庭農場,農場地理位置優越,位于湘漓鎮至界首鎮的二級公路旁。
時至七八月,天氣炎熱,走進其中一個大棚,棚內潮濕溫熱,一個個菌苞一層層整齊地擺放著,一簇簇秀珍菇沖破薄膜冒了出來,長勢喜人。只見七八個工人正在清理菌棒上的菌渣,這個大棚剛采摘完一批秀珍菇,這位“菇爺”正忙著打電話,聯系發貨廣東。

何振明規模化種植,為當地產業扶貧和食用菌產業發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今年43歲的“菇爺”,名叫何振明。言辭不多的他,一說起種菇,便侃侃而談。從他的介紹得知:菇緣家庭農場成立于2018年,農場的前身是2011年成立的振明食用菌種植基地,但是種蘑菇的歷史還要追溯到2003年。
2003年以前何振明,還是一名大城市的農民工。因為家境貧寒,初中一畢業去到廣東,做起了建筑工,一做就是十年。2003年,27歲的他,聽說家里的一位叔叔在家里種植起金針菇,效益不錯,于是,何振明決定辭職,先去到浙江、福建考察學習金針菇種植技術。學成之后,重返家鄉的他,決定趁自己年輕,在自己的家鄉試一試,大不了一切重來。在這樣的決心下,開始了他白手起家的創業之路。
就這樣,何振明先在自家的地上建起了大棚,種植起了金針菇,有了效益后來不斷擴大規模,他又研究起了種植秀珍菇,秀珍菇本是喜寒植物,適合在冬季生長。何振明勇于創新,大膽實踐,通過設施栽培,溫差刺激,進行夏季反季節栽培。通過調控溫度控制產量,運用冷庫機24小時控溫在10℃以內,刺激菇蕾形成。經過反復實驗不斷探索,反季節種植秀珍菇取得了成功。就是這樣,憑著堅定的信念,執著的追求,刻苦的鉆研,何振明在食用菌行業創出了一片天地,成為全縣效益最好的蘑菇種植基地。
2018年要建農場了,因和蘑菇的“緣分”,何振明為他的農場取名“菇緣家庭農場”。
目前基地種植反季節秀珍菇40萬棒,產鮮菇240噸,平均每棒產1.2斤,每棒收購價均價每斤在5.5元左右,最高可達8元。純利潤2.2元左右,產值達240萬元,產品銷往廣東、湖南、廣西等地,供不應求。農場由3年前每年5-60萬元的純收入,增加到每年80~90萬元的純收入。
由于經濟效益好,栽培技術成熟,何振明成為赫赫有名的種菇致富能手,慕名前來參觀學習的越來越多。2017年縣農業局支持30萬獎補資金給何振明,用于規模擴建基地。
何振明介紹說,秀珍菇又叫小平菇,外形悅目,質地鮮嫩,口感好,是一種高蛋白、低脂肪的營養食品,又沒有平菇的腥味,深受消費者青睞,市場需求量大,供不應求。
現在農場種植基地面積達15畝,全部采用標準化種植。目前擁有標準化生產菇房13個,其中工廠化生產菇房5個,機械設備有拌料機1臺,接種箱10個,食用菌生產裝袋機2臺,木料粉碎機1臺,鏟車1臺,滅菌鍋1個,移動制冷機2組、冷庫房機組2座,排風扇60個;16年的努力,農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如今固定資產達400萬元。
何振明的農場長期所需一批管護人員,在眾多求職人員中,他著重偏向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低保戶、殘疾戶招聘,目前現有長期管護人員20人。
正在清理菌渣的54歲的貧困戶楊桂芳告訴記者,她是五里峽庫區移民,愛人身體不好,家有90歲老母,還養著一個64歲無法勞動的殘疾哥哥,兒子還在念技校,女兒剛剛大學畢業。家里僅有幾塊貧瘠的干田,且位于5公里山路之外,一大家子的生活非常艱難,而附近周邊能提供就業的崗位微乎其微,很多男勞力就近找不到工作。
得知貧困戶楊桂芳家庭困難,何振明主動邀請她和另外4位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來到他的農場長期務工,每年為他們增加務工收入一兩萬元。近兩年來,其中3戶貧困戶順利實現脫貧,楊桂芳也將在今年脫貧摘帽。
楊桂芳心懷感激地說道:我們村的年輕人很多都外出打工了,年紀稍微大點的,因為要照顧家里,也不敢外出,再說年級大了,出去也沒人要。我們附近村也幾乎沒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多虧了何老板,我年紀大了,能在大棚里干點雜活,活動活動筋骨,還有錢賺,多虧了何老板,幾年下來一直留著我在他那打工。
在何振明的帶動下,湘漓鎮花橋村、江口貧困村有5戶群眾也發展食用菌規模化種植,規模也都在一二十萬棒左右。同時何振明也先后培養出10余位種菇致富能手,為湘漓鎮產業扶貧和食用菌產業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借“風”發財的源江村
拜訪完了湘漓的“菇爺”,小陳又興致高昂地說帶我們去看看借“風”發財的源江村。借“風”發財?如何借“風”,小黃但笑不語,只說到了源江你就知道了,懷著好奇,我們朝著源江村奔去。轉過一個山口,遠處山頂一架架高大矗立的“風車”撞入眼簾,山腳一幢幢整齊漂亮的樓房,田里一排排綠意盎然的荷包豆,還有山間的樹木、花朵,在藍天白云的襯托下,構成了一幅美麗的畫卷,讓人心曠神怡。
“這里是興安鎮源江村委周家園自然村,你現在看到村子這么漂亮,四年前可不是這樣。”源江村黨支部書記候文介紹說。源江村距離縣城17公里,是一個典型的偏遠山區村,這里四面環山,海拔約600至700米,群眾生產生活條件艱苦,村經濟收入主要來自于農業,糧食主要為水稻、玉米,經濟作物以高山蔬菜、荷包豆為主,是“十三五”自治區級貧困村。
興安地處“湘桂走廊”要沖,風力、光照資源十分豐富。近年來,憑借國家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機遇,該縣走出一條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新路。目前,興安縣已投資65.3億元在全縣境內安裝了機組340臺,成為華南最大的風電基地。
當我們問起如何借“風”發財時,村支書候文告訴我們,2015年以來,隨著綠色風電項目不斷縱深推進,興安提出“風電產業+蔬果產業+農旅結合”的綠色發展思路,制定“靠山吃山”的發展策略,發展藥材種植、打造高山蔬菜基地等多種途徑不斷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依靠項目的帶動。源江村因地制宜,把高山蔬菜產業作為產業扶貧的支柱產業,通過“合作社+農戶”模式發展高山蔬菜種植產業,帶動源江村7個自然村20戶貧困戶增收致富。
高山蔬菜種植因天氣影響大,見效期長,管護難,貧困戶單獨發展面臨種種不穩定因素。在堅持自愿、有償的前期下,源江村提出“企業+貧困戶”的經營模式,引導和鼓勵貧困用戶積極參與,通過貧困戶提供土地,公司提供菜秧以及管理技術,貧困戶出工出力管護,公司最后回收統一銷售,高品質的甜心菜、芥藍、迷你小冬瓜、荷蘭豆、香菜、西蘭花、荷包豆等有機蔬菜售賣到桂林市區及廣東、港、澳等地,最大的避免了農戶的損失,使利益最大化。農民除了收取地租,還可以幫公司種菜掙工錢,一年下來,每畝地的收入有三四千元。通過與公司合作發展高山蔬菜產業為貧困戶脫貧找到了一條新途徑。同時成立了周家園種養合作社,主要以荷包豆種植為主,將產出資金作為貧困戶入股的股金,已帶動源江村12戶貧困戶40人種植,每戶貧困戶年收入增收2500元。2016年,源江村順利脫貧摘帽。楊超良一家曾經是源江村的貧困戶。他身有殘疾,家中勞力缺乏。在扶貧攻堅過程中,源江村根據他家的實際情況,積極引導楊超良家種了兩畝地荷包豆。在楊超良的荷包豆地里,正在澆水的楊超良告訴記者,目前,源江村的荷包豆種植已成規模,在豆子成熟的季節都會有客商到村里面收購。靠著荷包豆產業,楊超良可以通過雙手支撐起整個家庭。

源江村利用豐富的風電資源,打造高山蔬菜基地等多種途徑壯大村集體經濟。

高山蔬菜產業為貧困戶脫貧找到一條致富新途徑。

2017年,興安以周家園自然村新村建設為試點,通過村容村貌整頓,宅基地復墾等方法整合200畝閑置土地,以“定單農業”模式,引領群眾發展獼猴桃、百香果、羅漢果及高山疏菜為主的旅游觀光型農業產業,每年為村集體增收3萬余元,帶動種植農戶每戶增收1.2萬元,2017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2000多元。
2018年,源江村利用風電項目重點區域的優勢,爭取20萬元財政資金入股風電企業,每年可分紅2萬元,全村村級集體經濟收入達到了9萬余元,人均年純收入達15890元,65名貧困人口通過參與開辦農家樂、種植生態蔬菜及水果、發展鄉村旅游等方式實現脫貧致富,源江周家園村被評為自治區四星級鄉村旅游示范區。
源江村雖然地處偏僻,但環境資源得天獨厚,10萬畝華南最大的風電基地、摩天嶺大峽谷、冰川瀑布都在其內。美麗的風光吸引了大量周邊市縣的游客,區內外游客也慕名而來,游客最多時旅游大巴車達十余輛,徒步、騎行的驢友更是應接不暇。
為增強發展后勁,該縣還以源江“風車文化節”、高山蔬果種植和高山雪景為“賣點”,打造“醉美天上源江·風車之歌飛揚”旅游品牌,吸引大量游客來觀光旅游。
“以前我們村是遠近聞名的貧困村,自從風電產業落戶后,2016年底,我們摘掉了窮帽,成為新農村小康示范村,現在村民搞起農家樂和民宿,日子越過越有奔頭。”村支書侯文高興地說。
目前,源江村經過“風電觀光+農旅結合”的發展模式提升和打造旅游區建設,已建成縣級農業核心示范區高山蔬菜基地400多畝,投入20萬元新建蔬菜棚10個近20000平方米,計劃今年年底建成1千畝的高山綠色蔬菜市級農業核心示范區,逐步實現工業、農業、旅游業深度融合的產業發展模式。今年上半年,到源江旅游的人數已達2萬余人 ,由旅游帶動起來的農家樂4家,旅游創收近60萬元,實現了從貧困村到新型旅游地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