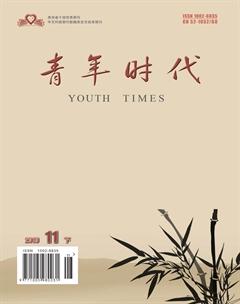從幕后到臺前
徐媛媛
摘 要:傳統(tǒng)藝術觀中藝術媒材與藝術品的從屬關系使得人們很少關注媒介物性在意義表達方面的重要作用。隨著裝置成為現代藝術中最受青睞的表達方式之一,藝術媒材逐漸由幕后走向臺前,媒材的物性成為構成藝術品表意系統(tǒng)的重要有機元素。在這一過程中,藝術媒材通過不透明化、意義獨立化等過程,消解了傳統(tǒng)藝術作品對媒介物性的克服,完成了對藝術品的“反叛”,從而在某種意義上成就了藝術品的本質特性。
關鍵詞:藝術媒材;藝術品;物性;反叛
藝術媒材是與一件藝術品的呈現最直接相關的因素,它是心靈與表現的橋梁,也是藝術品觀念的最直接載體。無可否認,任何一件藝術品都必須以物性的方式存在,僅僅停留在腦海中的靈感與構思只是藝術創(chuàng)作開始的第一步。
在觀賞一件藝術品的過程中,人們最先接觸到的就是構成藝術品的媒材,最容易忽略的也是藝術媒材。然而正如海德格爾所強調的:“極為自愿的審美體驗也不能克服藝術品的這種物的特性。建筑品中有石質的東西,木刻中有木質的東西,繪畫中有色彩,語言作品中有言說,音樂作品有聲響。藝術品中,物的因素如此牢固地現身,使我們不得不反過來說,建筑藝術存在于石頭中,木刻存在于木頭中,繪畫存在于色彩中,語言作品存在于音響中。”[1]可見,藝術媒材賦予藝術品的物質性與藝術本身密不可分。同時在藝術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中也都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對于藝術家來說,它是自我表達得以實現的客觀前提;對于藝術品來說,它是使其成為獨立審美對象的依托;對于欣賞者來說,它是藝術品可感性的重要特征。當人們將目光集中于媒介物性之上后,就可以勾勒出一個關于藝術媒材與藝術品關系的發(fā)展史。回顧這段發(fā)展史有助于明晰媒介物性的自由與彰顯并不意味著藝術性的消弭,反而有助于藝術品打開去往純粹觀念表達的大門。
一、作品對媒介物性的克服階段
古希臘諸多理論家都將藝術的本質歸為對自然的模仿。柏拉圖的“三張床”理論認為藝術是理念的“影子的影子”。亞里士多德繼承了模仿說理論認為:“史詩和悲劇詩,喜劇和酒神頌,以及大部分雙管蕭樂和豎琴樂——這一切實際上是模仿,只是有三點差別,即模仿所用的媒材不同,所取的對象不同,所采取的方式不同。”[2]雖然亞里士多德從更現實的角度出發(fā),認為現實世界不是對于理念的模仿,而是真實的存在,但兩者都沒有離開模仿是為藝術的本質這一觀念。
從西方藝術誕生之始,模仿說一直占據主導地位長達二千余年。在這樣的藝術本質觀的指導之下,對于藝術作品最核心的要求就是逼真,越趨向于真實的藝術作品就越是上乘之作。達·芬奇致力于研究人體結構與解剖學,目的是更真實地反映人體;他同樣精通數學和算數,為的是更準確地表達真實的比例關系。直至巴洛克時代之前西方藝術都是基于對真實的再現。這樣的藝術觀使得藝術媒材的重要作用完全被忽視了。或者說,創(chuàng)作者和評論者還沒有意識到應該將藝術媒材納入到衡量藝術品的范疇之內。雖然亞里士多德認為藝門類的差異表現在模仿所用媒材的差異,但是這里的藝術媒材僅是一種純粹物質載體性的存在。它沒有真正參與到創(chuàng)作過程當中,只是被動地被創(chuàng)作者挑選以完成物質承載的任務。
二、作品與媒介物性的融合階段
隨著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對人的主體性的贊揚,“模仿現實是藝術的本質”這樣的觀點受到了表現論質疑與抨擊。隨之出現的流派開始注重在藝術作品中表達觀念、個性與情感。表現論的產生有著特定的社會歷史原因和哲學背景,但是它取代了模仿說成為統(tǒng)治20世紀之前西方文藝領域的藝術本質觀,于是對藝術作品的核心要求由逼真轉向了共鳴。正如托爾斯泰所概括的:“在自己的心里喚起曾經一度體驗過的感情,在喚起這種感情之后,用動作、線條、色彩、身體以及言辭所表達的形象來傳達出這種感情,使別的人也能體驗到這同樣的感情——這就是藝術活動。藝術是這樣的一項人類活動:一個人用某種外在的標志有意識地把自己體驗過的感情傳達給別人,而別人為這些感情所感染,也體驗到這些感情。”[3]這強調了兩點,一是藝術是通過可見的藝術媒材將自我的內心情感外化的過程;二是外化過程的目的是使得其他人能夠感同身受,也就是引發(fā)觀賞者的共鳴。
這時藝術媒材與藝術品之間的關系發(fā)生了細微的變化。鮑桑葵將藝術媒材視為討論藝術問題的一條重要線索,說明了藝術媒材是如何在藝術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發(fā)揮作用:“我們剛才看到,任何藝人都對自己的媒材感到特殊的愉快,而且賞識自己媒材的特殊能力。這種愉快和能力感當然并不僅僅在他實際進行操作時才有。他受魅惑的想象就生活在他的媒材的能力里;它靠媒材來思索,來感受;媒材時它的審美想象的特殊身體,而他的審美想象則是媒材的唯一特殊靈魂。”[4]此時藝術媒材已經不再是被忽視的外在物質載體,而是在內在構思時就開始參與到藝術過程當中。也就是說,藝術家要通過藝術媒材來思考,而藝術媒材通過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來獲得藝術價值。
盡管藝術媒材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但它們依舊是一種隱形的、透明的存在。當人們遇到羅丹那個穿著睡袍、面目滄桑深沉的“巴爾扎克”時,似乎感受到了這位文學巨匠深沉與炙熱的創(chuàng)作精神以及他所展現的時代氣質。但人們還是無法聚睛于它的藝術媒材——青銅本身。或許作為藝術媒材它很好地展現了巴爾扎克的個人氣質和時代特征,然而青銅本身并不象征著什么,它依舊是為巴爾扎克而服務的。作為符號象征系統(tǒng)的藝術品以一個整體的形式向人們傳遞觀念與情感。然而組成這一系統(tǒng)的藝術媒材是消極的、被動的。它們隱匿在藝術作品的整個價值系統(tǒng)的背后,沒有單獨的所指,只有在整個系統(tǒng)當中才能獲得屬于自己的價值。
三、媒介物性的反叛階段
回顧歷史可以發(fā)現,長久以來藝術媒材都是一種被動的存在。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開始對傳統(tǒng)藝術觀進行反叛與改寫,隨之出現的達達主義等藝術流派在藝術創(chuàng)作上不斷進行先鋒式探索。在創(chuàng)作形式上就是將生活中的現成品、復制品甚至廢品運用到藝術品當中。1950年,杜尚將簽有自己名字的小便池搬進了藝術展,命名為《泉》。一個生活中的日常品就這樣表現了超出它實用價值的藝術價值。杜尚的做法在當時的藝術界掀起了軒然大波,引發(fā)了關于日常品是否可以走進藝術行列經久不息的爭論,但是這種對藝術觀念的革新使藝術走上了另外一條更廣闊、多元的道路。
在當代,藝術早已不再是高居神壇的圣品,而是越來越走近人們的生活。同時受解構與多元思維的影響,關于藝術本質問題的答案不再單一,藝術的表現手法更加多樣,評判標準也越發(fā)多維。這樣的觀念轉變催生了藝術媒材與藝術品關系的又一次變化,這種轉變在裝置藝術中表現最為突出。
業(yè)界對于裝置藝術的緣起與界定并不十分清晰,國內學者蕭元在《裝置藝術的概念及其呈現方式》中作了較為充分的考證,其將裝置藝術界定為:“裝置藝術(installation)是一種物體并置的藝術,一般由兩件以上拾得物或現成品裝配而成,通常不是用雕塑翻模鑄造的方式進行復制。20世紀60年代的裝置藝術被稱為集合藝術(assemblage),更側重以未經過造型處理的現成品來裝配作品。20世紀70年代在裝置藝術蓬勃發(fā)展后,installation才被借用來指稱大型的、不能被表描述為雕塑的、經常使用各種混合材料的、三維空間的作品。”[5]可見與傳統(tǒng)藝術相較,裝置藝術在物性特征上發(fā)生了較為明顯轉化。在這種藝術形式中,藝術媒材對藝術作品來說已經不單單是承載與外化藝術價值的客觀存在,它們由藝術作品的背后走向臺前,使每一個觀看者都將目光集中在它的身上;它們的不透明化使任何人從任何角度都無法忽視它們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在意義的承載上兩者的從屬關系發(fā)生了改變。可以說從裝置藝術開始,藝術媒材開始脫離藝術品本身的操控,完成了對藝術品的“反叛”。
首先,這種“反叛”表現在多樣性與大眾化上。與傳統(tǒng)藝術中常出現的線條、顏色、音調、大理石等媒材不同的是,裝置藝術的媒材幾乎可以是任何材料。座椅板凳、鋼筋水泥這些非傳統(tǒng)式的媒材消弭了傳統(tǒng)藝術由于工藝的復雜或者獨一無二性所獲得的神圣感。這些在每個人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品在充當藝術媒材的過程中使藝術走向了平民化。這意味著藝術獲取了更多的可能性。
其次,這種“反叛”還表現在意義系統(tǒng)構成的變化上。裝置藝術除了整個作品所表達的一整套意義價值外,其藝術媒材也攜帶自身所固有的價值意義。雖然這種價值意義通常都是其作為生活品或現成品所獲得的實用價值,但是這種價值通常都會積極參與到整個藝術品價值系統(tǒng)的建構過程中。例如,徐冰創(chuàng)作的《何處惹塵埃》使用了在9·11事件中收集到的灰塵在地板上書寫了:“As there is nothing from the first,where does the dust itself collect?”(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在這件作品中徐冰想表現人類意志同自然關系的問題,他說:“為什么世貿大廈一旦失衡,頃刻化為平地,回到物質的原始形態(tài)?因為在它之上聚集了太多本不應該的人為意志。這類事件的起因往往是由于政治關系的失衡,但本源卻是對自然形態(tài)的違背。所以說9·11是對人類本質性的警示。”[6]可見,作為藝術媒材的塵埃,由于來自于9·11事件,本身就具有自己的意義價值,它既代表著自然界中最原始的物質形態(tài),也承載了整個9·11事件的整個過程。這兩重含義就使得整個藝術品的價值系統(tǒng)豐滿起來。
除此之外,最為重要的“反叛”是藝術媒材的獨立性使得藝術品所表現的觀念成為了一種變化中的未知。不論位于臺前還是幕后,藝術媒材作為藝術品價值觀念載體的物性始終不會消失。也許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對構成某件裝置藝術品的藝術媒材的觀念發(fā)生轉變,由于其獨立性,這種轉變可能會更改整個作品的價值傳達。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操控與預知的。
也許是這些轉變過于巨大并突如其來,在20世紀初有多學者為工業(yè)化、科技化時代的藝術擔憂。他們認為藝術走下神壇會破壞藝術對現實的批判力。哈貝馬斯就認為,任何試圖將藝術與生活、現實與虛構放置于同一層面的作品都是胡鬧的實驗。當藝術也涉及到商品流通,那種神圣性、獨特性與批判性就已經消失殆盡,它放縱人們欲望化的一面,使自己也淪為商品拜物主義的犧牲品。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藝術媒材的日常化消除了一些藝術品由于其物質或工藝的特殊性所帶來的價值,同時也消除了由于獨一無二的不可復制性所具備的此時此刻。這些處于藝術作品價值系統(tǒng)之外的附加意義將隨著藝術媒材對藝術品的“反叛”而消失,剩下的只有純粹觀念上的表現。正如蕭元所強調的:“裝置藝術是廣義的觀念藝術之下的一種藝術形態(tài),觀念是裝置藝術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也是裝置藝術區(qū)別于傳統(tǒng)三維藝術最為重要的標志。”[7]那么是否可以認為,被“反叛”之后的藝術品成為了純粹的觀念之作,這樣的作品也許才更加接近了藝術的本質?同時,雖然藝術的日常化表面上看似降低了進入藝術世界的門檻,但其實當這些日常品進入藝術的瞬間,藝術媒材的身份就使其“陌生化”,它們既表達著作為日常品的意義,又負載著構成藝術品觀念表達一部分的意義。這種身份意義的“陌生化”能夠促使觀看者反觀自身、思考現實,從而在觀念上拉開了作為藝術品本身同日常生活的距離,成就了其作為藝術的本質——表達觀念與引人深思。
參考文獻:
[1][德]海德格爾.藝術作品的本源[M].彭富春,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24.
[2]亞理斯多德.詩學[M].羅念生,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6:3.
[3][俄]列夫·托爾斯泰.藝術論[M].豐陳寶,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47.
[4][英]鮑桑葵.美學三講[M].周煦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31.
[5][7]蕭元.裝置藝術的概念及其呈現方式[J].華南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1(3):126-138.
[6]徐冰回應對《鳳凰》批評:無法脫離“破爛”的本質[EB/OL].(2010-07-15)[2019-10-30].http://art.china.cn/voice/2010-07/15/content_361156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