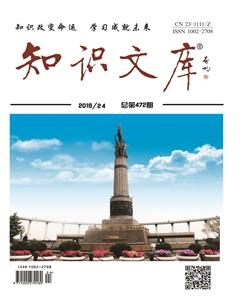“啟蒙辯證法”的現代性價值
崔飛宇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曾說,“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但是,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也就是說,財富的積累會導致無產階級權力的積累,而通過財富,權力的積累,無產階級會越來越認識到他們所受到的壓迫,他們會起身反抗這種制度。在二戰的背景下,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兩人就試圖去理解:為什么當壓迫變得愈加明顯的時候,大眾沒有起來反抗? 換句話說,在了解了法西斯和納粹主義的誘惑后,工人們為什么不去反抗他的資本所有者,不反抗大公司,不反抗他們所供養的政黨?為什么當時的人們要參與到他們自身的控制或壓迫中?為什么他們要給那些使人們變得不那么自由和不那么有能力的人賦予了權力?盡管自由有可能性,但他們仍對統治的持續存在感興趣?
1 追根溯源,回到“啟蒙”
1.1何為“啟蒙”?
“啟蒙的根本目標是要使人們擺脫恐懼,樹立自主”。但是,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難之中。“啟蒙的綱領是要喚醒世界,祛除神話,并用知識替代幻想。”但是,在啟蒙中發生的是,啟蒙為一種新的恐懼創造了條件。
從赫拉克利特到亞里士多德,古典理性主義宣揚通過理性把握人與世界萬物的關系,從而達到對自然的控制與操縱;的確,人們也做到了這一點,印刷術引起了學識的變化;火炮引起了戰爭的變化;指南針引起了金融、商業和航海的變化。這些變化使得原本分散的世界走向聯合,原本獨立的人們開始走向緊密,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以“科技萬能論”為核心的技術理性主義。
1.2“啟蒙”的異化
培根認為,知識中“存留著的”“許多東西”,其本身也僅僅是一種工具:無線電就是一種精致的印刷術,轟炸機是一種更有威力的火炮,遙控系統則是更為可靠的指南針。
的確,科技的潘多拉魔盒,在使得人類社會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的同時,也孕育了深刻的文化危機。科技,既創造了使人類走向美好的物質財富,也使得異化,物化成為統治人的巨大力量。二戰中,“技術惡魔”——原子彈,就是科技的典型示范。“啟蒙”這一美麗的神話,誘惑著我們落入圈套,同時又控制著我們的每一步,削弱著我們的自由。
2 人的“主人精神”
2.1“主人精神”
在19世紀,人們對哲學的解釋和其他模式的定性調查、定性實驗都被稱為知識;但到了20世紀中期,唯一被視為知識的,科學的,是那些可以被量化的知識,最終能統治研究對象的知識。人們的“主人精神”被無限放大,認識——變成了“把握”并“掌控”某種東西;而“知識”——意味著對世界的統治,只是成為了一種統治方式,對知識的其他理解都被推到一邊。
看似具有主動性的人們,實則成為了被動的一方。“知識”作為人們理解的方法,卻赤裸裸的成為了壓迫人們的手段。而在這一過程中,“可計量化”成為了認定知識的唯一框架。
2.2人的“本質力量”
通過“啟蒙”,人成為了上帝的替代品;而在人取代上帝的過程中,人類成了命令的代理人,人擁有了決定將來之事的權利;人也因此成為了主體,事物的認識者,展現自身權利的能力者。那么,人又是如何使用自己的權利呢?不言而喻,在當時的背景下,人是通過知識,運用量化的方法,使得事物發生變化。啟蒙運動曾經向人們承諾出一個不斷進步的文明社會的目標,但是,歷史的發展卻證明,“啟蒙對物的作用正如獨裁者對人的統治。獨裁者只是在操縱人的時候才能了解人,而科學家們只是在制作物的時候才能了解物”。
而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只有無所不知,才不會恐懼;從而人們開始去建立包羅萬象的世界體系,一切都被用來增加操控和統治的權力,所有的知識都被整合到科學和技術模式之中,認識和暴政聯系在了一起。一如今天關于平等的一個觀點,標準化的測試,在追求一視同仁的過程中,消除了個體間的差異,不斷追求平等實際上更多的為強制創造了根據。
3 啟蒙的“自我摧毀”
3.1“啟蒙”成為神話
“啟蒙以消除神話為己任,意欲以知識來代替想象;但是,在現實中,實證化的啟蒙理性卻走向了反面,走向了新的迷信,退化為神話。”
“人通過壓抑他們的內在自然而學會把握外在自然……,曾用犧牲智取神話的自我據再一次被神話命運所征服。”這就形成了啟蒙辯證法的核心命題,“神話已經是啟蒙,啟蒙蛻變為神話”,啟蒙沒有使人進步,樹立自主,卻導致人進入了新的野蠻主義。啟蒙倒退回神話的狀態,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人們給自己披上了理性的外衣,但是內心極度追求物質享受,人類將自己推進了無盡的深淵,與資本主義獨特的生產方式的結合,大眾人群逐漸從理智的“理性追求”轉向狂熱的“工具理性的追求”。
3.2對自然的破壞
啟蒙理性在確定人們在自然面前的無限統治權的同時,并沒有使人真正地成為自然的主人,相反,人對自然的破壞,導致了自然對人們的報復。“在這個擺脫了幻想的世界上,人們喪失了反思能力,再次變成了最聰明的動物……,而是把它看成是對進步的背叛。”由此可以看出,在人取代上帝成為命令的代理人的同時,工業文明正在急速的發展,人們對自然的認識局限于對自然的征服,盲目的認為自然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認為自然會無條件、毫無保留地服從于人類的索取與社會的發展,無法意識到人過分征服自然所帶來的消極后果。
3.3物化加劇
在《進步的代價》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與人類,我們與一般的生物,都像我們與自己的關系樣,經歷過一次手術,便對痛苦麻木不仁……,然而,對自然的永恒統治,各種醫療技術和醫療的技術,都必須在經歷過這種迷惘和遺忘之后,才有可能被創造出來。記憶的喪失正是科學的先驗條件。一切物化過程都是遺忘過程。”在技術的大發展中,人們傾向于用抽象的科學理性去描述現實,傳統的文化信念被打破,曾被“啟蒙”解放了的人類,在高度宣揚主體性的同時,成為了無主體的客體。人們在被動的機械活動中,在逐漸的喪失主體性的同時,創造性也在逐漸的喪失,技術本身成為了扼殺人的自由和個性的力量,而人們也由此被籠罩在完全受啟蒙了的世界所帶來的巨大的不幸之中。
4 “啟蒙”的現代性價值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句話告訴我們,科學技術可以改變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并推動整個社會向前發展,但是事物都具有雙面性,科學技術給人們帶來了益處也給人們帶來了弊端,中華民族要發揮民族特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吸收科學技術對工業文明推進的巨大生產力量,同時注重工具理性帶來的社會問題,務實地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走穩步發展的道路。《啟蒙辯證法》之啟蒙精神啟迪我們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 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啟蒙辯證法》中強調人與自然應當和諧共生,工業技術對大自然無止境地挖掘開采,“自然作為現象與本質、作用與動力的二重性曾經使神話與科學變成了可能,這種二重性正源于人類的恐懼,而恐懼的表達則變成了解釋。”自然曾經作為人生存的載體,現在,人成為自然的一部分,那么破壞自然也就意味著加速了孕育人類生命載體毀滅的進程。人類為了利益無所不用其極,榨取自然的每一分使得自然傷痕累累,生態環境堪憂,人與自然的平衡被人類自己親手打破并且自食惡果。人們要正確認知人與自然的關系,其實,對自然的尊重就是在保護人類自己。
- 正確對待工具理性,揚長避短。科學技術給人們帶來的進步是不容置喙的,我們對科學技術不能全盤否定,要積極地正視它,力圖對其長善救失,發揮科學技術最大作用并避免被控制、奴役。“對工具理性的批判需要某種和解的歷史哲學,需要某種烏托邦的態度......對歷史在場的批判就變成了對歷史存在的批判——對塵世苦海的神學批判的最終形式。”在科學技術的控制之下,人們為追求最大化利益喪失了真正自我以及自由,政府應借助大眾宣傳手段的正面效應,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使人們自由地生產生活,掙脫現實的枷鎖。
- 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相互統一。工具理性帶來的不僅僅是肉眼可見的自然破壞,更重要的是對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了不可泯滅的損傷。因此,應當汲取優秀傳統的人文精神,發揚時代發展的科學精神,二者之間的相互統一能夠抑制科學技術膨脹的后果,要正確分析我國現狀,找到一條適合我國國情,適合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道路,促進個人與社會的共同發展。
5 結語
《啟蒙辯證法》對當時代和后時代的西方哲學家具有長遠的影響,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哲學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長久不衰,真正達到了“啟蒙精神”的作用。《啟蒙辯證法》之“啟蒙精神”對中國道路發展也多有裨益之處,因此,我們要借鑒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科學技術批判的相關理論,聯系我國國情,反思技術理性帶來的問題,尋找適合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