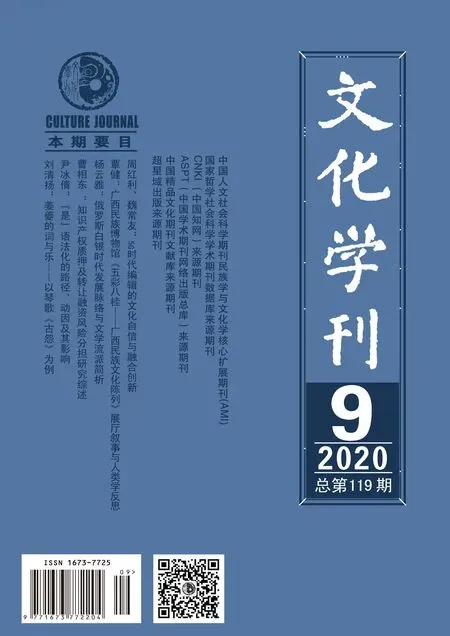帳房寺院在游牧部落的文化功能
——以祁連阿柔大寺為例
多日吉昂毛
寺院在藏文化傳播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媒介作用,是世俗群眾與佛教文化的溝通橋梁,也是代表地區文化特色的博物館。而帳房寺院則是藏區宗教和自然條件、社會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寺院形式,在游牧地區起著重要的文化紐帶作用。
一、帳房與帳房寺院
帳房分為黑色牛毛帳房和白色帆布帳房兩類[1]。在祁連游牧地區多以黑牛毛帳房為家庭主要起居室,以白布帳房為就寢室兼儲物室。牛毛帳房的制作材料以牛毛為主,兩片大帳房布由干片牛毛織物縫制而成,由頂棚、四壁、門、撐桿、橛子多個部分構成,四周用皮繩牽引,固定在橛子上,再用撐桿支撐起來。頂棚設天窗,雨天可覆蓋,晴天可打開。另外,在沒有鐘表的情況下人們通過天窗照進的光線移動來判斷時間。寒冬來臨之際,家庭婦女用牛糞將帳房四周透風部位砌牛糞墻擋風保暖。帳房大小根據財力與家庭成員人數而異。帳房可拆卸,便于搬遷。牛毛保暖、防水、透氣,既適用于高原地區的氣候,又適用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人類文化的產生依賴于自然環境,并遵循自然規律以求發展。帳房寺院以帳房為寺院形式,不同于農區固定的寺院建筑群,帳房寺院可以隨著牧帳圈的移動而遷徙。帳房寺院宗教器物也具有便于搬遷的特征,佛像多以懸掛式唐卡畫像為主,此外據筆者觀察藏傳佛教寺院建筑頂部固有的銅制“雙鹿與法輪”在帳房寺院則用印制在白色帆布上的圖案代替。諸如此類,帳房寺院具有很多自身特色。
二、阿柔帳房寺院概況
阿柔大寺亦即阿柔帳房寺院,又稱“噶丹群培林”,意為“具喜弘法洲”,是阿柔部落所屬的寺院[2]。阿柔部落是作為環海八族之一的土著游牧部落,有著漫長且動蕩的漫長遷徙史,阿柔大寺作為帳房寺院是隨著該部落的遷徙而逐漸發展的。
阿柔帳房寺院發展過程分為多個階段,從初次建寺、初次命名、擴建和獲得法名、幾世達賴的傳經、寺院內部初具規模、至阿柔帳房寺院成為祁連境內最大的格魯派寺院伴隨阿柔部落的整個歷史發展與地域變遷,阿柔帳房寺院的功能與規模也在逐漸變遷。
阿柔部落作為遠離兩大文化圈即漢文化核心地帶中原地區與藏文化發源地帶雅礱地區的游牧部落,在發展過程中保持著完整的部落文化特征,歷史上兩世達賴喇嘛的傳經使得阿柔部落在青海藏區具有一定威望。阿柔大寺隨著部落發展逐漸成為凝聚藏傳佛教文化與阿柔部落民俗文化的主要機構,反映著宗教文化在阿柔部落動蕩的遷徙史中所承擔的文化功能,在多民族文化之林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祁連地區多元文化增添絢麗色彩。
三、文化功能
阿柔部落主體部分遷至祁連地區,從蒙古默勒王手中租牧地而居,休養生息。在遠離阿柔部落文化聚合地區與其他民族共存時期,阿柔部落宗教文化與傳統習俗得以保存與傳承,在多元文化中保持獨具特色的游牧部落文化離不開帳房寺院所發揮的文化功能。
(一)傳承文化習俗功能
帳房寺院如期舉辦的傳統宗教節日是再現的部落文化傳統,節日作為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著一個民族與地區共同的民族記憶與民族文化。祁連地區阿柔大寺有正月法會、藏歷年、娘乃節等為主的幾大節日。
正月法會,自正月十一至正月十五,為祈愿法會,祈禱一年人畜平安,無病無災[3]。節日習俗與其他藏區沒有大的差別。通過這樣的節日,人們可以將對變幻莫測的自然環境與動蕩的遷徙活動的不安寄托于宗教,進行精神層面的自我建設。
娘乃節,又稱四月閉齋節,在四月十五日這一天舉行。信眾集體在寺院周邊搭帳篷留宿閉齋、忌食、忌言一日一夜,行善戒殺一月。閉齋期間念誦瑪尼,轉寺院佛殿。這是一項依靠寺院而舉行的佛事活動,傳承歷史悠久,具有帳房寺院獨有的特色。
藏歷年,是一年一度的節日,接近漢族文化的安多地區受漢文化影響,農歷春節代替藏歷新年,但是節日意義與儀式等同于藏歷新年。節日慶祝和宗教儀式與帳房寺院阿柔大寺密切相關,家中的男性家長承擔期間所有儀式。除夕為“古突節”,與藏歷新年前的“古突節”儀式相一致。除舊大掃除結束后,將垃圾(古突節掃除的垃圾成為“古道”)[4]倒在同年神來臨方向相反的位置,以免沖撞年神。家中男性理年頭,女性編辮子。夜晚準備的晚餐要具備九種食材,一般以粉湯餃子、紅棗等或米飯、紅棗、肉類等食材為主的飯為“古突節”節日盛餐。“這一夜一定要吃飽,半夜閻王會派小鬼來稱斤,越重的人來年越健康。”老一輩的阿柔人的節日習俗,一直沿襲至今。大年三十布置佛龕、燃燈、掛哈達,凌晨在自家房后的煨桑臺煨桑、吹海螺、放鞭炮、磕頭通過一系列儀式來迎接新年的到來。大年初一親戚間互相拜年送去節日祝福,年初二一般不會出門,初三凌晨到寺院祭神,給寺主活佛拜年,男性家長領活佛打卦之后列出家庭誦經單。初三這一天新年未出門串親的婦女、兒童會騎自家的馬在家門外轉幾圈,以祈愿這一年騎馬不出任何意外。宗教儀式是對宗教觀念的具體實踐,阿柔部落群體對傳統習俗及民間儀式的傳承,體現了阿柔帳房寺院作為媒介對藏傳佛教傳統文化習俗的傳承與保護作用,同時祁連地處多民族區域阿柔部落群體在接受他文化影響過程中保持著自己獨有的特色,對自身文化進行重構與解讀,使得祁連地區成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溫床孕育多元的少數民族文化。
(二)民族文化互動功能
阿柔部落作為歷史悠久的游牧土著部落在其動蕩的遷徙歷史中與其他民族產生或多或少的文化互動,帳房寺院承擔著文化傳播與保存的功能。在與祁連地區的其他民族進行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時保持部落文化的特色,阿柔部落初入祁連地區時祁連地區主體民族以蒙古為主,阿柔部落向蒙古默勒王租下牧地,從此在祁連休養生息,阿柔部落與蒙古族日常互動過程中互相影響,藏族接納并借鑒使用了蒙古的部分語言、服飾、習俗等。祁連地區許多地名是蒙語,如祁連俄堡鎮“俄堡”為蒙語,意為“祭神的堆子”,“默勒”意為“江河”[5]。在傳統藏族服飾中也有融入蒙古族服飾元素,如阿柔婦女辮套來自蒙古婦女服飾特點,男士穿的蒙古靴等。此外,阿柔習俗中小孩三歲剃毛頭儀式是蒙藏共有的習俗。而阿柔部落作為外來民族對蒙古族的影響以阿柔大寺為媒介傳播藏傳佛教文化,語言方面祁連地區蒙古族通藏語、蒙古語、青海方言。多數蒙古族沿襲藏族活佛取名的習俗,很多人的名字以具有宗教意味的藏族名字為主,這些是藏族作為后來者對主體民族的影響。
祁連地區的部分漢族也信仰佛教,重大的宗教節日漢族民眾同蒙、20世紀80年代以來阿柔大寺開始定居后其定居建筑風格包含藏式建筑、蒙氏建筑、漢式建筑。其信眾也不局限于藏族群眾,包括漢族、蒙古族。阿柔大寺是傳播佛教文化的場所,是多民族文化互動的媒介,帳房寺院作為主要的宗教場所為阿柔部落適應當地文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祁連地區還有回族以從事半農半牧或商業為生,各民族貿易互動時本著尊重民族習俗文化的同時進行更多的文化互動,為減少與其他民族的溝通障礙與隔閡,祁連地區各民族男女老少皆通青海方言,寺院宗教人士也會強調多民族和諧共存的重要性,促進民族文化多樣性發展。
(三)民眾教育功能
在沒有學校教育的年代,阿柔帳房寺院承擔著教育機構的角色,對寺院僧侶進行宗教文化教育,僧侶大多是來自阿柔部落,帳房寺院活佛與僧人是該部落的宗教文化精英和知識分子,在民眾日常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帳房寺院所培養出來的高僧及佛學精英在整個安多藏區聲名遠播。寺院活佛還擔任部落民眾私人糾紛家庭矛盾調解員、婚喪嫁娶出門遠行卜算者等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角色。
(四)社會控制功能
帳房寺院隨帳圈搬遷,與部落群體同生共存,在這個階段所扮演的角色對整個部落的發展起著關鍵作用。用社會學的觀念來說,社會控制分為硬控制和軟控制兩類,硬控制是強制性、制度性、權威性的規范治理一個群體,軟控制是由習俗、道德倫理等形成規范來控制人的行為。那么,在游牧部落部落制度是硬控制,宗教文化是軟控制,兩種控制互相補充,為游牧部落在遷徙與發展過程中維持著社會秩序,增強族群凝聚力、創造力。
四、結語
帳房寺院在游牧部落的動蕩史中扮演部落文化保存與傳承的功能,是研究阿柔部落文化的關鍵場所,是阿柔部落群體與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動時的紐帶,是邊緣游牧部落與藏文化核心地帶溝通的橋梁,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動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