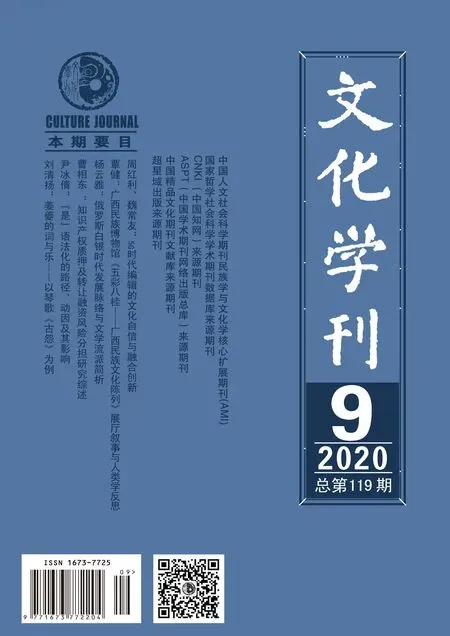雙江南勐河畔瘴氣下的傣族文化適應研究
楊雅雯
一、雙江瘴氣的歷史成因
從病理上來說,瘴氣是由于密閉的地理環境、冷熱溫差較大的氣候特點及當地復雜多樣的生物性等多種因素形成的有毒氣體,易導致諸如瘧疾、痢疾、黃疸等綜合性地方疾病。云南是歷史上有名的瘴區。“云南古蠻瘴之鄉,去中原最遠。”[1]云南瘴區又集中分布在瀾滄江、元江、南盤江等地。雙江位于瀾滄江流域,縣內瀾滄江縱貫于東,小黑江橫亙于南,于東南角交匯而取名,北回歸線橫穿縣內,所以雙江又被稱為太陽轉身的地方。
“縣志記載,民國16年普洱道尹徐為珖,將東面的上改心(忙糯)和西面的四排山加上兩山之間的傣族土司勐勐壩合并設縣,民國18年正式成立雙江縣。”[2]地理環境上,雙江四面高山環繞,西北方四排山突聳,與耿馬傣族佤族自治縣相隔;西南方小黑江奔騰不息,與滄源佤族自治縣相望;東南方以奔騰的瀾滄江與景谷傣族彝族自治縣為界;東北方由高聳的臘東山、打雀山、天生橋山脊為緬寧分界線。大山大河將小小的雙江縣城四面包裹起來,在云貴高原西南邊緣,偏安一隅。縣內整體地勢西北高,東南低。中間縣城壩子由大河灣附近凸起的筆峰山,與西邊的大雪山,東邊的天生橋相連,壩子即分為勐庫壩和勐勐壩。勐庫壩夾在兩個高大的山脈之間,地形像一個鍋底。勐勐壩在四周的山之間,成了一條狹窄的長壩。勐勐壩區內勐勐河由緬寧南美山南部發源,橫穿縣內,又將勐勐壩區一分為二。“氣候類型上,雙江位于北回歸線23°30′上下,日照充足,晝夜溫差較大。受印度洋暖濕氣流和西南季風的影響,干雨季分明。縣內地形復雜,兩壩海拔低,地勢平坦,四周崇山峻嶺,深溝河谷交錯。壩區與四周大山海拔高度相差懸殊,海拔最高為邦馬山之大雪山主峰3 233米,最低為東南瀾滄江與小黑江交匯處669米,相對高差2 564米。”[3]氣溫垂直變化明顯,是典型的立體性氣候。立春時節,兩壩區氣候已然明顯回暖,再無寒意,地里菜籽破土而出,稻田也可以插秧,開始一年的農活;而周圍半山地區還有微微寒意,插秧要延遲到四五月份;高寒山區夜里還需要生火取暖,熱量不足,谷類產量極低,近些年已改為種植烤煙等經濟作物。這樣的地理環境和氣候類型是雙江瘴氣形成的自然原因。
雙江瘴氣的肆虐,不僅是因為封閉的地理環境,悶熱潮濕的氣候類型,還源于當時人們落后的生產生活習慣。“勐庫勐勐……惜乎瘴癘橫生,病疫大起,……考煙瘴的來歷,成于地近熱帶,氣候炎熱,山嶺太高,氣流不暢者小半,而成于人畜雜居,污穢狼藉,死水滯積,腐菌滋生者實大半。”[4]生活污水和人畜糞便在高溫潮濕又密閉的環境中發酵,滋生細菌、腐氣,蠅蚊蛇鼠四竄。瘴氣在兩個壩區不斷積累發酵,瘧疾遍野。
雙江瘴氣主要是分布在南勐河沿岸的勐勐和勐庫兩個壩區。只有傣族敢在壩區居住,其他大部分民族居住在半山坡或者高山地帶。被采訪的當地人回憶道,在瘴癘高漲的時期,日間雖有壩外的人敢下去,但入夜即不敢住宿,哪怕是天生的硬漢,只要在壩內歇幾夜,沒有不送命黃泉的。因此,“除擺夷(傣族)民族外,四山已有人滿之患,還沒有任何民族敢下壩居住,以身嘗試”[5]。當時的雙江山區流傳著這樣一句諺語:“要下勐勐壩,先把婆娘兒女嫁。”由此可見山區人民對勐勐壩瘴氣的畏懼。民國勐勐城的新政府和簡易師范學校都因瘴氣的原因,冬春在勐勐縣城辦公和教學,夏秋為躲避瘴氣移至那賽。自有歷史記憶以來,雙江壩區瘴氣1950年解放軍進入雙江縣內,成立國營農場,疏通壩區河道,清理泥塘蘆蒿,采用化學制品殺蚊滅蠅,改善居民生活條件,直至1952年,瘴氣才得以徹底清除。
二、傣族遷入南勐河兩岸的歷史記憶
“雙江是多民族聚居的縣,縣的境域處在云南古代的百濮、百越、氐羌三大族群匯合的結合部。”[6]雙江于漢代(109年)起有史料記載,縣境為益州郡徼外地,東漢(69年)增永昌郡,縣境為所屬。此時縣內居住哀牢山古國的百濮是布朗族和佤族的先民。“《禹貢》梁州南徼地。殷、周時皆為蠻夷所居。或曰即百濮之國也。”[7]唐代至宋代,小黑江邊的賽罕村是布朗族在雙江境內最早的活動遺址,曾出土過大量生活器具,如土鍋、瓶罐等。瀾滄江畔的忙炭、巴哈、小忙賽出土的卡拉罐,是佤族文化特征的代表。“元代,拉祜族入遷。他們經今云南省臨滄市臨翔區的南美拉祜族鄉進入今雙江自治縣勐庫鎮西北部,在冰島一帶定居下來;以后逐步往雙江東南部的馬鞍山延伸,馬鞍山被稱為‘倮黑山’。”[8]雙江四個主體少數民族中,傣族是最后進入雙江定居的。元至正十六年(1356),傣族先民罕甸因戰爭擴展地盤,從麓川(瑞麗)東遷,于勐庫定居,這是傣族于雙江建立的第一個政權。后因勐庫發展人口較多,耕地資源有限,于建文四年(1402),罕珍帶領勐庫居民南遷勐勐河西岸,建立第二個政權勐景莊。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景東麓川思倫法軍與明軍交戰于摩沙勒(新平傣族彝族自治縣),思倫法軍戰敗。戰敗途中,思倫法軍攜沿路傣族居民一起向西逃竄。西渡瀾滄江后繼續西行,于南勐河東岸野宿。次日,難民占卜得出,此地適宜他們居住。從此,第二批勐卯傣族定居雙江,建立第三個政權勐允養。初期,南勐河東西兩岸的傣族居民來往頻繁,其后在圈控(大文鄉千信村)建立管理瀾滄江沿岸各民族村寨的行政機構,這是傣族于雙江建立的第四個政權。成化八年(1472),威遠土司聯合耿馬官罕邊法攻打勐景莊、勐允養及勐庫。勐允養、勐景莊、勐庫戰敗被征服。勐臥土司將其轄地勐允養和圈控送給其妹夫耿馬官罕邊法統一治理,并在瀾滄江邊大蚌渡口處立一巨石為界碑,以示瀾滄江以西勐臥的轄地、屬民從此永遠歸屬耿馬官罕氏統一治理,罕邊法即把勐景莊合并勐允養為勐勐,從此勐勐統一了。至明朝萬歷二十七年(1599),朝廷授罕曼子罕竟為勐勐巡檢土司巡檢,脫離耿馬官罕氏管轄直隸永昌府。由此,雙江第一個由中原統治者承認的合法政權正式成立。除有關傣族由勐卯遷入雙江的史料記載,在雙江民間還流傳著關于傣族人定居勐勐壩的民間故事。
傳說中,雙江傣族是從勐卯而來。由于當時麓川擴建,勐卯傣族被明朝軍退擊敗,勐卯部落中的兩兄弟帶著大象、傭人沿瀾滄江而下,經過思茅、鎮康、南傘。哥哥到南傘休息的時候,看南傘這個壩子適合居住,就決定留下。于是就對弟弟說,我分你一部分兵、牛、馬,我在這里作頭人,你往前走再去找一個地方。耿馬土司看到勐卯過來的公子,就把女兒陪嫁給他。哥哥就此和耿馬公主定居南傘。在傣語里,“南傘”就是指公主開發的地方。弟弟罕甸帶著其余的部落往勐庫方向走,看見勐庫水草豐茂、土地肥沃,就帶著當地的佤族、拉祜族一起開發。罕緬甸在勐庫養了很多牛,有一天傭人上山放牛,結果一只牛找不到了。第二天,水牛回到家中,頭上掛了很多水草。罕緬甸就讓傭人跟蹤水牛,讓他看看水牛到底去了哪里。第三天,傭人跟在水牛后面,發現水牛去了一個大旱塘。水牛去的這個大旱塘里有魚、藕、螞蟥,螞蟥身上還長著長長的毛,水牛跳到水塘里和龍打架,所以回去時頭上掛了很多水草。傭人回去就和罕緬甸說了大旱塘的事。旱緬甸來到傭人說的大旱塘,發現大旱塘比勐庫壩還大,就將勐庫壩的一部分人遷到大旱塘進行開發,大旱塘就是現在傣族人居住的勐勐壩(1)2019年3月13日于雙江勐勐鎮公很村俸國興(原雙江縣長,已退休)家采訪,內容根據訪談整理而來。。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選定的條件下創作,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創造。”[9]通過歷史文獻的梳理和對民間故事的整理,可以從中對傣族由于戰爭遷入雙江的歷史記憶窺探一二。首先,傣族是較晚進入雙江的少數民族,半山區和山區都已經被其他少數民族占領,只剩下南勐河兩岸的低谷區和壩區,因有瘴氣的制約而得以空置。這樣的歷史條件無疑給傣族提供了一個生存空間的選擇,且與其他山地民族避開了空間資源的競爭關系。其次,傣族淵源于古越人,秉承了越人善植水稻的文化特征。“遠在兩千多年前,傣族地區就有了以水稻種植為主的農業生產。”[10]在雙江傣族人的記憶里,是水牛帶他們從勐庫壩順著南勐河找到了土地更加肥沃和地勢更平坦的勐勐壩。水牛是農耕文明不可缺少的生產要素之一,這其中隱喻著傣族的生計方式決定了他們對居住環境的選擇。作為傳統種植水稻的民族,傣族的生產生活中離不開河流。南勐河流經勐勐壩,水流緩慢,兩岸地勢平坦,充沛的水資源為灌溉水稻提供了良好的生產條件。南勐河流經勐勐壩后,下游水勢湍急洶涌,兩岸都是懸崖峭壁,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之下很難對河水加以利用,所以住在下游的布朗族都是在半山坡上以種植陸谷為主。自然生存環境和社會生存環境的制約,也就將雙江傣族的居住分布限定在勐庫和勐勐兩個壩區。“南勐河”由傣語音譯過來,在傣語里是“母親河”的意思。在族群戰爭、空間資源、自然環境、生計方式的多種因素之下,傣族在南勐河的兩岸扎根下來,在瘴氣肆虐的生存環境中創造出屬于自己的智慧。
三、雙江瘴氣下的傣族智慧
瘴氣是傣族生活的雙刃劍。一方面,南勐河為傣族提供了優質的生存資源。傣族在壩區種植水稻、挖掘魚塘,將壩區建設成了一個天然糧倉,相比之下,半山坡或高寒山區的糧食產量要比壩區低得多。在當時各種資源的匱乏的歷史條件下,瘴氣成了傣族的天然保護屏障,山區居民或土匪對瘴氣的畏懼使他們不敢輕易下壩掠奪。另一方面,傣族并不是天生對瘴氣就有非凡的抵抗力,壩區的瘴氣在一定程度上威脅著傣族人的生命安全。當時壩區中流傳著“只見娘懷胎,不見兒趕街”的諺語,是當時瘴氣彌漫致使嬰兒較高致死率的真實寫照。感染瘴氣的人就會表現出發寒怕冷、高燒不退、全身發抖的病理表征。在這樣一個利弊雙生的生境中,傣族在生活習俗的方方面面都創造了屬于自己的文化。面對壩區瘴氣時,雙江傣族人以順應自然為原則,運用自己的生存智慧,在生計方式、宗教信仰、生活習慣、民族醫療等多方面順勢而為,最大限度利用自然資源,調試人與自然的關系,興利剔弊使社會生活與自然環境達成高度的適應性。
生計方式上,傣族依據傣歷的時間來進行農事活動,傣歷二月(農歷冬月)之時開始犁田,傣歷四月(農歷正月)開始撒秧苗做秧田,傣歷六月(農歷三月)開始插秧苗。在此農事期間,壩區瘴氣因氣溫較低還未生起,傣族的農耕活動有效規避了瘴氣最烈的時節。另外,種植水稻必然開墾荒地、開發蘆蒿地、大旱塘。在水稻種植過程中,雙江傣族人清理河道中的淤泥,開渠引水使河道暢通,翻曬土地減少蚊蟲滋生,一系列農耕活動有效地削弱了南勐壩區的瘴氣。
宗教信仰上,“明成化十六年(1480),罕廷法派18名頭人前往勐艮,請釋迦牟尼至勐勐傳法”。南傳上座部佛教傳入勐勐,至今雙江傣族全民信教。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節慶中有一個“毫洼節”,“毫洼”在傣語中是“進入三個月齋期”的意思。毫洼節從傣歷9月15日(即農歷6月15日)到傣歷12月15日(即農歷9月15日),整整三個月是傣族的齋期。這幾月壩子熱氣騰騰,是全年最熱的夏、秋兩季,壩區瘴氣升騰最嚴重之時。傣族已經完成了插秧、薅草、灌田等農事活動,就聽從佛爺和召勐的安排,進入佛寺聽經教化。毫洼節的進齋活動無形中將傣族與壩區最烈的瘴氣隔離,避免傣族因在田邊地腳從事生產勞動而沾染瘴氣。
生活習慣上,當時傣族還沒有掌握蔬菜種植的方法。蔬菜來源基本上是以野菜為主,如蘆子葉、豬鼻子草、魚腥草、香香菜、火鐮菜、酸包菜、杷哈菜等,這些野菜都具有清涼、解毒、消炎、降火的醫用價值,加之烹飪方式多為原始,以搗、拌、舂為主。這樣原汁原味的烹飪方式較好保存了植物中的維生素,又使食物風味頗佳,在炎熱的氣候中能有效清涼解暑。傣族的住房外形呈傘錐狀,被稱作“雞罩籠”,無樓層,只是平房。南勐河壩區有豐富的竹資源,傣族先民就地取材,用竹子、木頭、茅草建造“雞罩籠”。屋面用茅草鋪蓋,四面沒有窗戶,只在屋面南半廈中央開一道小長方形的草排窗。白天用撐竹撐開窗戶,入夜取掉撐竹即可。“雞罩籠”既有良好的透氣性,又能隔絕蚊蟲,可控制瘴氣通過蚊蟲傳播的渠道。
民族醫療上,傣族醫療對瘴氣瘧疾提出了治療方藥,并記載于佛經中。“方一,藥物:胡椒9粒。‘費丸’、‘查楞’,姜,藕節。混合舂細后內服,外擦。方二,病癥:三年宿根擺子,藥物:寬筋藤,曼陀羅根,黑蘇子。混合舂細,用酒為引,以溫水送服。”[11]今天,瘴氣已經不能再對當地人們的生活造成威脅。雖然無法驗證傣醫瘴氣的藥方是否真的靈驗有效,但這些遺留在佛經中的傣醫方藥至少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傣族先民在應對瘴氣造成的瘧疾時采取了積極的應對態度。他們對瘴氣瘧疾的癥狀加以描述,根據病情特點進行分類治療,認識生活中的植物特性,與疾病斗爭,對癥下藥。這些點點滴滴里無一不是傣族先民的智慧和對生活積極樂觀的態度。
四、結語
“生境決定生產,生產決定生活,由生境和生產所決定的生活方式一經形成,并固定為傳統和習俗,便會反作用于生產,并影響生境,這是民族文化體系中生態環境、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之間相互關系的一般規律。”[12]從上述幾個原因的透析中可見,雙江傣族人面對瘴氣這把雙刃劍時,采取了因勢利導的文化適應策略。瘴氣嚴重的生存環境下,雙江傣族先民通過水稻種植,開渠引水,清理河道淤泥,既能遏制瘴氣的形成,又能發展勞動生產。南傳上座部佛教中崇敬自然的觀念在傣族的思想和行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雙江勐勐壩區瘴氣最為嚴重的時節,當地通過緬寺進齋習俗減少人員外出活動,對傣族社區人員活動進行了有效管理,降低了人們感染瘴氣的概率。在生活實踐中認識自然界中的植物,從住房到飲食,無一不體現著人與自然的和諧精神。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雙江傣族先民沒有畏懼生活的考驗,而是創造了與之相適應的生存策略。從生產勞動、宗教信仰、生活習慣、醫療治理等,生活的多個方面相互調試,最大限度克服瘴氣對生活的影響,體現了雙江傣族先民在面對強大的自然外力時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