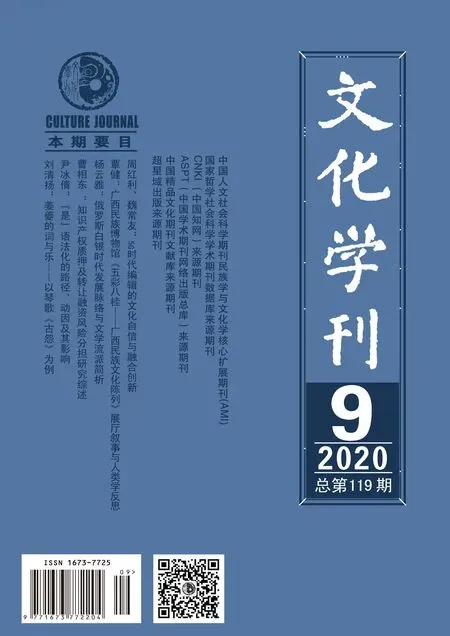淺析蘇童《河岸》的象征手法
于依洋
蘇童是當(dāng)代文壇最享有盛譽(yù)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始終以虛構(gòu)的南方小鎮(zhèn)作為故事的背景,文字中透著憂郁的氣息,深受讀者喜愛。可他不僅僅滿足于過去取得的成就,而是一直嘗試創(chuàng)造一種全新、突破自己傳統(tǒng)寫作技巧的敘述方式。《河岸》的出現(xiàn)被認(rèn)為是蘇童寫作生涯的一個(gè)關(guān)鍵的轉(zhuǎn)折點(diǎn)。河流對蘇童來說似乎有一種特殊的含義,因?yàn)橐恢庇幸粭l想象中的河流作為意象出現(xiàn)在蘇童的作品里。作品以河流作為貫穿全文的線索,描繪了“河上”與“岸上”兩類不同人群的生存空間和精神軌跡。此外,小說還構(gòu)建了“河”與“岸”這兩個(gè)既對立又共存的生活場景,塑造了在河上漂泊的苦難者形象,并表現(xiàn)了這群“漂在河上的人”窘迫的生存狀態(tài)。蘇童在作品中刻畫的各類事物不僅僅具有它們本身自帶的固有屬性,更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
一、河與岸的象征
蘇童在《河岸》開篇寫到: “向陽船隊(duì)一年四季來往于金雀河上,所以,我和父親的方式更加接近魚類,時(shí)而順流而下,時(shí)而逆流而上;我們的世界是一條奔涌的河流,狹窄而綿長,一滴水機(jī)械地孕育另一滴水,一秒鐘沉悶地復(fù)制另一秒鐘。”[1]作者從故事開篇就將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狀態(tài)與金雀河融合起來,他將洶涌的河流作為故事發(fā)生的場景,在河流的襯托下人類的生命變得非常渺小。作家通過第一人稱視角,通過兒子的敘述將父親的人生經(jīng)歷細(xì)細(xì)展開,將發(fā)生在“河上”與“岸上”的故事有機(jī)聯(lián)系成一個(gè)整體, 創(chuàng)造出一個(gè)歷史與現(xiàn)實(shí)融為一體的敘述空間。小說情節(jié)最初從河上開始,隨著故事的發(fā)展,庫文軒被剝奪烈士后裔的身份而被從岸上驅(qū)逐,最后只能來到駁船上,此后他的人生都與河流息息相關(guān),他的生命也在河流之中結(jié)束。
“河”象征著在河上生活的人被驅(qū)逐的人生,而河上的生活就是漂泊在河上的被驅(qū)逐者的生活。“向陽船隊(duì)一共十一條駁船,十一條駁船上是十一個(gè)家庭,家家來歷不明,歷史都不清白。”[2]向陽船隊(duì)的船員們多數(shù)都是帶有“污點(diǎn)” 的人,他們遭到世俗社會的忽視和拋棄,只能在河上漂泊,船只靠岸也必須接受審查,行動也受到限制,未經(jīng)允許就無法上岸活動。在岸上的治安隊(duì)員手持警棍巡邏,如果有人擅自上岸就會遭受懲罰。庫東亮是治安員重點(diǎn)監(jiān)視和修整的對象, 可其實(shí)這些名義上的“治安員”不過是一群街頭地痞和無賴,他們仗著自己“治安員”的身份隨意欺壓河上的人們。在壓迫下河上的人只能壓抑著自己對自由活動的渴望。河上的人隨著河水終日漂泊,一天中大部分時(shí)光無所事事,只好天天盯著河水發(fā)呆,好打發(fā)這無聊的時(shí)光。生活的壓力使人們的精神越來越麻木,他們想不到通過行動來改變他們的生存狀況,只是日復(fù)一日的虛度光陰。作者對向陽船隊(duì)船員生存狀態(tài)的表述,表現(xiàn)出了“河與岸”具體的象征意義。漂泊在河上的人們的生活壓力比岸上的人沉重許多,他們的苦難也就更難消解。他們?nèi)缤永锏聂~,依托著河水生存同時(shí)也承擔(dān)著水流的重壓,終日隨著河水漂泊,自己的命運(yùn)無法靠自己掌握。
“岸”是對油坊鎮(zhèn)日常生活的象征,岸上的世界才是現(xiàn)實(shí)世界。作品開頭部分著重表現(xiàn)了庫文軒一家在岸上生活時(shí)的美好場景,父親庫文軒由于屁股上有一塊魚形胎記,而被認(rèn)定是烈士鄧少香的兒子,由于身份帶來的好處得到了油坊鎮(zhèn)書記的職位,住在條件相對較好的房子里,也娶到了鎮(zhèn)上有名的播音員做自己的妻子,一家人過著令人羨慕的生活。可是,好日子沒過多久,專門調(diào)查烈士后裔的工作組來到了鎮(zhèn)上,經(jīng)過調(diào)查庫文軒并不是烈士鄧少香的兒子,他“成了來歷不明的人”。從此他們一家的生活產(chǎn)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妻子不僅離開了他,他也被認(rèn)定成需要贖罪的“罪人”,被岸上的人從自己賴以生存的岸上驅(qū)逐,只能帶著兒子庫東亮來到河上,“到向陽船隊(duì),也許不是下放,不是貶逐,是被歸類了”[3]。從此,父子二人在船上開始了長達(dá)13年的漂泊生活。
“河”與“岸”的二元對立形成了一種帶有象征色彩的獨(dú)特審美結(jié)構(gòu),象征著人們心理的病態(tài)與行為的悖離。岸上的人自視甚高而看不起河上的人,然而通過蘇童對岸上人們所謂“正常生活”的描寫卻更加突出了岸上生活的反常。無論是烈士后代的評估方法還是調(diào)查組的取證過程,都使人感到有某種程度的怪異,體現(xiàn)出人們?nèi)馀c靈的扭曲。而與岸上異常生活對比來說,河上的生活則更加簡單。他們相處時(shí)十分和睦,也能互相包容。可到了岸上,卻被岸上的人稱為“空屁”,用刻薄的語言對其進(jìn)行諷刺和挖苦,可在駁船上,沒有人用外號嘲笑他們。作者在刻畫被岸拋棄的河上生活時(shí)運(yùn)用了許多充滿溫情的話語,營造出一種溫暖和諧的氛圍,從側(cè)面表達(dá)出對現(xiàn)實(shí)生活的無奈,和對現(xiàn)實(shí)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也能有些溫情的期許。
“河”是一個(gè)與“岸”對立共存的世界,在河上生活的人們被岸上的主流社會所拋棄,只能在河上茍延殘喘艱難度日,自尊心也受到岸上人們的集體踐踏,就算得到短暫的在岸上活動的機(jī)會,在岸上的人眼中他們也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尊重。河與岸之間的對立沖突日益鮮明,兩個(gè)生存空間之間存在著一種“隱形的堡壘”,使河與岸兩個(gè)世界彼此理解融合的可能性趨近于無。
二、父與子的象征
在蘇童的許多作品中都出現(xiàn)了父子關(guān)系這一主題,蘇童認(rèn)為:“父子關(guān)系說到底也是基本的人際關(guān)系,背后是指向某種更大的社會倫理和政治關(guān)系。”[4]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河岸》中所展現(xiàn)的父子關(guān)系具有更豐富的象征意義。庫文軒這一父親形象象征著在經(jīng)歷動蕩后心理病態(tài)的人。父親波折的人生經(jīng)歷暗示隱喻了歷史時(shí)代發(fā)生的變局。他的權(quán)勢、家庭都是因“烈士后代身份”得到的,生活十分順?biāo)臁?墒牵?dāng)調(diào)查組將他的身世認(rèn)定為“懸案”,說他不是烈士鄧少香的兒子后,他因?yàn)樯矸荻@得的一切瞬間離他而去,他從天堂墜入地獄,被岸上的人當(dāng)做罪人而驅(qū)趕到了河上生活,從此開始了低潮的生活。他不愿與生活在駁船上的人交流,性格孤僻。在他身為油坊鎮(zhèn)書記時(shí)所做的出格的事在當(dāng)時(shí)看來好像沒有影響,可此時(shí)卻成為了他人生的污點(diǎn),想要抹去。庫文軒終日惶惶不安,最終痛下狠手, 切斷了自己“罪孽之根”, 他想通過這樣的行為來贖清自己過去犯下的罪。在他心中自己的烈士后裔身份高于一切,為了彰顯自己的身份,也為了紀(jì)念自己的“烈士母親”,他每年都大張旗鼓地舉行祭祀儀式,并且決不允許兒子質(zhì)疑烈士后代這一身份,竭盡所能來維護(hù)自己的地位。可當(dāng)他身上烈士后代的象征——魚形胎記消失后,他無法忍受這樣的痛苦,尤其是當(dāng)烈士石碑上自己的孩童圖像被抹去時(shí)他最后一絲希望也破滅了。最終他為了捍衛(wèi)自己所謂“烈士后代”的聲譽(yù)和尊嚴(yán)帶著石碑投水自盡。父親的悲劇是對烈士身份的扭曲渴望導(dǎo)致的,在對地位的追逐中他逐漸喪失了判斷的能力,所以自己的烈士后代身份被質(zhì)疑時(shí),他無法承受命運(yùn)的變故,只能漂泊在河流之上,最后生命也消逝在洶涌的河流之中,這樣的行為是對現(xiàn)實(shí)的逃避,也是對人生的無奈。
兒子庫東亮則象征了受原生家庭影響的無辜者。他的命運(yùn)一直受父親影響,不能決定自己的人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的不幸其實(shí)源自自己的父親。庫東亮的人生經(jīng)歷也反映了原生家庭對人的巨大影響,他沒有選擇自己生活的權(quán)力,隨著父親被剝奪烈士身份,家庭也遭受變故后,同齡的孩子總是想方設(shè)法欺負(fù)他,他們叫他“空屁”,認(rèn)為他是一個(gè)無足輕重的人。他巨大的心理壓力不僅源自于遭受同齡人的霸凌、父母婚姻的失敗,更是因?yàn)樗慷昧烁赣H所作所為而產(chǎn)生的心理厭惡。父親被岸放逐只能選擇河流,他也只能跟隨父親離開岸上,在河上生活了13年之久,他無法壓抑自己內(nèi)心對重回岸上的渴望和對曾經(jīng)自由生活的追求,這樣的愿望卻屢遭父親呵斥, 對岸上生活的興趣逐漸喪失。正當(dāng)他的生命漸漸枯萎,對自由的向往漸漸淡去時(shí),一個(gè)叫慧仙的女孩像光一樣出現(xiàn)在他的生命中。在慧仙長大,從船上回到岸上之后,他無法壓抑自己對她的思念,想再見她一面的渴望越來越強(qiáng)烈,甚至對慧仙產(chǎn)生了欲望,可這份心意他只能自己知道,像做了賊一樣偷偷隱藏起來不被人發(fā)覺,特別是自己的父親。因?yàn)樗母赣H將自己人生的所有失敗都?xì)w因于“欲火”,所以他不允許自己的兒子走上他的老路,要兒子記住這“血的教訓(xùn)”。為了慧仙,庫東亮開始與自己的父親抗?fàn)帲墒墙K究是徒勞的。庫東亮對父親的反抗看起來氣勢洶洶,可最終還是被歷史上的“河岸”阻隔, 他始終無法擺脫來自父親權(quán)威的壓迫,也無法逃離父親對自己生命意志的操控。
蘇童用充滿象征色彩的敘事話語賦予了河與岸、父與子豐富的象征意義,雖然作品中的時(shí)間、人物和情節(jié)都是虛構(gòu)的,可作者通過隱喻和象征的修辭手法含蓄地揭開了歷史神秘的面紗。蘇童在隱喻與現(xiàn)實(shí)之間穿梭,將修辭敘事和歷史經(jīng)驗(yàn)融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獨(dú)特的美學(xué)風(fēng)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