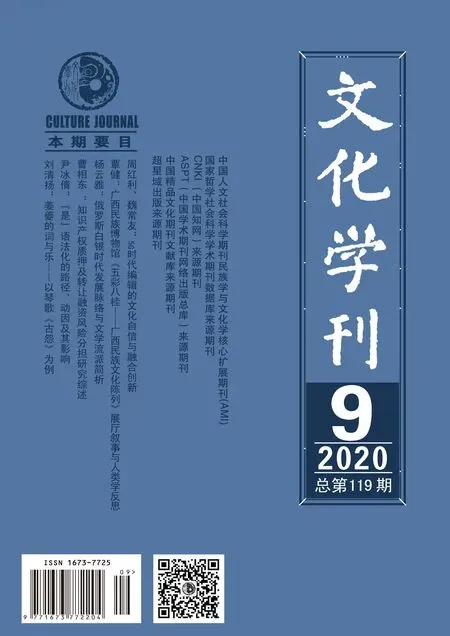論《兒童雜事詩》中的民俗情結
馮 妮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兒童首次成為文學舞臺上頗受關注的角色,既有冰心的《寄小讀者》、葉圣陶的《稻草人》等專為兒童而寫的作品,也有許多作家創作出為兒童發聲的文章。魯迅和周作人都熱切關注著兒童的精神世界,魯迅有過“救救孩子”的呼聲,周作人對兒童文學理論及外國童話的翻譯和介紹作出了重要貢獻。兒童和婦女的不幸是周作人雜文中持續關注的一個問題。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作人因叛國罪成為國民黨的“階下囚”。在服刑期間,周作人除了翻譯外國作品,唯一留下的原創作品就是《老虎橋雜詩》。1947年,周作人移居于東獨居,“稍得閑靜”,個人的心境終于得到沉淀,舊時的回憶重現眼前。1947年8月完成了《兒童雜事詩》的甲乙編共48首,1948年3月完成了《兒童雜事詩》丙編24首,詩體均為七言絕句,這一次的兒童書寫既是周作人感懷往事之作,又因其對民俗文化豐富的積累,故此蘊含著濃厚的民俗情結。
一、周作人的民俗經驗和兒童觀念
回憶兒時的舊夢,有限的虛構摻雜在真實的情境中,作家在過往的舊事中發現自己的童年。對于已成為過去的童年生活,巴什拉認為“季節才是回憶的基本標志”。中國的傳統習俗中有“四時八節”,這些時節最初是為了適應傳統農耕社會而出現的,久而久之便成為傳統節日。周氏兄弟的作品中經常出現以時節或民俗節日為背景的文本,魯迅的作品中有《社戲》《五猖會》《無常》等直接描寫節日的場景,周作人的作品更是直接以此為題。《兒童雜事詩》有許多以“時節”為題的雜詩,如《新年》《上元》《夏至》等。在《兒童的文學》一文中,周作人旗幟鮮明地呈現了兒童本位的思想主張。他站在現代人的立場來看兒童,與兒童相關的文章寫得較為深刻,仍脫離不了周氏文筆一貫的風格,“蘊含著苦味的閑適,攙和著詼諧的憂郁”[1]。《過去的生命》中收錄了三首名為《小孩》的同題詩歌,其中一首寫道:“我看見小孩,又每引起我的悲哀,撒了我多少心里的眼淚。”[2]兒童本應是天真快樂的,周作人卻更多地感受到兒童在傳統禮俗中和時事影響下的不幸。
對兒童的憐憫一直伴隨周作人前期關于兒童的創作。對于兒童文學,他在《王爾德童話》中稱安徒生童話的特點是像“小兒說話一樣的文體”,這是真正的兒童文學,這也幾乎概括了他對兒童文學的全部要求。但是,周作人在前期很少真正去創作為兒童所讀的文本。他在前期的創作中專注于兒童學的理論研究及童話翻譯,或者是把這種兒童心態作為一種精神和理念注入散文的創作之中。這種內在而又一貫的童心幾乎成為他的一種人生與審美的理想,并不斷在生活與作品中追求這種超然的境界,這些蘊積的理論觀點在《兒童雜事詩》的創作中如數體現。
二、民俗情結與童稚語言的結合
雜詩既非傳統詩詞,又與白話新詩相去甚遠。周作人在《老虎橋雜詩題記》中表示:“只是別一種形式的文章,表現當時的情意,與普通散文沒有什么不同。”[3]實際上,不過是作者意在用一種特殊的文體描繪自己一直心心念念的兒童。與散文文體不同,卻又能似散文一般表達相似心境。“它不是舊詩,而略有字數韻腳的拘束”[4],這或許是周作人用這種文體寫兒童雜事的原因。“用韻只照語音,上去亦不區分,用語也很隨便,只要在篇中相稱,什么俚語都不妨事”[5],所以雜詩像是歌謠,讀起來朗朗上口,適于為兒童所讀,這與他所倡導的“小兒說話一樣文體”不謀而合。
周作人在《兒童的文學》中對不同時期兒童的詩歌進行劃分,創造出自己獨有的兒童文學理論。他不僅是理論的創造者,也是這些理論的實踐者。他認為,在幼兒前期,兒童唱歌只為好聽,“第一要注意的是聲調。最好的是用現有的兒歌,……只要音節有趣,也是一樣可用的”[6]。到了幼兒后期,周作人指出兒童喜愛的詩歌“恐怕還是五七言以前的聲調”[7]。《兒童雜事詩》中通篇七言絕句,同時作注進行解釋,詩注用來解釋詩歌所描述的民俗、名物及讀音等鮮為人知的內涵。從整個文本的體例上來看,也有方言和俗語巧妙地融于七言絕句之中。白話的詩歌和文言的詩注之間形成一種語音和語義上的互文關系,這與周作人的文學主張是一致的。
周作人強調聲調是兒童前期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非常重視兒童雜詩的用詞和讀音。為了使詩歌音韻和諧,適于兒童唱讀,部分詩歌中對一些詞語的讀音進行了解釋。在《兒童雜事詩》中,有5篇詩歌在注中明確標示出詞匯是來自兒歌和童謠,如甲編《兒童生活詩》其六(上學)“龍燈蟹鷂去迢迢,關進書房耐寂寥。盼到清明三月節,上墳船里看姣姣”[8],注“兒童歌云,正月燈,二月鷂,三月上墳船里看姣姣,猶彈詞語云美多姣”[9]。還有一些詩歌,語言并非來自兒歌和童謠,而是來自俗語或者是民間口語,音節有趣可愛,語言活潑生動。如乙編《兒童故事詩》十二(陸放翁)中用“伢兒”一詞,注“杭州人稱小兒曰伢兒,讀如芽,浙中他處無此語,或是臨安俗語之留遺耶”[10],這一詞本是杭州地區的俗稱,在雜詩中表現出親切之感。《兒童雜事詩》中的俗語和兒歌均來自兒童,又為兒童而寫,融入七言絕句之中,這些詞語的運用使得舊體詩與兒童相得益彰,兩者在內容和形式上達到了充分自洽。
周作人在《兒童的文學》中稱:“將來的新詩人能夠超越時代,重新尋到自然的音節,那時真正的新的兒歌才能出現了。”[11]《兒童雜事詩》不受傳統意義上的字法、句法及聲韻的約束,用詞可愛詼諧,語調和諧輕快,來自小兒語或者民間口語的詞語被放置在兒童詩歌中,既不落俗套,又顯得親切可愛。這一方面有賴于他對民俗學的研究,另一方面少不了他對兒童的熱切關注。
三、民俗情結與諧趣內容的結合
周作人在《〈紹興兒歌述略〉序》中表示,故鄉的言語相對于故鄉的山水風物而言是最難擺脫的。同時提到:“普通提起方言似乎多只注重那特殊的聲音,我所覺得有興趣的乃在其詞與句,即名物云謂以及表現方式。”[12]地方話語獨特的表達方式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是考察某地地域文化的載體。在他看來,方言的意義不只在于語音上的獨特性,更重要的是語音所承載的風土民俗。在前期的研究創作中,周作人非常重視收集民俗學和兒童學的本土材料,這些都對《兒童雜事詩》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創作源泉。
周作人詩中的民俗大多源于江浙一帶,其中也略有幾篇涉及北方,尤其是北京的童謠,這也與周作人的人生經歷相關。他出生于浙江紹興,又在北京生活了很長時間,并潛心收集歌謠、童話,對兩地的民俗有深入的了解。甲編的詩歌以歲時為綱,從新年到中秋,有春節拜歲、上元節放燈、清明掃墓、端午習俗、中元鬼節、中秋夜祀等風俗。丙編對兒童的描寫從名物的角度出發,大多是某地風物,這與民間文化息息相關。花紙、童謠、玩具、姑惡鳥、河水鬼、目連戲等,取材于民間故事,或是某地獨特的風俗,或是民間傳聞。
四、結語
《兒童雜事詩》是呈現周作人傾心兒童的重要作品,并且與民俗學和兒童學的研究有著莫大關聯。周作人稱這組雜詩是“關于兒童論文的變相”,他把兒童本位的主張和民俗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七言絕句中,既是對傳統文化適度的保留,又是對先進的兒童文學觀念的發展。兒童的獨立人格一直以來被封建傳統所忽視,五四時期的作家一直在努力為兒童發聲,倡導人性,周作人為兒童所作出的這些努力無疑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