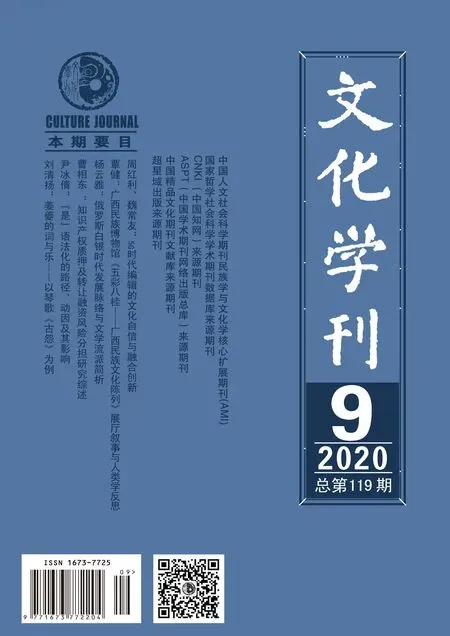從勒菲弗爾三要素理論看林語堂《大學》英譯
陳斌玉
《大學》作為儒家經典“四書”之一,因其承載了中國智慧,在傳播中國文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一直備受國內外翻譯者、學者的重視。而20世紀80年代,操控學派的代表安德烈·勒菲弗爾提出翻譯不應該僅局限于文本語言的研究,還應該將研究的視野擴展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面臨的意識形態、贊助人、詩學,也就是著名的勒菲弗爾三要素理論。這一理論打開了翻譯研究的新世界,為研究《大學》譯文提供了新視角。本文即以三要素理論為研究框架,深入分析著名國學大師、翻譯大家、曾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林語堂先生在翻譯《大學》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
一、三要素理論
安德烈·勒菲弗爾的“三要素”理論又稱為操控理論,是其于1990年出版的《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中首次提出。該理論認為對某一文學作品進行翻譯即是對作品的改寫,改寫的過程是對文本操控的過程。改寫文學作品的譯者并不是處于真空狀態,不受外界影響,恰恰相反,因為譯者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而翻譯“能夠投射出作者的形象”,使得譯者是“在另一種文化中工作,需要把那個作者和那些作品轉移到他們的文化的邊界之外”[1],因此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不是完全置身于社會文化之外,他們往往還會受到社會上意識形態、贊助人、詩學三要素的制約。
意識形態是一個社會的意識走向,“泛指存在于眾多個人或社會行為身后的思想與解釋系統”[2],是“反映特定經濟形態、特定階級或社會集團利益和要求的觀念體系”[3],它囊括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譯者的翻譯目的、在文本翻譯時譯詞的選擇、對文本內容的增加或刪減選擇,在很大程度上約束了譯者對文本的翻譯,操控了譯者的翻譯活動。不僅如此,意識形態還通過影響三要素之一的贊助人間接地對譯者進行約束、操控。贊助人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贊助譯者的翻譯研究,而只有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譯作才能讓贊助人從中獲利,因此,贊助人也會根據主流的意識形態對譯者提出相應的要求。
根據勒菲弗爾的觀點,贊助人是文學系統外部最大的影響因素,它隱藏在文學作品閱讀、創作以及改寫的內部,不容易讓人察覺出來。贊助人的類別繁多,可以是個人,如美第奇家族、路易十四,也可以是團體、教徒、政黨,還可以是現在比較常見的社交媒體,如新聞報紙、雜志等。這些贊助人通常關注文學的意識形態,以其為導向,通過提供譯者的稿費、幫助譯者所翻譯作品的出版發行等方式來操控譯者的翻譯。
三要素理論的最后一種要素為詩學。詩學,是一種關于詩歌的學問,其研究的對象為詩歌,但從廣義上來看,詩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僅局限于詩歌。詩學包含了文學的一切因素,一種詩學觀的形成包含特定的手法、體裁、中心思想、人物原型、場景及象征等,這些內容中的任何一個發生變動都會導致詩學形態的改變。從而可見詩學對文學系統的深遠影響。詩學也不是亙古不變的,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詩學,這就導致“那些曾被抵制的作品也可能隨著詩學的變化而重新被奉為經典”[4]。
綜上所述,勒菲弗爾的三要素理論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穎的視角,翻譯研究不應再局限于文本語言層面,還應充分考慮譯者所處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所擁有的文化背景等對翻譯的影響,推動了翻譯學的發展。
二、林語堂《大學》英譯介紹
《大學》原是《禮記》中的一篇文章,后由宋朝理學家朱熹將其摘出,成為“四書”之一部,此后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中國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在翻譯界深受學者的青睞。馬禮遜、理雅各、馬世曼、柯大衛、辜鴻銘、龐德等都對其進行過翻譯,少有人注意的是,林語堂先生也曾翻譯過《大學》。不同的譯者出于不同的目的、文化背景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林先生遵循其一貫的幽默筆調,以輕松而又不缺乏嚴謹的字詞將《大學》文本譯出。其《大學》譯本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別具新意,“既有通俗文學的趣味性,又兼具哲學著作的嚴肅性,極大地激發了讀者的閱讀興趣”[5]。
林語堂在翻譯《大學》時并沒有將其放置在“四書”體系下,而是在其用英文書寫的《孔子的智慧》(TheWisdomofConfucius)一書中將其作為單獨的一章存在。在《大學》一章中,林語堂為其制定的標題為“倫理與政治”,認為《大學》是以倫理和政治為主旨,“是專為教育王子貴人而作……而大學即王子貴人受教育之所”[6]。
林語堂根據朱子重新調換過全文順序的《大學》版本進行翻譯,但是又不完全依照這個版本。在他看來,朱子對段落錯亂的古本《大學》進行了梳理功不可沒,但是仍然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大學》中“此謂知本”有兩處重復,朱熹的做法是在第二句“此謂知本”與“此謂知之至也”之后補上一段他認為遺漏的結語,并“借此機會把宋儒以冥想為格物致知的道理插入書中一些”[7],林語堂則在仔細對比了東漢鄭玄的《大學》原文與朱熹的《大學》版本之后,得出版本“錯誤的由來是那相同的兩句‘此謂知本’,原來在那段文字是分開的”[8]的結論,即兩句“此謂知本”的位置錯亂了,要想更接近《大學》的原貌,需將其中一句“此謂知本”放置合適的位置。因此,林語堂的《大學》譯本雖是按照朱熹改編的《大學》原文順序進行翻譯,但他對“此謂知本”一句進行了位置的調動,把“原來承上啟下的那個雷同的句子,改放在我認為適當的所在”[9]。
縱覽林語堂《大學》譯本各方面的情況,可以推出這個譯本在傳播效果上受眾廣泛,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在歸納主旨上簡明扼要,直截了當;在版本選擇上慎重嚴謹,《大學》正文出于朱本又不完全對朱本亦步亦趨。總體上看,林譯本《大學》有諸多出彩之處,對當今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國文學作品“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三、從勒菲弗爾三要素理論看林語堂《大學》英譯
勒菲弗爾的三要素理論為《大學》英譯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點,使得《大學》英譯研究擁有了更廣闊的視野,擴大了研究者的研究范圍,將意識形態、贊助人、詩學納入其中,對林語堂《大學》英譯本更深層次的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
(一)意識形態
譯者的主觀意識與對象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否融洽,決定了譯作能否被對象國接受。“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林語堂先生一直以傳播中國文化,對外展示真實的中國形象,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為己任。1935年他在美國出版了使其名聲大噪的《吾國與吾民》之后,1938年,林語堂編譯了《孔子的智慧》一書。《孔子的智慧》是林語堂編譯的第一部中國經典,此書中囊括了《史記》中介紹孔子生平的《孔子世家》全文、《四書》之首《大學》全文、儒家哲學入門《中庸》全文、記載孔子語錄的《論語》全文、被認為是傳承了孔子學說的孟子的《告子篇》以及記錄了中國古代禮儀制度的《禮記》的部分篇章英譯本。
20世紀30年代美國民眾在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這樣巨大的社會動蕩、經濟變動之后,最終引發了人民的信仰危機。他們內心充滿了困惑、不安,對資本主義社會充滿了不信任以及對西方精神的懷疑。林語堂英譯的儒家經典所表達出的思想與這種思潮相對沖,對當時的美國民眾具有安撫效果,因此在美國受到廣泛的贊譽,久經不衰。
林語堂所處的時代的意識形態對他的《大學》翻譯產生了重大影響。林語堂熱愛中國文化,一心致力于中國經典對外英譯,使西方讀者了解真正的中國,西方由于自身的需要也正積極向東方尋求精神良藥,渴望從擁有五千多年歷史的中國獲取解決方案,二者一拍即合,造就了《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等經典的成功譯介。
(二)贊助人
前面已經提到,贊助人對譯者的翻譯活動有諸多影響,他們可以干涉譯者的翻譯,是“鼓勵、宣揚或者阻止、審查、破壞文學作品的各種有影響的社會勢力”[10]。贊助人可以有多種形式,隨著時代的變化,出版商形式的贊助人較為常見,他們對于作品的傳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林語堂先生的出版商為美國著名作家賽珍珠的丈夫理查德·華爾舍,林語堂在他的《從異教徒到基督徒》一書的附錄《八十自敘》中提到:“由于賽珍珠和她丈夫理查德·華爾舍,我才寫成并且出版了我的《吾國與吾民》,這本書的推廣銷售也是仰賴他們夫婦。”[11]由此可見贊助人對作者作品的推廣作用。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20世紀30年代,此時西方世界正面臨一場信仰危機,人心惶惶,人們向外尋求精神的寄托,這就使得一部分知識分子將目光轉向了東方哲學、中國思想,企圖從中尋找到美國的出路。
美國著名出版商蘭登書屋鑒于這種社會意識形態,邀請林語堂撰寫一本介紹中國哲學的著作,并將其列入《現代叢書》。蘭登書屋在美國出版業頗負盛名,其“《現代叢書》只出版經典之作”[12],出版的作品無一不是質量上乘。這種出版商主動邀請譯者進行創作、翻譯,并且得到其高度重視的情況下,對作家或譯者的社會地位、其作品的宣廣都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這也就是林語堂在海外聲名遠播,《孔子的智慧》一度成為暢銷書,包括《大學》在內的儒家經典為更多美國讀者所了解的原因之一。
贊助人對于作家或譯者名望的提高、作品的廣泛傳播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們對于時下的社會意識形態、讀者往往有著比作家、譯者更敏銳的感知,能夠迅速根據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讀者的喜好來選擇文本。可以說,一個合格的贊助人對于作家或譯者及其作品來說彌足珍貴。
(三)詩學
詩學是一種美學理念,是譯者為盡善盡美地譯介而采取的翻譯原則。林語堂在為吳曙天的《翻譯論》作的序《論翻譯》中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翻譯理論。他認為“翻譯是一種藝術”,為呈現好這種藝術,譯者需要在翻譯的過程中立足本國語言,在完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注重措辭,使譯文具有藝術美感。這是一個合格的譯者理應具備的素養,也是譯者對作者、讀者及藝術應負的責任。在以上三點規范要求上,林語堂繼而提出翻譯的三個準則——忠實、通順、美,這三個準則可以說是其翻譯理論的核心所在。忠實準則,要求譯文忠于原文,不改變原文的主旨中心;譯文通順,不佶屈聱牙,譯文才具有可讀性;譯文還要具有美感,給人以美的感受才能達到“以饗讀者”的目的。
詩學具有私密性、獨特性,每個譯者都有屬于自己的詩學,每個時代也都有每個時代的主流詩學,“不同的詩學在文學體系發展的不同階段占據主導地位,它們將以不同的、不可調和的方式來評判作品和改寫作品,所有這些方式都基于善意和信念,即每一種都是唯一真理的代表”[13]。這就使得譯者在從事翻譯活動時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主流詩學的約束,在遵循自己一貫的翻譯手法時也要考慮主流詩學,在其允許的范圍內進行翻譯。
值得慶幸的是,林語堂獨特的翻譯觀正好迎合了美國民眾的審美及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主流詩學,在“忠實、通順、美”的翻譯標準上,語調幽默,用詞精煉,使得《大學》譯文通俗易懂,“給西方讀者以一種舒暢的方式來解讀中國名著”[14]。此外,無論是在林語堂的創作還是譯作中,都可以發現他對個人內心世界的關注,重視作品對個人精神的滋養。這一點也與常見的西方文學作品中側重描寫個人思想的特征相差無幾。
創作者或譯者的詩學決定原文或譯文的質量,而對象國的詩學則決定了創作者或譯者的作品能否被其主流社會所接受。林語堂的《大學》譯本詞語簡約大方,既傳達了《大學》的中心思想,又兼顧了對象國民眾的審美需求,因而其翻譯創作能夠完美地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且掀起了一度席卷美國世界的“林語堂熱”的浪潮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結語
通過對林語堂的《大學》英譯過程的分析可以得出,勒菲弗爾提出的三要素對其翻譯活動存在影響力,產生了一定的操控作用。意識形態極大影響著林語堂對翻譯文本的選擇,贊助人影響《大學》譯文的傳播,詩學則影響了林語堂的翻譯技巧,在與這三種要素的博弈中,林語堂譯出了自己最滿意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