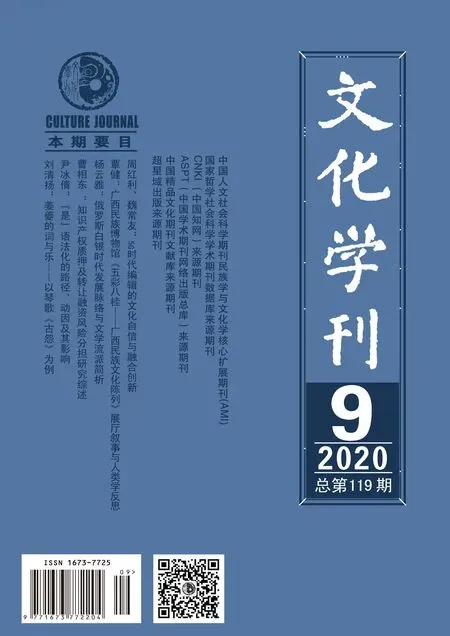論唐傳奇小說(shuō)中的法律
李 靜
用法律的角度去研究文學(xué)主要是從文學(xué)作品中去發(fā)現(xiàn)并提出一些法律或者是與法律相關(guān)的問(wèn)題,從這些法律問(wèn)題中我們可以更真實(shí)地了解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一些法律制度和法律觀念。當(dāng)然,文學(xué)與法律的影響是相互的,文學(xué)作品中法律問(wèn)題的出現(xiàn)有一定的意義,或推動(dòng)劇情往另一個(gè)方向發(fā)展,或顯示出深厚的意蘊(yùn)內(nèi)涵,或表現(xiàn)出某種特定的人文心態(tài)。
唐傳奇小說(shuō)題材內(nèi)容豐富,其中公案小說(shuō)和愛(ài)情婚姻小說(shuō)占不小的比重,所以其涉及的法律問(wèn)題也是種類繁雜,包括訴訟、婚姻的成立與解除、復(fù)仇、出軌、繼承、立嗣等。透過(guò)這些問(wèn)題,我們可以了解唐代法律制度中的弊病及其法律實(shí)施過(guò)程中的問(wèn)題,更重要的是把法律作為傳奇小說(shuō)中的一個(gè)文學(xué)因素,對(duì)其進(jìn)行分析,以了解法律在小說(shuō)中的作用。
一、唐傳奇中的訴訟法
唐傳奇小說(shuō)中有關(guān)訴訟的案例有很多,從提出訴訟的對(duì)象來(lái)看,有人的訴訟、鬼魂的訴訟、神仙的訴訟等,他們?cè)V訟的內(nèi)容十分繁雜,大到生死冤案,小到丟雞找狗,都可通過(guò)訴訟來(lái)尋求一個(gè)裁決。
(一)人的訴訟
人的訴訟是向地方官吏或者是主管事件的官吏申訴,通過(guò)正當(dāng)程序?qū)Σ竟靡跃S護(hù)自己的利益。蔣防《霍小玉傳》中李益疑妻子盧氏與人有私,開(kāi)始沒(méi)有證據(jù),后來(lái)看到有人從門口扔了一個(gè)盒子給盧氏,盒子里裝的是兩顆相思豆,盧氏辯解不清,隨后李益便經(jīng)常鞭打虐待妻子,直至訴訟到公堂把妻子休棄。
(二)鬼魂的訴訟
唐傳奇中關(guān)于鬼魂的訴訟最為豐富多彩,也更為沉痛慘烈。因?yàn)樗麄兊脑┣诂F(xiàn)世往往無(wú)法昭雪,死后則通過(guò)鬼魂的形式或直接向人間的官吏申訴冤屈,希望借法官之手給自己伸冤;或寄希望于上天和冥司,希望他們比人間的官吏正直無(wú)私。比如,牛僧孺的《齊推女》[1]中齊推之女齊氏在生產(chǎn)時(shí)被一個(gè)梁朝將軍的鬼魂要求搬出此房間,不搬就殺了她。而齊氏的父親齊推不從,第二天晚上齊氏果然死在房間。已成為鬼魂的齊氏不甘心自己陽(yáng)壽未盡便這樣死去,于是他找到丈夫韋會(huì),讓丈夫去訴求扮作教書(shū)夫子的冥王,務(wù)必忍受冥王的侮辱打罵以顯示誠(chéng)心,最后冥王叫來(lái)那個(gè)將軍的鬼魂對(duì)質(zhì),查明真相后懲罰了將軍并放走了齊氏。這便是一篇鬼魂借助生人的力量向冥司訴訟的作品。
二、唐傳奇中的婚姻法
唐代傳奇小說(shuō)中關(guān)于愛(ài)情婚姻的作品眾多,每個(gè)愛(ài)情故事中不可避免地會(huì)涉及那個(gè)時(shí)代有關(guān)婚姻的法律制度,比如締結(jié)婚姻和解除婚姻的程序、對(duì)于越軌和出軌行為的法律裁決等。
(一)婚姻的締結(jié)
唐代婚姻實(shí)行一夫一妻制,締結(jié)婚約突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必須由父母主持操辦,父母不在則由叔伯、兄嫂做主,而且必須有媒人作為中介存在,若無(wú)此二者,則婚姻不受法律保護(hù)。比如,《李娃傳》中鄭生到長(zhǎng)安應(yīng)試,遇名妓李娃便一見(jiàn)傾心,于是不顧禮法與李娃在一起。而當(dāng)他功成名就之時(shí),李娃提出離開(kāi)不耽誤他娶高門貴女,鄭生竟半推半就地答應(yīng)了。從這就可以看出,即便鄭生和李娃已一起生活多年,無(wú)論他們?cè)趺聪鄲?ài),沒(méi)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他們的婚姻仍然不能得到認(rèn)可,因而也就不受到法律保護(hù)。由此可以看到,唐代婚姻締結(jié)的程序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者缺一不可,這也是造成婚姻悲劇的原因之一。
(二)解除婚姻的法律程序
而傳奇小說(shuō)中正式解除婚姻的方式有休妻、和離。如《霍小玉傳》中李益認(rèn)定盧氏與人有私,最后一紙?jiān)V訟把盧氏休棄。唐代解除婚姻法的正當(dāng)法定程序采用“七出三不去”的制度,《唐律疏議》中對(duì)“七出”內(nèi)容的規(guī)定是“一無(wú)子、二淫逸、三不事姑舅、四口舌、五盜竊、六妒忌、七惡疾”[2]。女子若有七項(xiàng)情形之一的,丈夫或公婆即可休棄之。而實(shí)際情況比這一規(guī)定更加殘忍,如果一個(gè)丈夫想休掉妻子,無(wú)論他的妻子有沒(méi)有犯“七出”之過(guò),他都可以找到理由休妻,畢竟“欲加之罪,何患無(wú)辭”。由此也可見(jiàn)當(dāng)時(shí)女性地位低下,法律系統(tǒng)亦不完善。
(三)越軌行為的法律處罰
越軌小說(shuō)在傳奇文中也是屢見(jiàn)不鮮,唐朝相對(duì)開(kāi)放的社會(huì)風(fēng)氣是越軌行為發(fā)生的社會(huì)基礎(chǔ)。越軌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未婚男女私相授受,二是已婚男女一方出軌有奸情。青年男女之間的私情比如崔鶯鶯和張生、霍小玉和李十郎私自結(jié)為夫妻,雖然沒(méi)有明確規(guī)定這種行為是觸犯法律的,但是他們的這種私情不受法律保護(hù)甚至是違背禮法的,即使人們對(duì)被拋棄的女性表示同情,譴責(zé)負(fù)心男子,但在當(dāng)時(shí)這種悲劇結(jié)局是不可避免的。
唐律對(duì)已婚男女奸情有明確的處罰規(guī)定:“諸和奸,本條無(wú)婦女罪名者,與男子同。”《唐律疏議》載:“和奸,謂彼此和同者。本條無(wú)婦女罪名與男子同,謂上條‘奴奸良人者,徒二年半’,此即和奸不立婦女罪名,良人婦女亦徒二年半之類,并與男子同。”[3]可見(jiàn)唐朝對(duì)已婚男女通奸罪處罰還是相當(dāng)嚴(yán)重的,且這種處罰是要男女共同承擔(dān)的。但唐代傳奇中關(guān)于奸情的描寫很少有簡(jiǎn)單的寫男女通奸被處罰,多有因奸情而殺人的情節(jié),比如奸夫殺死奸婦的丈夫或者奸夫奸婦合謀殺死奸婦的丈夫,這就涉及通奸罪和殺人罪兩種罪行,關(guān)于上述情況唐律中也有明確的規(guī)定,《唐律疏議·賊盜》“謀殺期親尊長(zhǎng)”條(253)載:“犯奸而奸人殺其夫,所奸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4]即只要二人有奸情在先,且奸夫殺了奸婦的丈夫,不管奸婦知不知情,也與奸夫一樣犯了殺人罪,二罪并罰。比如《鸚鵡告事》[5]的故事中,楊崇義的妻子劉氏與鄰居李弇通奸并將楊崇義殺害埋入枯井,劉氏向官府報(bào)案稱自己的丈夫失蹤,縣官命人日夜搜捕竟無(wú)線索,后縣官到楊崇義家搜查時(shí),架上的鸚鵡告訴他了真相,他便立即將劉氏和李弇捉拿入獄,經(jīng)審問(wèn),二人招供,縣官將此事向皇帝匯報(bào),皇帝十分驚訝,封那只鸚鵡為綠衣使者,并將它送到皇宮內(nèi)喂養(yǎng),當(dāng)時(shí)的宰相張說(shuō)特意寫了一篇傳奇文《綠衣使者傳》來(lái)記載此事。在這個(gè)故事中,劉氏和李弇二人犯了通奸及殺人罪,雖并未直接描寫二人最終的量刑,但依當(dāng)時(shí)律法,二人同罪,當(dāng)斬。
三、復(fù)仇小說(shuō)中的法律
唐代傳奇小說(shuō)中涌現(xiàn)了一批復(fù)仇女性形象,這種故事一般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活著的人復(fù)仇,二是死去的鬼魂復(fù)仇。
(一)生人的復(fù)仇
活人復(fù)仇在唐人傳奇并不少見(jiàn),比如《賈人妻》寫一位名叫王立的縣令任期已滿,到長(zhǎng)安等待調(diào)令時(shí)遇見(jiàn)一位美麗的婦人,兩個(gè)人頗為投機(jī)就生活在了一起,還生了個(gè)兒子,如此過(guò)了兩年。一天,婦人拿著一個(gè)裝著人頭的皮囊對(duì)王立說(shuō)她有一仇人,今日大仇得報(bào),需要立刻離京。婦人看到王立驚恐的表情,稱自己不會(huì)連累到他,于是折回將兒子殺死別去。殺人是死罪,這一點(diǎn)身為官員的王立清楚,所以他驚恐,那婦人也很清楚,所以才會(huì)連夜離京出逃,為斷自己的眷戀之情,使王立免受牽連,甚至不惜將自己的兒子殺死。由此可見(jiàn),這一婦人盡管殺的是自己的仇人,也逃不過(guò)殺人償命的法律。但唐代游俠之風(fēng)盛行,有時(shí)法律的執(zhí)行頗受俠義之氣的影響,比如李公佐的《謝小娥傳》中,謝小娥為父兄報(bào)仇殺死兇手,本該依法償命,而太守贊賞她的志氣和行為,免她一死。
(二)鬼魂的復(fù)仇
鬼魂復(fù)仇大都是活著的時(shí)候遭受某種不好的境遇,死后心懷怨恨,因而以鬼魂的形式復(fù)仇。如《霍小玉傳》中,霍小玉死后變成鬼魂故意挑撥李益和妻子盧氏的關(guān)系,使得李益逐漸變得猜忌多疑,甚至因此將妻子盧氏休棄。傳奇小說(shuō)中屢屢出現(xiàn)鬼魂前來(lái)索命復(fù)仇事件,實(shí)則折射出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法律的不完善,它不能使生者依靠它而得到公正的評(píng)判,所以人們只能寄希望于虛擬的鬼神世界。
四、唐傳奇中的繼承法
唐傳奇中涉及的繼承問(wèn)題有二:一是家族財(cái)產(chǎn)繼承問(wèn)題,二是家庭地位繼承問(wèn)題。古代家庭人口眾多,結(jié)構(gòu)復(fù)雜,有妻妾、嫡庶、長(zhǎng)幼之分,家庭中每一個(gè)因素都可能影響繼承的權(quán)利。
在中國(guó)古代宗法制社會(huì)中,家族地位的繼承將女性排除在外,然而關(guān)于女性財(cái)產(chǎn)繼承權(quán)的問(wèn)題,唐代已經(jīng)有具體的法律規(guī)定。唐《戶令》:“諸應(yīng)分田宅者,及財(cái)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財(cái),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則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別與聘財(cái)。姑姊妹在世者,減聘財(cái)之半。寡妻妾無(wú)男者,承夫分。”[6]由此可見(jiàn),女子雖沒(méi)有男子繼承地位的權(quán)利,但是對(duì)于家中財(cái)產(chǎn)有權(quán)得到,不過(guò)這種財(cái)產(chǎn)繼承權(quán)只兩種女性擁有。一為未出嫁的室女,且她們繼承的份額只能是兄弟聘禮的一半,一般是給作為女子出嫁的嫁妝。但是,很多家庭財(cái)產(chǎn)并未能依法分配。比如,《霍小玉傳》中小玉本是霍王之女,其母親是霍王的婢女凈持,小玉頗受霍王寵愛(ài),霍王死后依照大唐律法其應(yīng)分得一部分財(cái)產(chǎn),但是其兄弟認(rèn)為她生母是卑賤之身,不承認(rèn)她的身份和地位,也沒(méi)有按照法律分給她一部分財(cái)產(chǎn),只是象征性地給了她一些錢財(cái)就把她趕出家門,而且還不準(zhǔn)她再以霍為姓氏,不能在外公開(kāi)她的身份。那兄弟分給她的錢財(cái)自然很少,這也為后文霍小玉淪為娼女做了鋪墊。二為守寡的妻妾可代替亡夫繼承應(yīng)有的財(cái)產(chǎn),且寡母在家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比如,《張褐妻》中張仁龜只是張褐與外室所生之子,從法律上來(lái)講,外室之子并沒(méi)有什么合法地位和繼承遺產(chǎn)的權(quán)利,即使提出訴訟也得不到任何財(cái)產(chǎn),張仁龜之所以能夠認(rèn)祖歸宗,絕大部分取決于嫡母的寬宏大度。當(dāng)然,也有毒辣的寡母與前任之子爭(zhēng)奪遺產(chǎn),例如,《滎陽(yáng)氏》中滎陽(yáng)氏的父親死后,繼母竟用毒把其兄弟姐妹毒死了,但是其繼母并無(wú)子嗣,害死他兄妹無(wú)非就是害怕與她爭(zhēng)奪遺產(chǎn)。可見(jiàn),雖有明法規(guī)定財(cái)產(chǎn)分割,但是家庭爭(zhēng)奪戰(zhàn)爭(zhēng)從來(lái)都沒(méi)有真正停息過(guò)。
五、結(jié)語(yǔ)
唐傳奇小說(shuō)中涉及法律的問(wèn)題并不罕見(jiàn),因?yàn)樗囆g(shù)來(lái)源于生活,好的文學(xué)作品必然有生活的影子,而生活中的矛盾糾紛解決必然需要法律的幫助,這里的法律則是豐富文學(xué)作品的一個(gè)內(nèi)容。不論是提出訴訟以尋求公正的結(jié)果,還是策劃復(fù)仇以解心中怨恨;不論是欣喜締結(jié)婚姻,還是負(fù)心解除婚姻;不論是絞盡腦汁爭(zhēng)奪財(cái)產(chǎn),還是大度公平分配,這些都是生活中會(huì)存在的真實(shí)情況。對(duì)唐代傳奇小說(shuō)中涉及法律問(wèn)題的探討讓我們了解到唐代法律的實(shí)施情況,從而折射出那個(gè)時(shí)代人們的思想意識(shí),這是唐傳奇重要的史學(xué)價(jià)值之一。反之,從文學(xué)與法律的角度研究傳奇小說(shuō),更有助于我們多角度理解傳奇小說(shu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