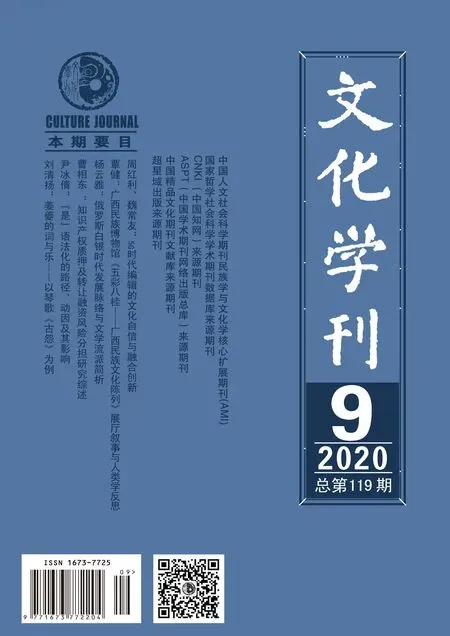渤海國與南詔國的民族關(guān)系問題比較研究
——從民族沖突與融合中管窺文化異同與存續(xù)規(guī)律
許冠華
渤海國和南詔國是我國唐朝時期邊疆地區(qū)的民族政權(quán),其所形成的渤海文化與南詔文化皆是中華民族文化史長河中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針對民族文化的研究,首先應(yīng)立足于孕育文化本身的民族,因此,將渤海國與南詔國的民族關(guān)系問題進行比較研究,可以清晰梳理出兩種民族文化的發(fā)展脈絡(luò),認識同一時期不同地域的文化所存在的相似性與特殊性,也能夠從兩者民族的沖突與融合中發(fā)掘文化存續(xù)的規(guī)律;同時,比較研究兩者對于我國民族文化史、邊疆史、地域文化差異等方面的研究亦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渤海國與南詔國歷史概述
(一)渤海國歷史概述
從大祚榮于公元698年自立大震國始,渤海國統(tǒng)治前后長達229年。其作為唐朝的藩屬國,積極地吸收先進的中原文化,其孕育的民族文化實現(xiàn)了與唐朝“車書本一家”,使得東北地區(qū)的社會經(jīng)濟文化得到了空前發(fā)展。渤海國全盛時,疆域覆蓋了我國東北地區(qū)大部及朝鮮半島北部、俄羅斯沿日本海的部分地區(qū),被稱為“海東盛國”。
渤海國為契丹所亡后并未留下渤海人自撰的史籍,其文化亦遭到了重創(chuàng)。當(dāng)前,針對渤海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只得通過《舊唐書》《新唐書》,日、朝兩國《續(xù)日本紀》《三國史記》等史料,以及貞惠公主墓、貞孝公主墓志,西古城、八連城等考古發(fā)現(xiàn)一窺渤海國的繁榮。
(二)南詔國歷史概述
自公元738年唐朝遣中使李思敬冊封皮邏閣為云南王,至902年被權(quán)臣鄭買嗣所篡,南詔國在我國西南地區(qū)共存在了165年。其統(tǒng)一六詔立國的背后既是其既定同一戰(zhàn)略的實現(xiàn),也是唐朝制衡吐蕃策略的貫徹。處在唐朝與吐蕃兩大勢力夾縫的南詔左右逢源,對唐朝時叛時附,與吐蕃且戰(zhàn)且和,但依舊沒有徹底擺脫對于唐朝的依附關(guān)系,亦依托于先進的中原文化推進了西南邊疆地區(qū)社會的發(fā)展及民族的融合。
我國歷代史家亦十分關(guān)注南詔國的歷史文化,有關(guān)記載不僅存于《舊唐書》《新唐書》《新五代史》《舊五代史》《資治通鑒》《云南志》等著名史籍中,更有《白古通記》《南詔野史》這樣的口傳歷史可供參考。同時,關(guān)于南詔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與存世文物也較為豐富,其中太和城遺址、羊苴咩城遺址與《南詔德化碑》等遺存最具代表性。
二、渤海國與南詔國的民族構(gòu)成
(一)渤海國民族的構(gòu)成
關(guān)于渤海國民族的構(gòu)成,古代文獻中有著明確記載。
《新唐書》有言:“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新唐書》又言:“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為左驍衛(wèi)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tǒng)為忽汗州,領(lǐng)忽汗州都尉,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1]
不難看出,渤海國為靺鞨人所建立,一度以靺鞨為號,直至唐冊封大祚榮為渤海郡王之后才“專稱渤海”。除靺鞨人之外,伴隨著渤海國的建立、發(fā)展、擴張,又有靺鞨之伯咄、安車骨、號室和挹婁、扶余、穢貊、沃沮故地原住民以及部分漢族和部分高句麗遺民加入。在相對統(tǒng)一的地域、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他們汲取先進的中原漢文化,并以其為紐帶,逐漸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體,即金毓黻先生于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渤海民族”。
(二)南詔國民族的構(gòu)成
關(guān)于南詔國的民族構(gòu)成,樊綽《云南志》卷四中記載:“西爨,白蠻也,東爨,烏蠻也。”[2]其中,“白蠻”源于兩漢時期西南夷中的滇僰、叟,并融合了大量的漢族及其他民族成分,“烏蠻”則是源于西南夷中的昆明與叟。
關(guān)于建立南詔國的蒙氏家族,目前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其為出自氐羌系統(tǒng)的烏蠻,但“貴族階級中數(shù)量占優(yōu)勢的卻是白蠻”[3]。由此可見,南詔國的主體并非由單一的民族構(gòu)成,其是二元化甚至是多元化的。王吉林先生言:“南詔一詞,非僅指統(tǒng)治階級之烏蠻,實指一聯(lián)合政權(quán),而非一單純之民族政權(quán)。”[4]
綜上所述,渤海國與南詔國都是唐朝的藩屬,是邊疆地區(qū)的民族政權(quán),其民族構(gòu)成多受其所在地域固有民族以及與中原漢族交流的影響。渤海國民族構(gòu)成的主體相對比較明確,其以靺鞨為核心,以漢文化為紐帶,逐漸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體;而南詔國民族構(gòu)成的主體相對比較復(fù)雜,作為建國者的“烏蠻”與構(gòu)成貴族的“白蠻”實際上也是兩個民族共同體。
三、渤海國與南詔國同周邊民族的關(guān)系
(一)渤海國與周邊民族的關(guān)系
渤海國周邊存在諸多民族政權(quán),下文筆者將從渤海國與契丹、突厥、黑水靺鞨三族的關(guān)系入手,對渤海國與周邊民族關(guān)系進行分析。
位于渤海國西部的契丹以畜牧漁獵為業(yè),雖與靺鞨一族早有往來,但兩者關(guān)系在渤海建國之后一直處于緊張狀態(tài)。渤海國在其扶余府“常屯勁兵捍契丹”[5],在長期的軍事壓制下,契丹與渤海之間形成了難以化解的民族矛盾。依以耶律阿保機所言:“惟渤海世仇未雪,豈宜安駐?”表明兩者之間早已存在軍事對抗與仇恨情緒。隨著民族矛盾的激化與兩者實力的消長,渤海最終于公元926年為契丹所滅,令人唏噓。
突厥是渤海國西北部的強鄰,是一支逐水草而遷的典型游牧民族,在唐初勢大時一度對契丹、靺鞨等族形成了控制。大祚榮建立大震國后,便遣使通于實力強大并在東北地區(qū)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突厥,以表達善意。由此可以看出,渤海國對于突厥有一定畏懼。
黑水靺鞨屬靺鞨七部之一,雖與渤海粟末靺鞨同源,但仍存在著矛盾與役屬關(guān)系。《新唐書》有言:“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當(dāng)黑水靺鞨遣使入唐時,大武藝對其屬下說道:“今請?zhí)乒俨晃岣妫潜嘏c唐腹背攻我也。”這表明了渤海國對于黑水靺鞨部的猜忌與戒備[6]。
(二)南詔國同周邊民族的關(guān)系
南詔國與周邊民族的關(guān)系實際上是與周邊諸蠻部的關(guān)系。
傣族先民“金齒百夷”,于南詔時期建立了茫乃政權(quán),南詔西開尋傳,于其地置麗水節(jié)度,將之納入控制之中。“么些”首領(lǐng)西可剌土因“陷交趾”之功,被南詔第十二代王隆舜封為“越析詔武勛公”。“撲子蠻”勇武,在南詔時期常被當(dāng)作軍隊的主力。公元862年,南詔進攻安南,有“撲子蠻”為唐軍所擒,“拷問之并不語,截其腕亦不聲”,表現(xiàn)十分英勇[7]。除此之外,“望蠻”“外喻蠻”等亦為南詔作戰(zhàn)。
不難發(fā)現(xiàn),渤海國對周邊民族的態(tài)度較為謹慎,對異族契丹部署重兵提防,對強大的突厥遣使相交,對同宗的黑水靺鞨加以控制役屬;南詔國則有所不同,其對于周邊蠻族部落比較優(yōu)容,在利用中逐漸融合,使其服務(wù)于南詔的統(tǒng)治。在分析的過程中亦可發(fā)現(xiàn),渤海國周邊的民族環(huán)境較為復(fù)雜,其周邊民族的強勢使其一直有較高的危機意識;而南詔國由于“烏蠻”及“白蠻”勢大且相對穩(wěn)定,周邊諸蠻部大多對其構(gòu)不成威脅,故敢于主動地接觸甚至融合。
四、渤海國與南詔國同唐朝漢族的關(guān)系
大祚榮建立大震國后便意識到了中原文化的先進性。渤海國想要實現(xiàn)社會進步、經(jīng)濟發(fā)展、文化繁榮,就必須與唐朝改善關(guān)系,同漢族學(xué)習(xí)。因此,大祚榮于公元705年接受唐朝招慰,表示臣服。公元713年,更是接受唐朝冊封,正式成為唐朝的藩屬國。其后,渤海國雖在大武藝時期與唐朝有過唯一一次短暫的沖突,但在“安史之亂”等動蕩時局的考驗下,仍與唐朝保持了穩(wěn)定的關(guān)系。
從歷史的發(fā)展中不難看出,渤海國與唐朝的漢族的關(guān)系相對穩(wěn)定,這種穩(wěn)定關(guān)系不僅是政治上的需要,更是源于渤海民族對唐朝漢族先進文化的渴望。據(jù)統(tǒng)計,渤海國存在的229年間,渤海派人到唐朝朝貢就達160余次,最頻繁時一年竟有五六次之多。而且,不論渤海國通行的語言文字、政治制度還是宗教哲學(xué)、藝術(shù)審美,都可見唐朝漢文化的蹤影,如渤海國中京顯德府遺址中出土的漢字文字瓦和蓮紋瓦當(dāng)?shù)取?/p>
而南詔國與唐朝漢族之間的關(guān)系相對比較復(fù)雜。起初,由于對吐蕃遏制戰(zhàn)略的需要,唐對南詔采取了支持與冊封的手段,雙方建立起了藩屬關(guān)系;隨后,由于南詔謀求向東吞并爨區(qū),唐朝對其勢力的擴張無法容忍以至兵戈相向,導(dǎo)致其與唐朝之間的藩屬關(guān)系暫時中斷;而在“安史之亂”后,南詔無法忍受吐蕃對其的剝削,便同唐朝會盟點蒼山,重新建立起了藩屬關(guān)系。
但是,這種時叛時附的反復(fù)多為政治與時局左右,并非南詔民族面對唐朝漢族時的真正心態(tài)。《僰古通紀淺述》載:“威武王化外一土酋也,以父興宗入貢于唐,故知中華禮樂教化,尊祀孔子,爰尊父命而建文廟。”[8]南詔國在宗教文化方面亦受到了中原的影響,《南詔德化碑》中“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就是道家哲學(xué)的體現(xiàn)。此外,南詔國在政治體制、語言文字、文學(xué)藝術(shù)等方面皆受到了唐朝漢族文化的影響。
由此可見,在政治上,渤海國與南詔國同中原王朝的藩屬關(guān)系,由于時局及利益訴求的變化而有所反復(fù);但在民族文化上,兩者同漢族的交流與學(xué)習(xí)似乎并未被阻隔,漢文化也一直深刻地影響著渤海與南詔的民族文化。拋開政權(quán)之間的斗爭來看,渤海國與南詔國同漢族之間的交流未曾中斷,二者對于先進漢文化的渴求也是一致的。
五、結(jié)語
在民族構(gòu)成上,渤海國統(tǒng)治集團以粟末靺鞨為核心,民族構(gòu)成相對較為鮮明,而南詔國兼有“烏蠻”與“白蠻”,其民族構(gòu)成是二元化甚至是多元化的;在民族生存環(huán)境上,渤海國周邊分布著突厥、契丹、新羅等民族政權(quán),可謂群強環(huán)伺,而南詔國周邊諸蠻部大多對其不構(gòu)成威脅,其生存環(huán)境也相對寬松;在處理同周邊民族關(guān)系的問題上,渤海國采取了戒備提防、控制役屬、軍事打壓的策略,而南詔國更多采取了恩威并施、融合同化、納為己用的方針。這些在民族關(guān)系問題上存在的差異直接導(dǎo)致了渤海國亡于契丹,其文化也在民族仇恨的殺伐中化為了歷史的塵埃。反觀南詔國,其雖經(jīng)歷了鄭買嗣篡國等一系列動蕩,但主體民族并未衰亡,文化更是伴隨著民族的繁衍得以存續(xù)。由此可見,民族關(guān)系問題對于一個民族文化的存續(xù)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由于這樣的對比分析實屬首次,其中尚有不合理之處,但這種對比對于渤海文化、南詔文化、中華民族文化史、邊疆史以及當(dāng)今的東北地域文化與西南地域文化的研究和發(fā)掘,想必是有一定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