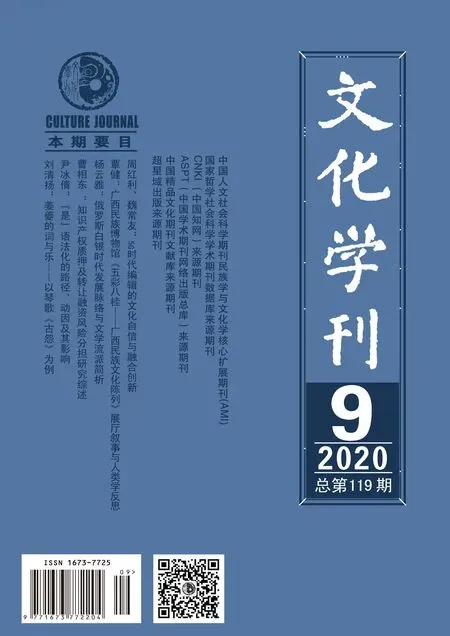明不亡于流寇 而亡于廠衛
——論廠衛制度建立的原因及廠衛對明朝滅亡的影響
呂黃艷
一、廠衛制度建立的原因
特務機構,作為歷代皇帝加強專制統治、集中皇權的工具,經歷歷代的演變與發展,在明朝達到了頂峰。明代的特務機構合稱“廠衛”。“廠”指東緝事廠、西緝事廠、大內行廠,分別簡稱東廠、西廠、內廠。“衛”指錦衣衛。錦衣衛設立于洪武年間,東廠設立于永樂年間,西廠設立于成化年間,內廠設立于正德年間。“廠”與“衛”的職權大體相同,但自從“廠”設立后,其勢力大于錦衣衛。這幾者的職權與關系大體為錦衣衛偵伺一切官員,東西廠則偵察官民和錦衣衛,內廠則監視官民和東西廠。四者直接對皇帝負責,由皇帝領導與監督,構成一整套嚴密的特務體系。廠衛制度的施行使明代政治陷入黑暗。時人談“廠衛”色變,尤以官員為甚。洪武年間,《萬歷野獲編》第二十一卷有曰“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可以說,廠衛制度是明代變態政治制度的典型代表,也是加速明朝滅亡的重要成因。
廠衛制度的建立有著很深的歷史原因。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貧寒,艱苦征戰,西平陳友諒,東定張士誠,北伐元廷,最后統一中國。他深感打江山的艱辛,“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1]只有不斷強化手中的權力,使官員無侵奪皇權的機會與可能,才能鞏固朱氏江山。鑒于此,他設立錦衣衛監視百官,這便是廠衛制度的開端。后來他又借胡惟庸案、藍玉案廢除宰相制,并立下嚴旨祖訓:“以后子孫做皇帝時,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宰相制的廢除,結束了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皇室、政府分立分權的良性傳統,使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成了獨夫政治。正如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黃宗羲所言:“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2]明成祖朱棣以叔篡侄皇位,為肅清反對者,進一步控制朝廷官員,強化專制集權,又增設東緝事廠,獨夫政治又勝一籌。至此,廠衛制度已漸成熟,廠衛宦官雖無“宰相之名”,已有“宰相之實”。正如黃宗羲所言:“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蓋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為科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故使宮奴有宰相之實。”[3]因此,可以說廠衛制度是“特務政治是獨夫獨裁極端化的結果”[4]。
廠衛制度建立后,“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進而奪得“氣勢不可近”的囂張地位,背離了設立時的初衷,無惡不作。明末沈起堂就有論:“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廠衛。”縱觀整個明史可以看出,廠衛這個特殊的特務機構的確成了明朝滅亡的加速器。
二、廠衛制度對明朝滅亡的影響
(一)亂法制,無立國之基
君統與相統的分立分工是中國古代良性政治制度重要的法理特征。從法理上來說,中國古代良性政治傳統有“君統”與“相統”二系。君統的代表是皇帝,相統的代表是宰相;“君統”代表國家的團結與統一,“相統”則負責實際行政責任。由于中國獨特的家國同構的文化道路,君統、相統的分界并不是特別明晰。但從鼎盛時期法理上的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實踐來看,良性的政治傳統應該是君統、相統分工明確。如漢代君統與相統分工明確,負責監察的御史大夫統屬于相統,而非直接統屬于皇帝。御史大夫不僅可劾奏不法的大臣,還可奉詔收縛或審訊有罪的官吏,監督審訊皆有章可循,與明朝“廠衛”侵奪“三法司”職權,任意監督、逮捕,甚至處死官員不啻霄壤。再如唐代三省六部制,分工更加明確。在政令出臺的環節中,皇帝所起的作用亦只是畫“諾”而已。如果皇帝不經三省六部直接下詔,是可以不被遵循的,故有《舊唐書》第八十七卷《劉祎之傳》中“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之說。此外,唐代司法監察設有刑部、大理寺、御史臺等,分別負責案件的審理、審批、監察百官與諫諍皇帝。正是因為有了君統、相統的相互制約,漢唐時期政治較為清明,國富民強。而明代廠衛一反良性的政治傳統,皇帝可以通過廠衛這種不符法理機構執行個人好惡,對稍忤其意的官民,任意逮捕、審訊、處死。這使得舉國臣民噤若寒蟬。“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5]法制已廢,基石已無,何談立國?
(二)亂朝堂,無立國之本
廠衛設置之初便擁有了凌駕于三法司之上的偵緝、審判、關押刑拷的司法大權,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后法司”[6]特權,這為其控制朝臣,進而控制內閣、代行內閣大權提供了便利,如武宗時期的劉瑾已被稱為“立皇帝”,權傾天下。正如龍文彬所說:“自來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之周,再傳而法制盡隳,釀成禍本,以至覆國。”[7]此外,大多廠衛宦官長期壓抑、心理扭曲,對蔑視他們的官僚士大夫有著濃重的仇恨心理。廠衛利用統治者的猜疑之心和自身的權利之便,為自身排除異己,禍害忠良,以致《明史·刑法志》有“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獄中,數更大獄,多使斷治,所誅殺為多”的記載。至此,功臣、忠臣皆為所害,臣僚有言不敢發,大多成為唯唯諾諾之臣。由此,朝堂之上多為沆瀣一氣者、茍且偷生者,國無棟梁,何來立國之本?
(三)亂民心,無固國之根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8]由此可見,民心穩固實為統治者鞏固其政權的根基。《明史講義》有云:“宦官無代不能為患,而以明代為極甚。”[9]這個時期,廠、衛合勢,特務遍布天下,大獄、酷刑大興。無論大小事宜,盡在其控制監視的范圍之內,以致“舉凡兵部有無塘報,城門關防出入,地方失火,雷擊何物,京城物價,禁地人命及至家人米鹽猥事”[10],“或以一人而牽十余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11],人人自危,草木皆兵。此外,廠衛利用職務之便霸占民田逼勒獻地,控制稅務、鹽利,開設皇店,大開礦產等,大大加重百姓負擔。廠衛制度的建立打破了原本就很脆弱的國家法制體系,完全以統治者和廠衛的好惡為好惡。這種結構的設置把人民逼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軟弱的人變得逢迎,投機鉆營,放棄正義,茍且偷生,社會風氣敗落,忍無可忍的人揭竿而起。誠如《明史·李戴傳》第二二五卷中李戴所言:“此輩寧不愛性命哉?變亦死,不變亦死,與其吞聲獨死,毋寧與仇家倶糜。”也就是所謂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道理。
(四)亂邊防,無御國之力
到明朝時期,“各邊防守之寄,益周于前,如各方面有險要者,俱設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各一員,下人名為三堂”[12],宦官竟成了和鎮守邊關武將一樣必不可少的固定官職。但是,大多數廠衛派出的宦官沒有治軍之才和征戰沙場的經驗。他們鎮守邊境,帶兵打仗,大多是為從中撈取好處。正如岳鵬舉所說:“宦官竟然將邊防兵力幾乎掏空,戰斗力極弱,致使明王朝腹背受敵。”[13]史料記載,廠衛“官員”到任后不是整肅軍隊,而是用軍隊開礦,修建私人房舍,克扣兵晌,敗壞軍紀,中飽私囊,這大大折損了軍隊的戰斗力。并且,宦官大多貪生怕死,如遇戰事,為求自保,故不派兵支援,延誤戰機,以致“賊勢猖獗,官軍失援……力戰死之”。更令人氣憤的是,宦官以個人好惡誣陷或提拔鎮守武將和地方官吏,致使軍中無良將,邊塞無清官,邊防局勢進一步惡化。更有甚者,為詐冒軍功,宦官有時濫殺外國貢使冒賞,挑起民族戰事,這無疑給岌岌可危的邊防雪上加霜。因此,廠衛做鎮守、守備駐邊防,一不能穩軍心,二不能利戰事,三不能抵外辱,使明王朝無御國之力,其加速滅亡愈加明也。
三、結語
簡言之,以廠衛為代表的特務制度在建立初期鞏固了新生政權,“滿足了明代加強皇權的需要”[14],實現了“對國家進行更為有效的控制”[15],但總體來說,這種制度違背中國政治制度的良性傳統,嚴重破環了國家的正常法制秩序,加速了明王朝的腐化與墮落,激化了明代的社會矛盾,蠶食了國家經濟軍事實力,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