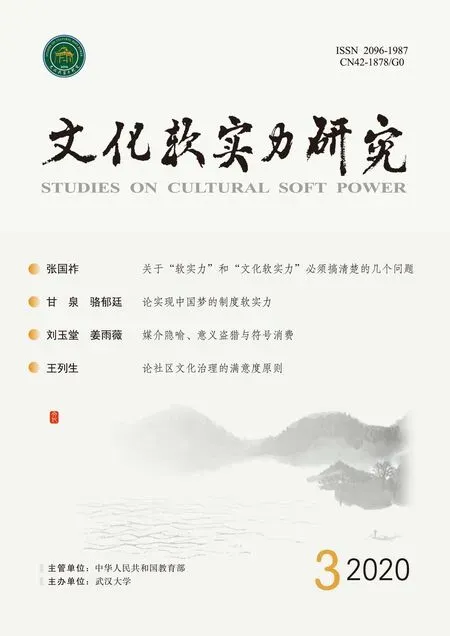論社區文化治理的滿意度原則
王列生
當代社會轉型至“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形態以后,扁平社會結構條件下治理效果無論主觀性把握還是客觀性分析,宏觀界面還是微觀界面,滿意度都會以基于個體獲得感的集體統計參量形式,成為計量社會學抑或公共管理學不可或缺的技術功能知識工具。正因為如此,對于邊際縮微的社區文化治理而言,其效度測值或者對績效標桿預期的后果評價,也就與此相一致地演繹為“滿意度原則”,一種與“公平性原則”“效率化原則”價值地位同步而功能指向相異的基本原則。所謂“一系列具有潛力的政策工具,以及每一個所擁有的多種設計選擇,使得找到適合幾乎各種情境并且在該過程中將眾多社會行動者帶入解決公眾需求的事業當中的工具成為可能”①萊斯特·M.薩拉蒙:《政策工具視角與新治理:結論與啟示》,引自其主編《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肖娜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526 頁。,是否已經獲得現實生活本身的必然確證,或者更具細節知識意味地在社區文化治理現場,有效消解諸如“盡管有關于怎樣評估非營利機構及其基本藝術活動的卓越文獻,但這一知識的主體部分,依然因對社區、公民及他們所作出努力進行測值缺乏理解張力以及隱存著的障礙而受到制約”②Kate Preston Keeney and Pam Korza:Assessing Arts-Based Social Chang Endeavors:Controversies and Complexities,in Max O.Stephenson,JR.and A.Scott Tate(ed): Arts and Community Change: Explor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Practices, and Dilemmas,Routledge,2015,New York,p.197.,也就是效果客觀性及這種客觀性的社會價值認同,始終是社區文化治理的肯定形式乃至價值尺度。
一
這一價值尺度通常會有兩種外在相似而實則內存分異的知識顯現方式,一種被處置為宣傳性(propaganda)的政策主張,另一種則體現為學理化(scholarism)的治理訴求,而在我們日常感知的絕大多數文本經驗事態中,人們雖未于表達和接受的意義發生鏈放棄后者的義項隱存,卻往往會在隱存的模糊狀態使得概念空心化或者命題真值率由此遞減。也就是說,至少在概念陳述的語用現場,所謂“滿意度“的知識工具分析已被宣傳辭令簡單化功能置換,并且因這種簡單功能置換而常常不經意間陷落于“被滿意度”,即成為相關層級文化行政官員抑或部分公共文化政策專家的“虛擬標桿”,而非社區文化治理后果的“實際效度”。
其中被簡單化或者模糊化的義差在于,學理界面的文化獲得感不僅具有主觀性價值存在特征,尤其表現為個體感受的主觀集合狀態,而且更是基于計量社會學測值研究或者精神分析社會學質性研究的行為后果合成產物。不僅包括社會動力學基于常量與變量時空條件的在地現場轉換,而且包括社會靜力學基于要素配置規則和要素配置方式的國家框架公平與效率一般標準全覆蓋。更何況在全球化碾壓與未來性誘引日益呈現其加速度態勢的今天,社區文化治理中的獲得感生成過程、方式及其結果形態變得更加復雜糾纏,而這顯然與宣傳口徑的文化獲得感語義差異甚遠,因為作為政策文本或者其它口號化非學理性亞學術文本,其模糊語義與虛擬標桿不過是某種文化存在意愿,或者被陳述為主觀臆想中這種意愿的或然狀態抑或必然狀態,且已經排除某些文本以追求社會利益名義謀求自身利益的動機不純可能性,盡管這種可能性至少在韋伯看來難以排除,因為在他看來“此種利害關懷構成了保持卡理斯瑪要素——在支配結構里,以即事化的形式存在的卡理斯瑪要素——的最強烈動機”①韋伯:《支配社會學》,康樂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329 頁。。
于是我們所面臨的知識事態,就是如何在社區邊際集合性主觀感受得以產生的客觀條件學理分析中,確立滿意度作為一種價值尺度在社區文化治理中的支配性功能地位,并因這種支配功能對現場治理行為的有效支撐而使宣傳性預設目標充分得以實現。作為感受產生條件與感受發生后果的主客觀存在性分析,一旦與它者化主觀虛擬融匯和統一,兩種知識處置方式間的隱存裂痕就能在事態現場實際得以彌合,而這也就意味著,只要我們對滿意度原則的學理分析于任意此存性問題焦點實現充分穿越,就一定能同步性地規避此議的當代知識域實際隱存著的種種紊亂和緊張,當然也就毋須擔心面對任何文化治理現場可能出現的所謂“作為暴力的解釋學……幻覺乃是充滿風險的”②James H.Olthuis:Otherwise than Violence:Toward a Hermeneutics of Connection,in Lambert Zuidervaart and Henry Luttikhuizen(ed): The Arts, Community and Cultural Democracy,Macmillan Press LTD,2000,London,p.139.。之所以要對此先行加以強調,是因為涉事各方誤以為滿意度命題具有精準確證過程可以省略的自明性知識構建,所以就粗放式地通過諸如問卷調查來獲取命題真值,甚至連這樣的簡單獲取也在權利任性的印象式“拍腦袋”中給予價值肯定。最為凸顯的代表性個案,當推農村社區的“農家書屋”,多少年來讓億萬農民在“被滿意度”極高的政績肯定判斷中,屈抑其滿意度極低乃至根本就不滿意的日常體驗,及其真實文化感受的正當表達權利和充分表達機會,進而也就在絕大多數體驗主體的失語態感受缺位狀態下,其他關聯者完全他者化地在給定性滿意度中得到較為充分的不同利益滿足,其結果是滿意度淪落為理論界面的偽命題與生存界面的虛擬呈現。
諸如此類的虛擬滿意度,顯然與社區文化治理價值本體的效度訴求極其相悖,尤其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本體革命新時代,更相悖于執政意志和執政理念孜孜以求的“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做到老百姓關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進什么,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①習近平:《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引自《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 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5 頁。,以及基于這種訴求確立唯一價值肯定形式的“我們黨的執政水平和執政成效都不是自己說了算,必須而且只能由人民來評判。人民是我們黨的工作的最高裁決者和最終評判者”②習近平:《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引自《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28 頁。。所以,如果要想從頂層制度設計環節開始便目的性地規避這些悖論,就必須存在論分析姿態地對現場關聯事態給予深層敞開,并且努力在敞開過程中,運用功能恰配的計量研究和質性研究知識工具,撬開諸多作為原因以及作為結果的社區居民文化滿意度生成要素、生成機理和生成方案,同時還要使所有這些知識行為,自覺定位于社會本體轉型后的社區生存背景系統化運作,否則就會因所議的時差性靶向錯位而喪失學理介入的準入合法性,從而只能在自言自語的言說興奮中自得其樂,與對象事態的知識解困抑或現實建構完全價值無涉。毫無疑問,涉事各方經歷了太多這樣的無涉,并且由此導致了社區文化治理現場那些作為當事人身份的社區居民大多數的失望與信任危機。
正因為如此,對社區文化治理滿意度原則進行存在論意義上的學理分析,或者說澄明滿意度原則在社區文化治理中作為價值尺度的基本地位,就成為此議的邏輯起點與命題向度。依此線性遞進,涉身者首先照面的學理議題,當然會是滿意度原則的命題所指,否則就極難做到“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而易于陷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這一古訓的現代邏輯隱存,其實就是命題真值率將會很低,甚至在極限情況下會低至零值抑或負值,于是本來具有理論和實踐價值的真命題,因語義清晰性缺失而成為語用過程中某種意義上的偽命題。社區文化治理中的滿意度原則,是指將滿意度作為治理效果的價值目標,而核心概念的關鍵詞“滿意度”,不僅可以從字面意義給予社區居民滿意程度的直觀把握,而且更應該深度揭蔽其所指的意義隱存。在此,我們不妨以雅克·拉康的“癥候說”角度切入議題,從三個方面澄明這一關鍵概念內在意義的外在表征,那就是集體心理反應、日常行為顯現、普遍表態狀況。也就是說,只有以質性研究抑或量化研究知識工具從這些方面獲取的認知后果,才能較為充分地體現特定社區文化治理的居民滿意度真實狀況,從而逆向追問,某種社區文化治理過程是否充分并且有效貫徹滿意度治理原則,所以是一個問題的兩個解釋向度。
二
集體心理反應必須通過精細而且深度的田野實驗作業,才能使特定邊際的居民群體積極反應或消極反應程度,在心理學系列知識工具功能支撐下被精準認知。心理反應包括集體顯意識與集體潛意識,或者精神分析學家基于形而上思辨追問的所謂“知覺現象學”之議,及其具議的所謂“既然現象場已充分地被界定,那么就讓我們進入這個模棱兩可的領域,讓我們和心理學家一起向這個領域跨出第一步,期待心理學家的自我批判能通過第二級反省把我們引向現象的現象,堅決地把現象場轉變成先驗場”①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商務印書館2001 年版,第95 頁。。兩者均可在具體社區及其居民群體生存聚集,并能通過反應強度、反應時長甚至反應方式的分析斟別,來獲得心理反應后果進而推演出與之相匹配的滿意度觀察成果。當心理反應研究從常量觀察系進入事態之際,他們更多從量化測值的精準研究入手,以求滿意度觀察能夠更加真實與準確,所以就可以知識操作如“布朗運動”這樣的實驗工具,并于某一意義維度甚或意義焦點,嵌位諸如“只要我們增加s/t商數里的分子s,或者減少分母t,都可以達到增加客觀的斷續速度v的目的。這是因為,通過s/t,v得到了界說……它不僅僅用速度的變化來對這些變化作出反應”②庫爾特·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學原理》,李維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第242 頁。,或者更具社會靶向地嵌位于那些“拓撲問題”“向量問題”“維度問題”“誘導域”以及“張力”等,從而在各種數學計量化的各種向量解困中,抵達“有可能確定這些區域的拓撲學。一個非現實性層面的拓撲結構有時類似于現實性層面。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尤其當現實性層面內的情境令個體十分討厭時,非現實性層面的結構一般不同于現實性層面的結構”③庫爾特·勒溫:《拓撲心理學原理》,竺培梁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199 頁。在此,似應參閱:“如果人們用β表示行為或任何類型的心理事件,用s表示包括個體的整個情況,那么β可以被看做s的函數: β=f(s)。在這個等式中,函數f,或更準確一點,它的一般形式就表示人們通常所稱的規律。如果人們以個案的特征常數取代這個公式中的變量,那么人們就可應用于具體情境”(同上第10 頁)。。在諸如此類的計量功能嵌位中,無論廣義“格式塔心理研究”還是引申義“拓撲心理研究”,無論針對“行為環境”還是針對“心理環境”,無論切入場的“整體”還是且入場的“組分”,凡此種種,都能在個體心理反應之上接續出集體心理反應,進而在常量變化的計算分析中求取可意義換算的反應值與反應差,而在社區文化治理現場,人們則可以從這些反應值與反應差中,換算出客觀性意義有效度和主觀性效果滿意度。
如果心理反應研究調節從變量觀察系出發,遭遇諸如心理場在社區文化治理過程中往往不可避免的諸如“分裂”“障礙”“逆反”“妄想”“癡迷”“狂熱”“抑郁”“從眾”和“焦慮”等變態心理傾向或心理場,則側重質性研究的“變態心理學” 就更加具有解困張力或分析效力。例如針對老年居民占比度高的社區,心理障礙的焦慮、抑郁、失眠、血管性癡呆乃至阿爾茲海默癥健忘等,選擇何種文化介入方式才能在參與性解困中達到心理緩釋的文化效果,就成為變態心理學嵌位社區文化治理的重大而且迫切的課題,反過來,當社會追問其文化治理效果的滿意度時,它又具有社會評價的質性方式通道功能與參照屬性,正因為如此,深度田野作業所獲取結果的諸如“意識到每一天都可能是他們最后的一段美好時光”④Teffrey S.Nevid、Spencer A.Rathus、Beverly Greene:《變態心理學:變化世界中的視角》(下冊),吉峰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728 頁。,就成為變態心理學有效獲取文化滿意度的關鍵癥候之一,唯此才能揭蔽集體變態心理反應。當然,我們也可以在知識操作層面將“精神分析方法”與“心理學方法”打捆到一起,協同解讀社區文化治理效果滿意度發生機理與作為癥候的集體心理反應,但問題是,在這樣的打捆工具協同作業中,必須時時注意甚至牢記兩者之間的知識邊界,否則就會在功能紊亂中,因喪失靶向定位與功能分異而導致無效作業的盲區或者歧途,因為精神分析方法的諸如弗洛伊德式觸點“癥候大都不依賴對象,因此與外界的現實失去接觸……因此,我們不容易在癥候中看出里比多的滿足,就不足為怪了,雖然我們常可證實這個滿足的存在”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1984 年版,第293 頁。,抑或梅洛-龐蒂與雅克·拉康糾纏化詭辯的“鏡像問題”與“凝視問題”,除了與如上所述的“變態心理學”每有多維疊合之外,其敘議重心則分離于作為實驗科學的普通心理學何止于一兩個知識譜系域區,后者更應納入思辨理論范式之中。也正是存在對象疊合與認知范式分異同步在場,才使得知識工具打捆分析的必要性與操作謹慎同樣不可低估,由此就會使得集體心理反應形而下生存分析結果能與形而上思辨結果形成知識合力,求證社區文化治理狀況及其對這種治理的實際感受,而且還可以延展至已然性感受、或然性感受乃至必然性感受,所以能在兼顧“常態”與“變態”的心理反應基礎上為社區文化治理者有效方案聚焦提供前置支撐。這種支撐無疑顯形為真實社會表征,并在“基耦”的觀念中,充分實現“這種基耦是指共同接受的知識或基本觀點,它是作為適應過程所指向目標的根源而存在的”①塞爾日·莫斯科維奇:《社會表征》,管健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176 頁。社區自驅力,驅動治理方案更迅速且更有效地轉化為積極治理成果。
至此我們就可以將所議的問題靶向,在集體心理效果形成機理分析知識性懸置之后,定位于集體心理反應的社會呈現形式,或者更精準化的生存場日常癥候,并且從直觀感受所能及的呈現形式抑或日常癥候中,判斷出基于集體心理反應維度的文化治理效果,由此推進其再決策進程。就這樣的判斷本身而言,決策者、實施者乃至研究者,甚至可以離開復雜糾纏的心理學知識分析工具,從如下兩種日常心理反應事態中,獲得我們意欲獲得的觀察結果,那就是:其一,從社區居民的“順應心態”中判斷特定文化治理行為有效與可持續。生存界面現象描述而非存在性分析的“順應心態”,是指特定社區文化治理過程中,人們對文化活動內容、文化活動方式、文化活動機會或者文化活動平臺所表現出來的可接受性集體意愿呈現形態,是諸多心理分析工具都可以功能性切入的集合心理完整心理事實,是適應、認同乃至趨隨的主體在場價值肯定態度,因而處在這樣的心態浸透與支配下,文化治理過程中治理主體與參與主體間意志疊合或意愿一致,就是順理成章的必然結果,而這種結果所現場發生的諸如“通過創建實踐機會與參與空間,在青年、有色人種和低收入家庭之間牽引聯系的紐帶”②Diane Grams:Achieving Success,in Diane Grams and Betty Farrell(ed): Entering Cultural Communities: Diversity and Change in the Nonprofit Arts,Rutgess University Press 2008,New Jersey,p.224.,就會更順理成章地嵌位于治理預期的諸如“為不同的鄰里之間的生存敞開與交往接觸提供機會”③Tom Borrup: The Creative Community Builder's Handbook: How to Transform Communities Using Local Assets, Art, and Culture,Fieldstone Alliance,2006,Saint Paul,p.75.。問題的關鍵在于,這種“順理成章”的線性事態邏輯,是社區文化治理現場所有場域事態得以發生的前置條件,而且是具有集體心理支撐功能的不可或缺條件。因為社區居民順應心態的存在程度,與社區公共文化生活效度與居民日常文化生活質量之間,構成正比例線性發生關系。其二,從社區居民的“逆反心態”中判斷特定文化治理行為無效與不可持續。生存界面現象描述而非存在性分析的“逆反心態”,是指特定文化治理過程中,社區文化活動與居民心理預期出現向量悖論,從而導致悖論結構中社區居民對現場文化事態的集體心理逆反,非意愿情緒由此使得絕大多數社區文化參與主體,表現出冷漠、厭倦、拒斥乃至價值無涉等一系列消極反應態度,即使被迫參與也只不過是沒有任何文化心理支撐的“被動形式”,并且這樣的“被動形式”存在越多,失去社區文化信任的逆反心態就積累得更多并功能拒斥得更強烈,最終導致場域失效或者去意義化的事與愿違后果。我們當然可以選擇“送文化”抑或“種文化”的不同文化模式,甚至也可以先行給予功能預設抑或價值預設,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如果正面遭遇社區居民的逆反心態,則任何一種文化發生模式或者任何理想化的預設行為,都將在對象去存與合作失敗中演繹為失靈、失效抑或失真的事態假象,而這樣的假象事態不可能具有行為可持續性。至于逆反心態的產生與加劇,盡管內在結構有其十分復雜的因果糾纏,但文化治理行為失真與居民意愿位格失重,顯然是較為凸顯的兩大影響因子。究其要,不僅文化治理行為失真悖離于日常生存質量訴求的諸如“就觀念層面而言,個體和社區同樣希望良性生存,意欲使其社區體系改造成為這些體系的最佳可能迭代狀態”①Craig Talmage and Richard C.Knopf:Rethinking Diversity,Inclusion,and Inclusiveness:The Quest to Better Understand Indicators of Community Enrichment and Well-being,in Patsy Kraeger,Scott Cloutier and Craig Talmage (eds): New Dimensions in Community Wellbeing,Springer,2017,Cham,p.8.,而且居民意愿位格失重后的參與主體性缺失,將會形成強度不同的反向沖擊力,抵抗介入性文化治理動機的諸如“設定目標……這些目標具有全方位可持續,而且具有社區及其項目的價值”②Tom Borrup: The Creative Community Builder’s Handbook: How to Transform Communities Using Local Assets, Arts, and Culture,Fieldstone Alliance,2006,Saint Paul,p.197.。正因為如此,良性社區文化治理行為,就必然發生于非逆反心態社區文化生存現場,而這也就意味著治理主體任何時候都必須清晰把握現場事態與社區居民心態,并基于這種把握努力尋求真實與適應的行為自律,否則就只有介入與抵抗直接遭遇后的零和甚至負向量后果。
三
日常行為顯現雖然或多或少與集體心理反應有內在聯系,但在生存論維度具有此在遞進意義,因為它是我們審視事態之際更為直接可感受的外部世界狀況,之所以將其處置為此議的遞進義項,是因為愈是“直接可感受”,愈是容易成為人們視而不見的知識盲區,至少對絕對多數的中國語境參與社區文化治理的類型學者與層級文化行政官員來說,這樣的認知盲區不僅帶有普遍性,而且還應將其視為文化形式主義導致社區文化生活減值的重要原由,由此也就使得深度關聯討論變得十分必要。
從純粹學理的角度審視知識背景,遞進義項的此在處置方式有其先在經驗,典型個案如20 世紀法國學者梅洛-龐蒂,在他反思“行為”及其結構就是基于癥候式心理分析且推進到不止于這種分析來完成其“結構”組裝的,由此而有歸納性的“如果這些評述是有根據的,就一定可能而且必須不再像我們通常所做的那樣,把行為分類為簡單的和復雜的行為,而是根據這些行為的結構是被淹沒在內容中,還是相反地為了最終成為活動的特有主體而從內容中涌現來進行分類”③莫里斯·梅洛-龐蒂:《行為的結構》,楊大春等譯,商務印書館2010 年版,第158 頁。。在進一步具議其“混沌形式”(forme syncrelique)、“可變動形式”(forme amovible)和“象征形式”(forme symbolique)之后,建構出具有知識延伸價值的結論:“行為不是一個事物,但它更不是一個觀念,它并不是某一純粹意識的外殼。作為對某種行為的見證,我并不就是一種純粹意識。這正是我們說行為是一種形式時所要表達的東西”④莫里斯·梅洛-龐蒂:《行為的結構》,楊大春等譯,商務印書館2010 年版,第195 頁。。
不過這樣的先在經驗,僅僅局限于心理學與精神分析理論倏然崛起之后,而在更加廓大的知識背景上,無論此前還是此后,行為研究的知識譜系都在諸多知識域廣為延伸,并且是在懸置心理發生前置事態的知識運作過程中,直接截取“人的行為”作為問題切入與命題建構的邏輯起點,由此尋求不同生存場域或者存在界面的各種知識解困方案,甚至不乏形而上學意義的本體價值追問。最容易受到關注的是法學,因為法律理論、立法規約與司法實踐等,都無不以“行為”作為對象實在、判斷依據以及追訴標桿,否則也就沒有客觀性以及價值訴求的公正性可言,由此不僅可以更容易自明于《民法典》的諸如“因故意或過失的違法的行為或不作為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人,應承擔賠償責任”①引自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權行為法》,齊曉琨譯,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3 頁。,而且可以深度理解何以在《摩奴法典》的古代印度,就將國王和武士的權利合法性規約于“種姓的行為”②《摩奴法典》,馬香雪轉譯,商務印書館1982 年版,第135 頁。,這就是古今中外都將“犯罪”定位于“犯罪行為”實際實施的存在論邏輯,因為只有特定行為真實存在,才可延推至諸如“動機”和“后果”等關聯性實在,“行為”在法學理論與司法實踐中的核心地位當然也就不言而喻。與此不同,行為關注對社會學知識域而言乃是極為滯后的知識事態,當然這種局面首先是由社會學作為學科知識域邊際清晰同樣很遲的根本制約,從韋伯將“行為的責任歸屬、代理關系”③馬克斯·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72 頁。擬定為社會學的基本議題,到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將具體行為作為交往顯示性與有效性與否的杠桿條件,從而使其問題指向轉移至“反抗是針對抽象的,即迫使生活世界接受的抽象,就是說,它們必須在生活世界之內加以研究,雖然它們進入了感性上集中,空間上、社會上和時間上遠遠區別的生活世界的復合性界限”④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第二卷),洪佩郁等譯,重慶出版社1994 年版,第504 頁。,再到那些組織社會學家將“行為”納入“系統”進行組織分析,例如在“行動系統不是自然既定之物,而是偶然構建的存在”⑤米歇爾·克羅齊耶、埃哈爾·費埃德伯格:《行動者與系統——集體行動的政治學》,張月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270 頁。的命題建構中闡證社會組織過程,皆無不著力于行為在社會構成中的驅動力地位及其功能復雜性給予知識澄明,而且是愈來愈細節化、深層化乃至清晰化的澄明,總之表現為社會行為制約社會生成并維系社會存在的全方位知識進展事態。如果以這種態勢作為參照物,就不難發現,對更多的社會科學知識域而言,行為的關鍵詞地位與行為研究的建構性知識凸顯,幾乎成為帶有普遍性的延展與拓值議題,而這也就給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及其更加具議的社區文化治理研究,形成勢不可擋的倒逼力量,迫使我們不得不從文化的日常行為顯現視角,去深化諸多公共文化問題研究和社區文化治理研究,否則我們就會始終滯陷于盲動狀態和淺表層面,其結果必然是理論與實踐的雙重一籌莫展。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專家及其對策處置的層級文化行政官員,現場聚焦于社區文化治理的“日常行為顯現”,無論認知維度還是實證維度,都不過是從“心理捕捉物”向“行為捕捉物”的方法轉換,而其轉換本身,決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結構抑或舍此取彼的置換過程。既然是一個方法轉換事件,那么很顯然,此前捕捉集體心理反應時所集中使用的一系列量化測值心理學知識工具或精神分析工具,就會較大程度上被捕捉日常行為顯現的各種質性研究知識工具替代,盡管這些替代并不具有全稱覆蓋意義,但在方法論意義上卻無疑是大概率知識工具替代事件。之所以只能是“大概率”而非“全稱覆蓋”,是因為一方面處在“數據時代”背景下,包括社區日常生活在內的整體社會行為,常常會在界面定位精準基礎上獲取普遍行為的數據呈現方式、分析方式和處置方式,由此使得計算社會學的諸如“生態瞬時評估法”,及其所謂“生態瞬時評估法主要有4 個特征:(1)在現實環境中搜集數據;(2)評估的是個體當前或最近的狀態或行為;(3)評估可能是基于事件的或隨機引發的(取決于研究問題);(4)隨著時間的推移需進行多次評估”⑥馬修·薩爾加尼克:《計算社會學:數據時代的社會研究》,趙紅梅等譯,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版,第104 頁。,具有不可替代的精準性訴求與規模化訴求,而另一方面,差異化社區的文化行為豐富性與同質化社區的文化行為多樣性,或者會以穩定結構抑或秩序化狀態的“社會表征”形態顯現,亦即連續行為的社會表征,一定程度上“將對象、個人和我們所經歷的時間習俗化。它們給予這些事件一個明確的格式,并將這些事件定位于一個既定的種類中,并逐漸建立起一套屬于它們的固定類型的模式,且將該模式在所屬群體中與大家分享”①塞爾日·莫斯科維奇:《社會表征》,管健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24 頁。,又或者會以非穩結構抑或非秩序化狀態的“功能后果”與“意外后果”互滲形態出現,亦即邊際群體行為的“功能—意外”后果,總體而言可以動態性地存身于遞進解釋的所謂“功能主義學者的工作在社會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恰恰是因為它促使我們關注到,在行動者有意為之的事情和他們所作所為實際導致的結果之間,的確是存在差距的”②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李康等譯,三聯書店1998 年版,第426 頁。,總之是任何計量知識工具所無法統轄的社區文化行為現場事態。基于此,一個不爭的對象事實直接知識訴求就是,要想后續精準施策成為現實,還必須較大程度上依賴于質性研究方法及其工具功能匹配,從而能最大限度地“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③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12 頁。進而在此議之際,問題的遞進延伸就在于,我們以何種質性研究姿態,委身于社區文化治理現象,通過對居民文化行為的歸納性深度把握中獲取文化治理意欲獲取的對象行為事實,或者換句話說,行為歸納的重要現場究竟何在? 在我看來,至少如下方面我們必須面對,那就是主動行為狀態呈現、被動行為狀態呈現、觸動行為狀態呈現。當然肯定會有其它義項的狀態呈現,而且更會有其它行為狀態精準把握的切入點或切入方式,但此議的必要性在于,它使日常行為呈現得以成為社區文化治理的遞進事實與增持標桿。
任意具在社區的文化活動行為,無論個體還是集體,置頂位格無疑是主動行為的狀態呈現,即社區居民作為文化行為者,此時具有自發抑或自覺的文化自組織身份,進而其行為也就一定具有文化主體性或者文化主體間性。田野事態呈現的諸如“我尤其想要討論兩部落印第安人,因為曾參加過他們組織的部分節慶聚集活動。在存世的局部,單個的人很少會進行一對一的對話。我發現,作為圣誕節化裝群體的領頭人,當他致力于從事自封的活動者時,即使相距較遠的其他人也停止私下談話。所有的人都想說,他看到稱之為領頭人的那個人,是如何在化裝活動中訓練年輕的表演者展示他們自己,是如何安排樂師,以及是如何進行種種維度享受快樂的組織活動”④Roger D.Abrahams: Everyday Life: A Poetics of Vernacular Practices,University of Pennisylvania Press,2005,Philadephia,p.153.,至少個案性地表明,不僅節慶儀俗活動“狂歡化”或者“沉浸化”是自發熱情與自覺理性內驅使然,而且這種內驅動力直接打臉組織社會學家們篤信的所謂“人們幾乎不會僅僅只是為了玩樂而從事集體活動、集體行動始終相當于一種反抗自然的聯合行動,這一聯合由面對諸種實際問題的人們構成,這些人如若彼此之間不進行合作,就無法解決自己面對的問題”⑤埃哈爾·費埃德伯格:《權力與規則:組織行動的動力》,張月等譯,格致出版社2008 年版,第287 頁。,甚至還現場建構20 世紀以來焦慮尤甚的場域權利關系,諸如福柯“生命政治”所面對的那種“治安科學”及其所謂“太多的地方沒有掌控和監督;沒有充分的秩序和管理。總之,管得太少”⑥米歇爾·福柯:《生命政治的誕生》,汪民安譯,引自汪民安主編《福柯文選》(11),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238 頁。,抑或別爾嘉耶夫“個體人格”所遭遇的“這樣的社會即‘我們’的客體化。它已不具有任何真實性和任何生存意義,而‘我’與‘我們’和‘我’與‘你’的關系也嬗變為外在的關系”⑦尼古拉·別爾素耶夫:《人的奴役與自由——人格主義哲學的體認》,徐黎明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85 頁。,總之是程度不同地解構掉社區自治境遇中,一切有可能形成文化權力支配關系之際個體主體性消亡的垂直生存結構和“中心—邊緣”生活方式。即使只有所述三個功能義項,實際上我們也完全有把握地獲得文化活動效度組織行為或自組織行為的肯定性結論,那就是社區居民文化活動只要呈現為主動行為,呈現為個體主體性隱在支撐其行為進程的“沉浸”“忘我”乃至“狂歡化”,就一定存在效度在場化與可持續性。傳統節慶、習俗儀典、時尚聚集、廣場活動等社區文化行為,之所以能在自發行為過程中不期然而至活躍、群歡甚或沸點狀態,無論主客觀因素是多是少,最核心的影響所在,都必推個體文化權利的充分實現以及作為其邏輯前提的主體性身份抑或主體間性價值肯定,由此而有社區文化活動的主動行為狀態。所以,只要呈現為這樣的狀態,則與之關聯的文化活動效度及其更進一步的社區文化生存質量,就一定能順理成章地嵌位于社區文化治理預設價值標桿。
問題在于,雖然如上所述乃是社區文化治理的理想存在方式,但就更多的現實狀況而言,往往能見到的卻是這種存在方式的異化形態,或者說否定性現場后果,也就是被動行為狀態呈現。社區文化活動中被動行為的田野癥候,可以歸納陳述為理論命題的“在場缺席”,即所謂在場者只是空間意義上的“在此”,而非存在意義上的“此在”,也就是在此的在場者并未真實參與文化活動的場域建構和交往分享,所以最終淪落為場域文化活動的缺席者。這種理論陳述方案的“在場缺席”,可以個案化還原為某個具在而且日常的通俗樣式,仿佛市級公共文化示范區內特定社區的居民,按照文化行政末梢的組織意志,從事一場場面熱鬧的讀書交流活動或者書畫展示活動,在迎接更高層級文化行政官員視察或驗收之際,不知其然從而更不知其所以然地屈身于事態和現場,進而也就以假性參與來對沖“權力他者”強制給定的“被迫”和“無奈”,所以就會出現個體居民一方面參加了該次文化活動,而另一方面他并沒有真實參加這樣的行為悖論。①2019 年12 月26 日,筆者在安徽馬鞍山(國家級公共文化服務示范區)市作了一次田野調查,3 小時內在該市城區10 個點位隨機問詢陌生市民,均不知所在城市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示范市,且尤為令人驚愕之處,市圖書館借閱處3 位工作人員在隨后的問詢中亦同樣不知,但該館展覽廳有大量示范文化活動現場,尤以層級文化行動官員活動參與存照居多。導致“假性參與”置換“真實參與”的負能量源,一是社區文化治理頂層設計的權力傲慢,二是文化體制末梢消極響應中的政績利益驅使,三是居民自組織本身因博弈方差所導致的亞卡里斯馬強勢。這些負能量源雖然維度有異,但屬性相同,皆可歸屬于社區文化治理過程中異化滋生的“任性他者”,而“任性他者”與“一般他者”的意義分異不過在于,彼此存在對誰是社區文化活動主體的認知和定位不同,由此也就決定其在社區文化治理過程中自身角色定位的天壤之別。處此可選擇情勢之下,一旦其中任意一種他者力量充當了社區文化治理的支配力量而非助推力量,其直接后果就是社區居民在社區文化治理中的對象化,對象化演繹非主體性,非主體性決定參與者被動行為狀態。沒有主體性或主體間性的被動文化行為,不僅無緣于文化活動可持續驅動的所謂“作為行動組織化普遍特征的合作累積……通過他者提供的轉換資源再利用來建構新的行為”②Charles Goodwin: Co-operative A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New York,p.23.,而且更容易導致他者權力支配的文化活動與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分離,這種分離使人們完全無法通過這樣的文化行為來充分實現“時間連續體取決于我們日常生活的連續性”③漢娜·阿倫特:《精神生活思維》,姜志輝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229 頁。,當然也就無法日常化地于所在文化活動現場,最大限度地致力于日常價值生存訴求的“自己的時間自己做主”④Peter Jones: How to Do Everything and Be Happy: Your Step-by-step, Staight-talking Guide to Creating Happiness in Your Life,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11,London,p.35.。正因為如此,介入社區文化治理的任何他者身份,無論其助推力強至何種程度,都不能與社區居民構成支配結構,否則就必然會在功能轉換與身份異化中迫使入場居民以及文化參與行為呈現出組織失效的被動行為狀態,而這也就逆向提示我們,只要明顯測度到類似的狀態呈現,也就意味著介入治理的任何先驗意志抑或行政預設皆已失靈,從而能在組織方式糾偏中重擬社區文化治理行動方案,并且以驅除被動文化行為作為新方案的邏輯起點。
由于主動狀態與被動狀態就社區文化行為方式而言,無疑具有定位指涉的極化意義,而現場事態常常表現為兩種極化方式的博弈、互滲、兼容乃至間隙時間轉換與異地空間轉換,所以也就存在過程性迭合的行為存在方式,那就是過去未曾引起足夠重視的觸動行為狀態。觸動行為不是合力驅動的結果,也不是對連續行為的一般陳述,而是所在時空當下性而且瞬間性的行為狀態,是他者作為外在力量于此在的有效驅動發力過程中,因受力方某一觸點被擊中而激發出二次元行為效應。在社區文化治理現場,由這種二次元效應所聯動、衍生和繼發的社區居民集合文化行為,都無不可以統轄于觸動文化行為,其現場事態呈現有如“沃爾克藝術中心”(Walker Art Center)社區推進的“青少年項目”(Teen Programs),在“調動和支持年輕人與當代藝術和我們所在時代藝術家的關系建構與互動影響”①Betty Farrell:Building Youth Participation,in Diane Grams and Betty Farrell(ed): Entering Cultural Communities: Diversity and Change in the Nonprofit Arts,Rutgess University Press,2008,New Brunswick,p.120.過程中,激發基于青少年代際傾向的社區文化活動,而激發后果本身,則無疑是觸點因外力作用所產生的觸動效應。問題在于,瞬時性或者即事化的社區文化行為,由此就完成了他者力量驅動向自我力量實現的轉化,這一轉化本身,導致衍生態自組織社區文化活動中的居民個體,不僅得以完成主體性身份構建,而且能夠最大限度地展現其文化參與過程中的主動姿態,甚至還能產生不可預期的社區文化創新能力,所以整個觸動鏈市反應過程,簡而言之就是反客為主的行為激活積極后果生成史。但值得涉事各方關注的是,觸動鏈式反應過程并非一勞永逸的動力事件,而是互動博弈的交互發生動力機制,當自組織行為衰變或文化主動性減值出現明顯癥候之后,機制本身就會呼喚新的外力形式作用于新的觸點位置,并激發出新的二次元行為效應,由此而致社區文化自治勃勃生機局面得以不斷延展。這一事態描述,其所能夠提示頂層文化設計抑或末梢文化賦能的是,就社區文化治理的觸動行為機制而言,在積極介入過程中務必做到角色自律,切切不可以一種“包打天下”姿態去全能負責乃至完全規置社區文化活動現場,或者以預設“標準化”或行政“規范性”置換社區文化的自組織方式與自建構能力,恰恰相反,更應該不斷審視社區文化現場的觸動行為呈現狀態,并在精準審視中有效確立對觸點的捕獲方案及作用方式,從而確保不同社區產生其非間斷性自恰鏈式反應,進而最終實現社區文化治理事半功倍的良性后果。
毫無疑問,對如上三種日常行為顯現形態的具體分析,雖然未必能做到學理全覆蓋,但能從有限的發生機理澄明中,使我們較為清晰甚至較為充分地定位社區文化活動的日常行為方式和行為功能結構,并獲得我們對居民文化參與“滿意度”的穩定觀察系或者測值標桿。由這一穩定觀察系或測值標桿所捕捉的“滿意度”質性后果,較大程度上可以確保其真實性而非虛擬性。
四
普遍表態狀況當然是對社區治理“滿意度”的最直接肯定形式與最可靠價值定位點,其所強調的是區別于心理反應和行為顯現作為治理主體間接效度測值路線的直接效度評價。在所議的問題軌跡上,這種對表態狀況的審視無疑是繼心理反應和行為顯現之后的邏輯遞進,其由內而外抑或由間接到直接的遞進設問,是滿意度原則真相揭蔽繞不過去的必然遭遇,因為直接表態及其所呈現狀態,能夠在最返璞歸真的語境之中獲得完整、真實而且有效的社區文化治理需求清單與績效答案。這種直接效度評價既適用于主動性文化參與,亦適用于被動性抑或觸動性文化參與,并且因其活動參與和效度評價的雙重身份疊合特殊性,可以較大程度上規避那些間接效度測值路線所容易帶來的“不確定性”或者“誤差”。
無論主動表態還是被動表態,或者無論就需求表態還是就效果表態,抑或無論批評性表態還是建設性表態,如此等等,無不是社區文化治理過程中直接民主的實現形式,是文化民主在社區文化治理中的充分價值實現路徑。從摩洛哥圓桌會議開始,世界各國就在社區文化生活的“公共價值”目標上漸趨共識,或者說顯示出共識曲線持續抬升的遞進過程,因而使得“參與”“參與度”“參與率”等概念日益成為所議語境系列關鍵詞。這些關鍵詞的核心價值指向,就是文化民主價值在日常生活現場的豐富性體現、多樣性體現和普惠性體現,所議也就要求“治理實踐理應目標定位于公共價值提升”①Dave O'Brien: Cultural Policy: Management, Value and Modernity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Routledge,2014,London,p.119.,而這種定位本身,雖然看似簡單直接,實際過程中卻極為復雜糾纏,所議公共文化政策專家才會由此議其“實際上,處于完全不同的抽象層級,關于‘治理、去治理和再治理’的常見公眾爭議,使得社會和文化治理理論乃是顯而易見地在不同的非確定界面起作用”②Jim MacGuigan: Rethinking Cultural Policy,Open University Press,2004,Berkshire,p.17.。所以無論如何,文化民主促進社區文化參與已然成為合法化命題,而“表態”也就成為“促進”事態進展狀況的重要確證方式,并且這一方式還直接與文化治理效果的“滿意度”之間構成可換算關系。
之所以特別標示“普遍表態”,是因為在基層自治和社區文化民主條件下,存在著質性研究意義上的三種“表態”方式,即表態的最大公約數、相對少數以及另類化個別,或可分述為“普遍表態”“部分表態”以及“極個別表態”,彼此有其對等的指涉意義。一般價值目標的社區文化民主,盡管致力于最大限度的居民普遍表態,卻并不排斥部分表態和極個別表態,甚至會在民主程序確保不同表態方式存在合法性的同時,為不同表態結果預留充分的權利實現空間,由此而使表態維度的社區文化民主不致陷落勒龐們鄙視和貶損的“烏合之眾”或“群氓暴力”之類的社會泥沼。但在具體操作環節,盡管社區文化治理涉事各方在“滿意度”功能植入與價值捕獲過程中,會從不同的角度并以不同的方法體現其對“相對少數”或者“另類化個別”的取向尊重與權利保障,但在日常運作機制中占據文化支配性地位的,卻必然會是最大公約數。也就是說,對文化參與效度滿意與否的現場反饋動力,一定取決于普遍表態后果的滿意度存在水準,而這顯然就是社區居民文化參與的最大公約數評價形式和效度測準方式。此議的線性延伸還在于,效度測準方式只能存在于對象常量,而對象變量呈現給我們的,更多情況下只能是效度測不準原理所揭示的模糊事態。③參閱:“不確定原理說ΔpxΔx≥h/4π,這里h是個常量,稱為普朗克常數,而π=3.14159 ……是我們熟知的圓周率,即圓周長和直徑的比率……量Δx不僅僅是測量的不確定度;粒子位置的不確定性是不可消除的”。斯蒂文·斯科特·古布澤:《弦理論》,季燕江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16 頁。測不準原理雖然屬于20 世紀自然科學領域的前沿成果,然而其知識解困方案完全可以移位至社會科學領域,并在功能轉換過程中持續施以援手,而這也就為我們進入社區文化治理現場找到了新的問題切入點及其學理切入方式,因為幾乎在任何表態現場,相對于滿意度測準常量與測準顯性而言,測不準變量與測不準隱形事態對目標捕獲更具遮蔽力量,更容易導致負面后果的效度值非精準性、非穩定性乃至非真實性。至此我們就可以清晰地意識到,如果不能按照測不準原理的知識邏輯進行有效解困,則實踐界面的“假性滿意度”及其由此推進的社區文化治理前置方案與后置進程,必然會在所有“假性”負能量釋放后演繹為無效治理或者社區居民逆反心態強勢反彈。
“假性滿意度”當然極大可能是權力意志或直接或間接的消極被動后果,但此議將其處置為自明性事實,且作為這樣的知識處置,那些事態涉身者甚或窺望者也都經驗過或多或少的社會親證,所以也就沒有必要在自明面前給予更多的真相揭蔽。這樣的議題懸置之后,本來處在細節事實存在位置的問題附著就會價值凸顯,那些基于技術理性分析所能觀察到的滿意度獲取過程與獲取方式,就在公共文化政策專家的關聯研究諸多環節,因科學信念缺位抑或技術規范不足而顯示出表態真值極端衰減的普遍態勢,而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當下的入場專家仍然在野蠻化的無理由自信中漠視所有的表態真值極端衰減。僅就習以為見的問卷調查效度取樣方式為例,至少有如下三種漠視會導致“假性滿意度”的必然后果。漠視之一在于,效度取樣者單向度給定問詢義項,導致表態者意欲表態與限定表態之間關系緊張,當這種緊張程度不同地對沖掉受訪者的真實表態沖動之后,就會以應付姿態隨意對問詢義項勾畫,極端個案甚至出現表態惡作劇,因其如此,由此取樣推證出的諸如“對移民社區而言,圖書館始終是一種資源,當慈善家安卓·卡耐基投入巨額資金滿世界建立起2500 個社區圖書館,尤其對移民群體而言,自我教育培養及所有居民進步推進就在這一行動中獲得了圖書館價值肯定……社會圖書館的貢獻乃是‘作為大學功能的圖書館’”①Michelle Filkins and August John Hoffman:Evolving and Essential Organizations that Facilitate Stewardship within the Community:Community Schools and Liberaries,in August Joln Hoffman(ed): Creating a Transformational Community: The Fundamentals of Stewardship Activities,LeXington Books,2017,Lanham,p.98.,顯然只能是自擬自證的自圓其說表態后果陳述。漠視之二在于,效度取樣者隨意性抽樣縮水,發放幾百份甚至更少的問卷來置換全稱覆蓋的居民普遍表態,并由這種隨意縮水置換的義項問詢統計結果生成其非普約性“最大公約數”。這實際上也就意味著,并非在方法論維度拒斥諸如“多樣化時長案例設計對發展軌跡調查以揭示一系列特定數量集群”②Derk Hyra and Jacob S.Rugh:The US Great Recession:Exploring its Association with Black Neighborhood Rise,Decline and Recovery,in Ronald Van Kempen,Gideon Bolt and Maerten Van Ham(ed): Neighborhood Decline,Routledge,2018,New York,p.50.的操作合法性,取樣設計本身或許并無設計缺陷,但問題是只要取樣覆蓋面不能涵蓋整個社區,達不到普遍表態的取樣訴求,哪怕群隨機選擇技術達標底線的所謂“樣本中幾個元素的樣本均值典型地用來估計總體均值,即”③L.Kish:《抽樣調查》,倪佳勛等譯,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 年版,第166 頁。,那么作為問卷對象的群隨機選擇就不可能有任何客觀有效的表態指涉意義真實性,而我們現在的表態問卷大多處在指涉意義真實性的底線之下。當然,我們所處的大數據時代完全可以規避這樣的隨意漠視,因為技術型公共文化政策專家們能夠毫無障礙地操作其“運用計算化和可視化技術全稱實現巨量文化數據集成與流量來確定文化解析學”④Lev Manovich:Cultural Analytics,Social Computing and Digital Humanities,in Mirko Tobias Sc?hper B Karin Van Es(ed): The Datafied Society: Studying Culture through Data,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7,Amsterdam,p.55.,由此獲取普遍表態及其某種表態的最大公約數,幾乎就是信手拈來的知識處置方式,只可惜我們的現場事態還沒有社會同步跟進地走到這一本該很容易到達的技術應用位置。漠視之三在于,效度取樣者處于自身傾向性目的或者受訪者處于非責任主體位置,或惡意或善意或隨意對待問卷或者問詢結果,由此導致社區居民文化表態的非真實性、非精準性乃至非意愿性,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社會統計倫理缺位背景下不期而至的被動后果。在大數據時代,如果我們在社區文化治理現場全面引入大數據知識工具,并且以智能化知識工具來處置社區居民文化表態的數據化實現形態,就勢必會前所未有地涉及數據倫理問題,因為數據真實性與精確性直接涉及它們能否有效指涉“對問題關切的問詢、對公眾關于民主的意見聚焦、對其公共生活及其他政策關聯事務的滿意度評價”①Julia Bauder: The Reference Guide to Data Sources,ALA,2014,Chicago,p.136.。因其“被設定為具有意義關聯性并且能夠客觀地給予意義測值”②Christine L.Borgman: Big Data, Little Data, No Data: Scholarship in the Networked World,The MIT Press,2015,Massachasetts,p.248.,所以不僅沒有任何道德綁架的意味,而且切實關乎這些問詢數據及其關聯意義指證是否合乎道德訴求,否則由此產生的治理決策和實際治理行動就極有可能影響到效度或者滿意度,當然也就必然會殃及社區居民的公共文化生活質量。
正因為如此,如何盡可能規避假性表態而從真實表態中最大限度捕獲真實滿意度,就成為滿意度原則在社區文化治理進程中能否真正實現的關鍵所在。當然這種真實滿意度取決于普遍表態狀況,因為這種普遍表態狀況將能充分體現社區文化治理的正負效度標示,并且這種對象性客觀標示往往以最大公約數作為其存在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