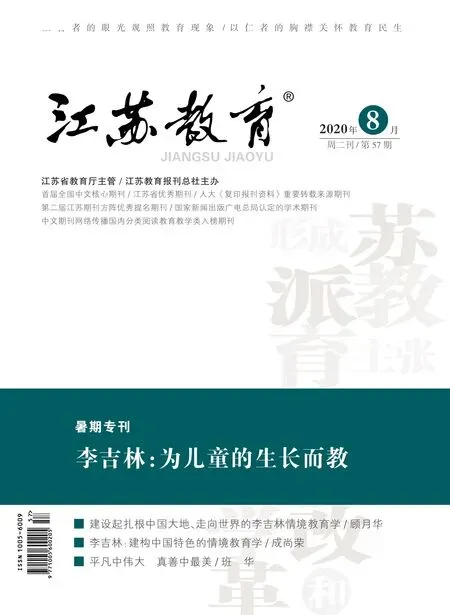我的小學老師李吉林
馬知路
(作者單位:中國民主促進會南通市委員會)
遇見李吉林老師,是在1978年,那時的她已經(jīng)是南通小語界知名的五朵金花之一。為了深入探索和提升已經(jīng)初具雛形的“情境教學”方法,李老師在通師二附領導的支持下開設了一個實驗班,而我,幸運地成為其中一員。那時的李吉林老師,梳著齊耳短發(fā),穿著整潔而略時尚的衣服,聲音脆落并且堅定,一雙大得出奇的鳳眼,只要輕輕從我們面前掃過,天然就生出了強大而溫暖的氣場,讓當年的我和其他“蘿卜頭”們生出親近和傾訴的欲望。
因為是實驗班,五年里我們上過數(shù)不清的公開課。教室后面坐著上百名表情肅穆的聽課老師時,做學生的總會有些緊張和不安。此時,李老師便會用她的大眼睛從左至右掃視一圈,微笑著撩一下耳際的發(fā)絲,然后筆直地坐在風琴邊,彈奏上一小段輕快的樂曲,我們的心緒便很快就安定下來了。此時,李老師會回到講臺,略傾著身子,抬起右手的食指,用略微誘惑的聲音問道:“同學們猜一猜,我們今天講的是誰的故事?”這個問題并不需要回答,她纖指一按,錄音機里便會流淌出一段朗誦,同時,她會在黑板上手繪出一幅粉筆畫。課堂上的李老師會用充滿磁性的聲音講述有趣的故事,引導我們想象古人的風采,啟發(fā)我們提出心中的疑問,在親切而且交融的氛圍里,一些靈感總會突然而至,并讓我們急切地生出分享的欲望。李老師并不總是站在講臺上,她會沿著課桌的間隔穿梭在“小兵”中間,隨時拋出幾個問題,瞬時,許多只手臂會齊齊高舉,期待著被點將的榮譽,一些性躁的甚至會把屁股挪離板凳,半躬著腰,把胳膊舉過頭頂,口中急促地高喊“老師”。公開課上的問題從未被事先準備,因而回答也是不可預測、千奇百怪的。但對爭搶著發(fā)言的學生,無關對錯,李老師一律給予鼓勵、贊賞的目光獎勵,碰到特別優(yōu)秀的回答,她會不由自主地興奮和激動,毫不吝嗇地高聲贊揚:“好!很好!太好了!”一個冬天,聽課的老師不知出于什么緣故摘下了我頭頂上的瓜皮小帽,而我沉浸在課堂的氛圍中,一整節(jié)課里凈忙著聽講和搶答,居然完全沒發(fā)現(xiàn),一次也沒回頭。不經(jīng)意間,這事在老師和同學中間被傳笑了很久……
李老師天生對幼小的生命充滿憐憫。她家院子里長著各類不知名的花草,這些植物很少被修剪施肥,卻總是生機勃勃地生長。數(shù)只鴨子和雞常年在院子里滿地亂跑,一只小貓陪伴了她很多年,還有幾只烏龜也總是懶懶地趴在某個角落。小東西們不只是李老師的寵物,也是我們的寶貝,幾乎每一天放學后,都會有三五個小鬼屁顛顛地跟著李老師回家,只是為了逗一逗那些小家伙。老師家的小動物是我們觀察日記里的常客,它們見慣了世面,從不知道懼怕,相反很有些明星的派頭。每每大家圍著它們指手畫腳時,它們總是用些許輕蔑的眼神回應,懶散散地昂首而過;可一旦看到有人掏出零食,它們的態(tài)度便會180°大轉(zhuǎn)彎,爭先恐后的景象總是讓老師和我們一齊哈哈大笑。
五年里,每個學生的喜怒哀樂都時時讓李老師牽掛著,每個學生的家她都走訪過多遍。一位同學的母親生了重病,那同學終日不樂,老師就在語文課上開展了一次“說說心里話,幫幫小伙伴”的捐助活動,讓全班和他共渡難關。后來那位母親走了,同學在很長時間里都有些沉默和自卑。剛巧國家號召大家捐獻蓖麻籽,那位同學在院子里栽種了一棵蓖麻樹,李老師就帶著全班同學去他家現(xiàn)場教學,讓他介紹怎么種樹、怎么養(yǎng)護、怎么收籽,最后還讓他準備了四十多個小紙包,把一包包蓖麻籽送到大家手上,讓我們捐獻。這次活動最終幫助他打開了心結(jié),也讓同學們和他的關系變得更加親密。
四年級時,學校要開運動會,李老師忽然讓我這個體育委員匯總每位同學的鞋子尺碼。過了兩天,每個人的課桌里就多了一雙嶄新的白球鞋。在那時,白球鞋幾乎還是奢侈品。當我們齊刷刷亮著白色的鞋幫在運動會開幕式上邁步時,直接就收獲了無數(shù)師生眼中的羨慕妒忌恨。長大后我們才知道,買鞋的錢居然來自稿費,是李老師從我們的習作里精心挑選,擇出每個人的一篇優(yōu)作,配上插圖,編輯出版了一本新書——《小學生觀察日記》(下文簡稱《日記》)。出版社給的稿酬穿在了我們腳上,《日記》也成為記錄著我們成長的線索。多年后同學聚會時,談起球鞋,談起《日記》,總會勾出許多童年趣事,彼此生出會心的一笑。
李老師對萬物復蘇的春天有著極深的眷念。每年春天,春蠶和蝌蚪就成了我們的寵物,“找春天”更是室外課堂的常規(guī)節(jié)目,朝霞、月光、春雨在李老師眼里都是大自然恩賜的禮物,她會一次次帶著我們與它們近距離地接觸。“你看到了什么?”“你聽到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漸漸地,這三個問題已不再需要老師提問,而成為每個孩子隨心而發(fā)的欲望。在幼小的世界里,鳥鳴與蟲語并不晦澀難懂,空氣、河水、星空……一切都是活生生、暖融融、甜絲絲的,大人眼里常被忽視的細節(jié)在我們的觀察日記里變得越來越鮮活起來。至今,我還記得一個農(nóng)歷十五的傍晚,李老師帶著我們圍坐在公園橋邊的草地上,跟著她手風琴里傳出的音符,我們唱著《彎彎的小船》《讓我們蕩起雙槳》,聽著蛙聲,看著明月,編織出一個又一個美麗而動人的童話。
很多年以后,我和十幾個同學捧著鮮花相約去那個熟悉的院子。李老師見到我們,拿出很多準備好的零食,她指著每個人的臉敘述一些我們自己都已經(jīng)忘記的往事,搬出一堆她寫的著作,送給每人一本。合影時,她的身體豎得筆直,張開雙臂輕搭在我們肩上,臉上滿滿地寫著開心和安慰。臨別時,李老師拿出一摞作文本,依次叫著每個人的名字,把略微泛黃的本子遞給大家。當我接過寫著自己名字的作文本時,眼眶忽然有些濕潤,整本都是我40 多年前的課堂習作,李老師娟秀的紅筆印跡包圍著我稚嫩歪斜的文字,每一頁都是波浪、圈圈、評語。我知道,那是她留給每一個還記著她的學生們最珍貴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