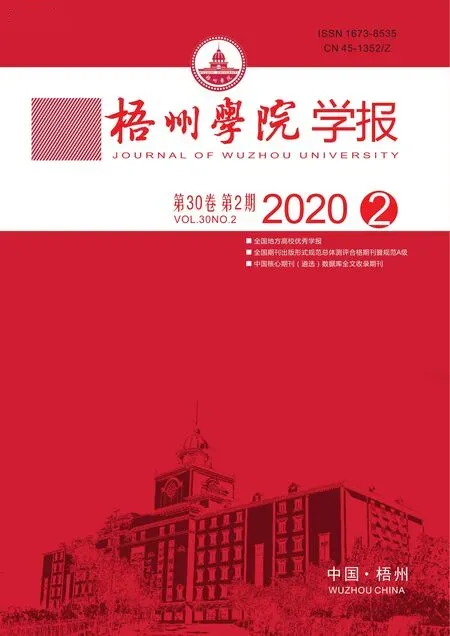“他者”的矛盾情結
——石黑一雄《別讓我走》的后殖民意蘊管窺
黃瑩瑩,杜興雨
(1.2.西北大學 外國語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一、引言
自20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掀起一場后殖民主義研究熱潮以來,身份認同問題一度雄踞西方文化理論界,“自我”與“他者”的概念常以二元對立的范式出現(xiàn)在公眾視野中。“一般來說,后殖民主義的話語體系為彰顯文化研究和人類科學等中心議題提供了契機。”[1]雖然后殖民主義思潮在20世紀中后期的文化研究階段略顯式微,但世界格局日趨全球化,跨文化、跨種族、跨范疇交際勢在必然,加之霍米·巴巴等新派學者側路進攻,試圖重新建構并解讀早期理論,后殖民領域的黃金時代又到來了。然而身份認同不僅僅是后殖民批評的寵兒,人類學理論也十分青睞于這一概念。“在人類學的族群研究中,‘族群’就是一種人類個體認識自我的整體意識——在西方族群話語體系中,族群始終是以一種‘他者’的面孔出現(xiàn)的,或純粹的文化群體,或想象的共同體,或工具性利益共同體。”[2]個體身份的邏輯結構確認總建立在對其他客觀實在參照的基礎之上,由鏡像反饋獲取自我認知。
石黑一雄的第6部小說《別讓我走》即從不可逾越的倫理禁區(qū)——克隆人的角度出發(fā),跳脫出傳統(tǒng)族裔作家拘泥于族群題材的僵化束縛,著眼國際主義話題,引發(fā)爭議性十足的觀照省思。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者就《別讓我走》多從倫理學、主題學、敘事學等角度切入文本進行了相應的解構分析,或是從法律邊緣性、反烏托邦等理論出發(fā)看待克隆人的身份焦慮,鮮少有論者以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義理論為基礎進行的文學批評。“在‘后殖民’一詞的名下,聚集著眾多充滿張力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話語。”[3]10在本文中,筆者將小說中的寄宿學校黑爾舍姆置于后殖民這一話語場下,探討人類作為殖民者對于被殖民者——克隆人的“他者化”過程,據(jù)此審視“去中心”背景下人類蓄意構建文化身份行為、邊緣他者的局限性,以期深化對特定族群尋求身份認同中所產(chǎn)生的矛盾情結認識,以及對“英國文壇移民三雄”之一——石黑一雄內蘊式寫作景觀的進一步解讀。
二、作為“他者”的克隆人
《別讓我走》中以凱茜為代表的克隆人自“誕生”以來便經(jīng)歷了一系列“他者化”待遇,懷揣著滿腹疑問,生存在不知何時會將其推向捐獻深淵的寄宿學校黑爾舍姆。如若最初那牽起克隆人萬千思緒的“美好校園”是一個灌輸他者身份的奠基過程,那么過渡時期的村舍及后來的金斯費爾德康復中心都在逐步強化克隆人的他者屬性。他們生來就是人類的參照,一種被隔離在“第三空間”中的“異己”派生物。
僅從生理結構上看,作為人類基因復制品的克隆人被迫背負了與生俱來的責任——為身體機能勞損或是局部細胞壞死的人類提供健康的器官,這也是他們無法抗拒的命運所在。“……我們和監(jiān)護人他們是不一樣的,并且和外面的人也是不一樣的;我們也許還知道,未來漫長的生活中,等待我們的便是捐獻。”[4]63事實上,克隆人自身的生理性從屬地位就先在地決定了他們不能合法享有獨立生存的權利。“基因復制品”和“器官捐獻體”成為了該群體的代名詞。雖然起初他們與多數(shù)人類同齡人一樣享有受教育的機會,擁有對于“童年生活”的珍貴回憶,但從始至終他們都是遵循著既定的腳本步步前行。
“……在黑爾舍姆,監(jiān)護人對待抽煙的事十分嚴厲。”[4]62這禁煙規(guī)定看似是校方的人性關懷舉措,實則是克隆人群體被無情物化的真切展延。監(jiān)護人們歸根到底在乎的是這些捐獻者的器官是否保持健康、免受尼古丁污染,即是否具備為買主們提供更優(yōu)質服務的身體條件。“你們是……特別的。所以,要保持自身良好的狀態(tài),讓自己的身體內部非常健康……”[4]63從生理層面反觀克隆人的一生,自其問世至器官成熟,再自可用器官所剩無幾至死亡,他們正是在不斷被“他者化”的過程中喪失獨立個體存在價值,最終走向被動捐獻器官的悲慘命運。生而為他者,何談主宰命運?
亦或是從社會中族群的共生屬性入手,克隆人原是不可逾越的倫理禁區(qū),必然面臨來自社會主要群體的族群排斥以及蓄意邊緣的危機。或出于恐懼等潛在心理,人類無法接受其高度仿真復制品與自己生存在同一空間之中,因此從一開始便將克隆人集中隔絕于主流社會之外的遙遠鄉(xiāng)村。在空間批評的視閾下,諸如《別讓我走》的各類文學文本中的諸多場所和景觀等空間便成為了一種蘊含多維文化信息的指涉系統(tǒng)[5]。空間的隔離象征著人類中心主義主導下的族群疏離,這不僅是人類為滿足自我延壽需求的具體措施,更是為其穩(wěn)固倫理中立站位的自我保護機制。
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諸多克隆人的姓氏都只是用一個字母來代替,一如凱茜·H、米奇·A、艾麗絲·F等。姓氏作為家族的印記,在大多數(shù)文化體系下都以其歷史向面象征著個體的根源與歸屬。然而,“長久以來,人們寧可相信這些器官是無中生有而來的,或者最多也就是相信它們是在什么真空里培育出來的。”[4]241人類主觀的回避恰恰印證了其作為“主者”的不知所措,甚至是愧疚難當。實際上,黑爾舍姆寄宿學校內部的顯著疏離即社會環(huán)境的縮影,人類在面對著眼前這些終將被無情剝奪生命的他者時,無法坦然直視,故決絕孤立。于社會而言,克隆人的他者身份內蘊著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后殖民批評理論觀中的核心要義之一:少數(shù)族(minoritarian)絕非因為數(shù)量上的絕對劣勢而被邊緣化對待,而癥結在于權力上的絕對被動。
在“生理他者化”以及“社會他者化”的共同作用下,克隆人族群注定會被動讓渡個體選擇權,遵從集權統(tǒng)治者的命運安排。其實,“他者化”這個術語并非新興產(chǎn)物,至少它可以追溯到殖民時代[6]。在戰(zhàn)爭時期的殖民國家里,宗主國作為權利主導方享有絕對的話語權,恣意剝削殖民地的一切剩余價值。而在小說前期發(fā)展階段,雖然作者石黑一雄努力建構一種看似“烏托邦”的微環(huán)境,為克隆人提供相對有話語權的童年生活,但正是在這樣不斷接受校方權威理念灌輸?shù)摹爸趁瘛边^程中,始終作為“他者”的克隆人們不僅萌生了千姿百態(tài)的個體意識,隨之而來的是其強烈的矛盾情結,自我掙扎、無法擺脫。迂回的征服策略在殖民擴張時期不失為一方良策,校方將器官服務意識篆刻在每個克隆人的心中,引導其主動付出,自愿捐獻。在某種程度上,后期器官“驗收”階段的約束成本便獲得了有效的縮減。
三、集權管理體系的規(guī)約
克隆人的童年時期都被主流社會隔離在遙遠的寄宿學校黑爾舍姆中,接受統(tǒng)一的“教育”以及管理,哪怕是后期的村舍也沒能夠賦予他們絕對的自由權。業(yè)已形成的集權統(tǒng)治體系在跨時空維度上的同一性成功地規(guī)馴與約束了該邊緣群體。無論是嚴禁克隆人做出有損健康器官的行為,還是始終對外界避而不談的舉措,這一切都以導向最終的“自愿捐獻”為原則。
黑爾舍姆的集權化管理模式通過女主角凱茜的憶述就可以前后參照地感受到——“……但是在黑爾舍姆,我們幾乎每周都要做身體檢查”[4]12;“埃米莉小姐,我們的監(jiān)護長……未經(jīng)召喚就去見她很需要一些勇氣”[4]36;“……我們還是不能真正明白她的那些訓詞。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她的語言,‘不配享受特權’和‘機會的濫用’”[4]39。某種程度上來看,黑爾舍姆不僅僅是外化的監(jiān)獄,而且是宏觀意義上的后殖民話語場。校方權威作為殖民一方,自始至終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制定游戲規(guī)則,強制“屬下”的克隆人實施。
在《別讓我走》書寫的這場殖民較量之中,盡管最初克隆人的個體生存意義是由殖民者依靠集權管理體系日益建構起來的,但由于事態(tài)發(fā)展后期“混雜性(hybridization)”的在場,被殖民者的價值觀發(fā)生了難以逆轉的改變。起初,在巴赫金(M.Bakhtin)“復調”理論和混雜理論的影響下,巴巴引入“混雜性”這個概念意在表征政治對立或是不平等狀態(tài)下的文化權威建構程度。但在理論發(fā)展過程中,巴巴將巴赫金的“混雜”置于后殖民主義話語場之中,強調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存在的第三空間,這種新型的過渡性存在不僅僅矛盾模糊、且交融雜糅。自“出生”起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疏離于主流社會的異質空間中,克隆人群體作為他者從被動接收話語方的規(guī)約逐漸墜入主動被馴服的深淵,這正是混雜性作用下的產(chǎn)物。
在他們的諸多成長階段中,“被他者化”的情況都是真實存在的[6]。遵從內心卻屢屢碰壁后,克隆人群體的潛意識初期癥狀(symptom)會在短時間內自發(fā)萌生,即——“我不能抽煙、必須保持身體健康、要服從于校方的管理、不聽話就會被訓斥或懲罰、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生活就是圍繞著捐獻展開的、不能離開學校去圍欄外的地方看看……”“癥狀的來源經(jīng)過分析可以知道是來自外界的各種印象,它們最初必定是顯意識的,后來因為被遺忘而成為潛意識的。”[7]一如學校老師們總是對種種規(guī)定背后的緣由保持緘默,對學生避而不談,學生起初試圖追問,此時即是顯意識階段;奈何抗爭無果,眾人漸漸也接受了這來自權力主宰者的命運安排。正如20世紀70年代出現(xiàn)在阿爾及利亞的籟樂一樣,混雜本身并不僅包含單一的過程[8],即克隆人群體本身對于既定命運的接受程度是在被動與主動之間來回切換的。
“至于癥狀的原因或趨勢則常為內心的過程,最初可能是顯意識的,但可能永遠不會成為顯意識的,而一直逗留在潛意識里。”[7]長此以往,潛意識不斷沉淀,即構成了克隆人們的“個人無意識”,待克隆族群中絕大多數(shù)成員的“無意識”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時,“集體無意識”應運而生,即——“不去問不該問的,完成監(jiān)護人們交待的任務就好;也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與我們無關;我們生來就是需要做捐獻者的,每個人都一樣。”在這樣的精神殖民統(tǒng)治下,克隆人們在被馴化的初期階段甘于屈從現(xiàn)狀,或懶于改變,或難于抗爭。但長此以往,現(xiàn)有的集權管理體系隨著主體和他者差異的日益外化顯露出難以彌合的弊端,克隆人開始思考“我究竟是誰,來自哪里?”
四、個體認知訴求的懸置
盡管克隆人作為人類的基因復制品存活于世,但作為“存在”本身,他們就具有其個性,此處強調個體屬性而非個體性格。前者較后者而言,所指涵蓋范圍更廣,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哪怕在如今高速發(fā)展的科技時代,克隆人是否具有真情實感也難以用客觀的數(shù)據(jù)衡量,換言之,就算其可被發(fā)掘,又如何證明這樣的情感是源自克隆人本身而非其基因源——人類呢?在石黑一雄的小說中,他以獨特的敘事策略將克隆人群體疏離于異質空間中,鮮少有人類參與,克隆人的買主也未曾以清晰的面目出現(xiàn)在讀者視野中。每個克隆人都擁有屬于自己獨一無二的經(jīng)歷及情感,個體性就產(chǎn)生了,隨之而來的是自我認知的需求。不僅是人類作為“主者”,需要通過構建“他者”來鏡像確認自己的存在;作為“他者”的克隆人也需要反復探究來核實自己的真實處境。
首先,小說中的克隆人要像“真正的人類”一樣追求個性,關注個體感受。從小生活在黑爾舍姆,克隆人群體早已適應了人類為其制定的游戲規(guī)則,也許一開始會歷經(jīng)抗拒的階段,但后來這種本能的抵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混雜性”的在場逐漸轉化為主動的接受。在巴巴看來,這樣的殖民關系是含糊不清的、是矛盾的、亦是混雜的——“……被殖民主體從來就不是簡單地、完全地與殖民者對立的。它不是將某些被殖民者設定為共謀的而另外一些被殖民者則是抵抗的,反而認為共謀和抵抗共存于殖民主體內一種搖擺不定的關系中。”[9]101這樣的權威結構中,策略上總會存在模糊性與矛盾狀態(tài)[10],這樣的矛盾狀態(tài)混淆了殖民與被殖民關系,克隆人們開始會無意識地“模擬(mimicry)”人類的行為,樹立個性標簽。“作為后殖民批評關鍵術語之一的英文單詞‘mimicry’,在漢語學界有很多譯法,如模仿、戲仿、戲擬、戲謔、學舌、翻易、擬仿等,在文本中一般通稱‘模擬’。”[9]106在巴巴的定義中,“模擬”一詞用以描述殖民者與被殖民之間的混雜關系,殖民權威方采取強制方式使被殖民主體接受所謂的“正確價值理念”,這即由風俗文化或是制度體系等基本要素組成。以黑爾舍姆為代表的校方話語施為場域正是在著力預設一套認知同構的完整制度體系,以期從多方位出發(fā)約束被殖民者的日常行為。
一如在克隆人們的童年時期,校方允許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收藏品。大家會把從拍賣會上得來的寶貝“財產(chǎn)”收集起來,小心翼翼地放在木箱內,收藏于床下,期待著哪天被夫人挑走。這樣的求勝心理就是追求個性的具體表征。再如抵達相對開放并且“成人化”村舍后,凱茜也開始對性愛蠢蠢欲動,這或許并不是源自她的本能沖動,而是“在觀察露絲和湯米一段時間以后,我相當好奇,想親自嘗試一下”[4]102。僅看到此,或許以為好奇使然。但凱茜在后面同露絲傾訴時,明確答道那就是她生理上的原始欲望,這和每個健全的“人類”所擁有的感受竟是一樣的。此即石黑一雄的匠心獨運,小說全文并未依靠描述克隆人器官移植過程中殘忍的畫面或是半點血腥來博得受眾同情,僅憑借對人物形象的高度“類人化”塑造,這一目的就達到了。每個克隆人都是被當做獨立的個體對待,有性格、有情緒,可他們卻偏偏擺脫不了被移除身體核心器官的命運。
然而,對于殖民主體來說,這種全方位的、卻并不完全準確到位的模仿是具有威脅性的[11]86,因為在這一模擬進程中的任意階段,被殖民者都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認知體系,時刻準備著推翻殖民現(xiàn)狀。如西方文明自古信奉自由、平等、民主、博愛等觀念,但倘若被殖民者全盤“模擬”了這種價值體系,那所謂的正義又由什么來維護呢?由是觀之,緣何整個黑爾舍姆起初并沒有監(jiān)護人敢于站出來澄清克隆人的身份事實自不待言。因此,模糊的“模擬”本身即諷刺、即嘲弄,揭露出殖民控制活動中強烈的不確定性,或稱不可控性。在巴巴看來,這種模擬行為本身就是建立在矛盾狀態(tài)(ambivalence)基礎之上的[12]。在英文中,“ambivalence”一詞通常指的是一種正反感情并存的搖擺狀態(tài),此外作為精神分析學術語,該詞又延伸為意指個體同時產(chǎn)生排斥和接納的心里狀態(tài),或譯作“矛盾情緒、矛盾情結、矛盾性、模糊性、曖昧等”,后被巴巴應用于后殖民領域。后文筆者將克隆人的這種“ambivalence”定義為“矛盾情結”。
“巴巴所指的矛盾狀態(tài)暗示道,殖民話語其實是建立于焦慮之上,而在這一張力結構中,殖民權力本身也受制于一種沖突過程的后果,也就是說,殖民權利也不是絕對的權威和強勢,被殖民者也不是完全被動的受害者,在他們的關系中,存在著某種模模糊糊的矛盾狀態(tài),而通過不斷的文化商討和交流,總會產(chǎn)生某種對抗和抵制的可能性。”[9]100《別讓我走》中克隆人的心理活動即呈現(xiàn)出上述的非典型、非二元對立的狀態(tài),這在消解了校方殖民權威的基礎上也派生出了其自身無法彌合的矛盾情結。
其次,就是身份認同(identity)問題。廣義上講,身份認同包含兩層含義:即身份和認同,是兩者的統(tǒng)一。在后殖民語境中,該問題的關注點較一般情形而言有所側重。在美國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看來,“普遍性權力關系語境中的認同構建分為三類:‘合法性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抗拒性認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規(guī)劃性認同’(project identity)。”[3]15或許是出于克隆人問題總在倫理邊緣徘徊的原因,小說關于“合法性認同”層面的構建未曾涉及,“抗拒性認同”層面有所覆蓋,但更具有指涉意義的部分是克隆人群體自我“規(guī)劃性認同”的建構。他們在與世隔絕的異質空間中摸索前行,試圖在不斷通過外界環(huán)境反饋自我形象的過程中訴諸身份認同。
一如克隆人在黑爾舍姆的最后一年的那場體育館棒球賽活動中,露西小姐作為唯一在場的監(jiān)護人凝重地向眾人潑了盆現(xiàn)實的冷水,似乎告知了眼前那群15歲少年的命運,又似未告知,起碼這在克隆人心中埋下了疑問的種子——“我們究竟是誰?擺在我們面前的到底是什么?”此后,大家會拿這件事當做玩笑來講,但當成熟以后,“它不再是尷尬和令人窘困,而只是陰郁和沉重。”[4]80以凱茜為代表的克隆人群體開始面臨“身份危機”,他們被告知在他們之中,不會有人成為電影明星,也沒有人能夠去美國,未來是不會實現(xiàn)夢想的等等。他們不知道自己除了捐獻器官外到底有什么作用,開始對于來自外界的傳言草木皆兵,試圖找到自己的那個“原型”。
在集權式管理的規(guī)馴與約束下,克隆人起初由被動接受殖民話語方安排到主動選擇相信命運;但在尋求身份認同的險途中,眾人又惴惴不安,試圖撥開迷霧、找到真相。正是在這樣混雜不清的糾葛中,每一位擁有個體屬性的“他者”都產(chǎn)生了相似的“矛盾情結”,無法抵制與反抗殖民者的體系化統(tǒng)治。
五、結語
《別讓我走》作為石黑一雄迄今僅有的一部科幻題材小說,族裔性特征趨于淡化,國際主義色彩不斷升華,內涵普適、受眾廣泛。作品中通過塑造一批“有靈魂的”克隆人來挑戰(zhàn)倫理邊界,引發(fā)讀者的廣泛關注,后殖民語境下殖民話語方與被殖民話語方的非典型對立關系回歸公眾視線,在“無意識”的作用下,或出于個人、或源于集體,“他者”的“矛盾情結”恣意生長,無盡的身心折磨清晰可辨。“尊重人的自由、自主性、自決權這項基本原則,并沒有在嶄新的科技時代出現(xiàn)什么發(fā)展變化,科技時代本身也沒有資格與能力使這項原則發(fā)生更新。”[13]此外,“夸大某些少數(shù)群體相異性的傾向會導致一種本質主義思想大行其道。”[14]作者以其意寓尤繁的小說敘事形式喚醒科技時代新讀者的文化反思能力,試圖消解傳統(tǒng)二元對立的人類中心主義格局,呼吁人們在失衡的社會結構中尋找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平衡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