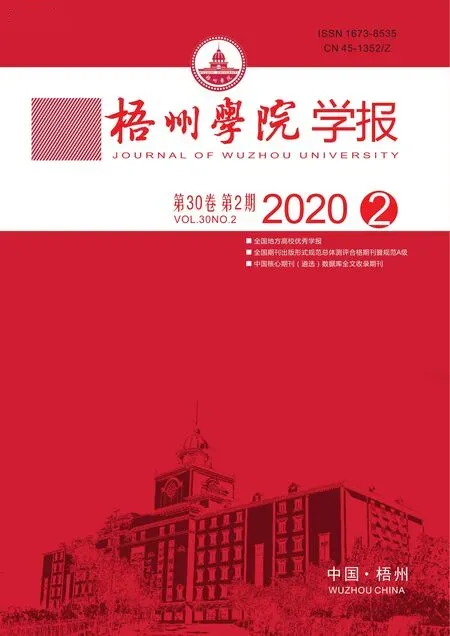中國—東盟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特征及國別序
戚兆坤,隋博文
(1.2.北部灣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廣西 欽州 535011)
2018年是中國—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系15周年,這期間中國—東盟關系取得巨大發展,從中國—東盟自貿區的成立建設到“升級版”的打造,以及習總書記提出以東盟為起點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構想,都助力中國—東盟成長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及產業內貿易得到深化發展,2017年中國—東盟進出口額分別為161.43億美元和158.37億美元,分別是2007年70.84億美元和39.33億美元的2.28倍和4倍。東盟是中國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優先選擇。中國東盟雙方具有相似的飲食文化、消費偏好、生產傳統、產品結構和市場結構,導致雙方農產品貿易有很強的競爭性和互補性,再加上良好的政治環境和運輸成本優勢,雙方農產品產業內貿易具備了形成和發展壯大的客觀條件[1-2],東盟成為中國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優先選擇。東盟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絕對的主力,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未來我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往來必將更加頻繁。當前跟蹤研究中國—東盟農產品產業內貿易,對于雙方進一步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農業合作關系,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文獻述評
Verdoorn開始關注產業內貿易以來,Balassa(1966)和Grubel等眾多學者不斷發展和擴展產業內貿易的研究內容,并提出衡量產業內貿易程度的各類指數[3-5],Falvey進一步把產業內貿易結構分為: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和垂直型產業內貿易[6]。在這些理論基礎上,國內學者對農產品產業內貿易進行了大量的定量研究。國內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國與東盟[4-5]、中美[6]、中日韓[7]、中國與南亞[8]、中國與中東歐[9],中俄[10]、金磚國家[11]、中國與中亞五國[12]、中非[13]、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14]等國家或地區組織。研究產業內貿易常用的指數有GL指數,GHM指數、FF指數、BI指數、TC指數和TM指數等。這些指數分別用來衡量產業內貿易程度、產業分類、邊際產業內貿易程度、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程度、水平型產業內貿易程度和產業內貿易結構測度等。其中一些指數既可衡量某產業亦可衡量某國家的產業內貿易水平或結構。衡量產業內貿易程度的指數眾多,使得問題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復雜性。許多文獻在完成GL等指數的計算之后,進一步選擇GL指數作為因變量,選擇GDP差異、人均GDP差異、對外開放度、FDI、各國之間距離等變量作為解釋變量,利用面板數據相關模型對影響產業內貿易程度的主要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由于BI等指數變化規律的復雜性,鮮有文獻分析導致邊際產業內貿易以及產業內貿易結構變化的影響因素。研究者使用的數據大多是來自UN Comtrade數據庫中的各類農產品貿易數據。文獻中對貿易農產品的分類方法主要有兩種,部分文獻采用聯合國SITC(REV.04)標準,該種分類方法將農產品分為四大類30小類;部分文獻采用WTO《農業協定》所定義的主要農產品中的前24章,即HS01-24。
關于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貿易格局、產業內貿易[4-5]、競爭性與互補性[15]、貿易便利化[16]、貿易效應[17]等幾個方面。特別是近來,部分文獻研究了“一帶一路”戰略及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對中國—東盟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影響[18]。對中國—東盟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研究的普遍結論,傾向于認為不同的產品之間產業內貿易的程度不同,食品及活動物類產品貿易以產業內貿易為主,其他類產品并沒有體現出明顯的產業內貿易特征。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增長較為緩慢,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增長較快。對于東盟十國來說,一般認為中國對越南、新加坡、菲律賓和泰國的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程度較高。由于文萊和柬埔寨等國的貿易量小且統計數據缺失比較多,部分文獻在分析時將這兩國省略。
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研究十分豐富,研究方法的使用有諸多共識(基本都使用幾類指數),由于影響農產品貿易的因素眾多以及農業生產的不確定性較大,另外東盟國家國情差異大,要準確把脈各國的農產品貿易,探析總結國家異質性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將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二、中國—東盟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特征分析
各類指數計算所需原始貿易數據均來自于UN COMTRADE數據庫。公式中提到的產業均指SITC(REV.04)標準分類下的四類產業,包括SITC0類(食品及活動物)、SITC1類(飲料及煙類)、SITC2類(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SITC4類(動植物油、脂及蠟)。

表1 中國與東盟十國進出口額及進出口總額所占比重(%)
農產品貿易國家間分布不平衡,根據表1,2017年泰國、印尼、越南、馬來西亞四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占中國—東盟貿易總額的87.2%。從時間維度來看,2005年至今,馬來西亞的貿易總額占比有所下降,由2005年的31%下降到2017年的13.7%。越南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很快,由2005年的6.3%上升到2017年的20.9%。老撾、柬埔寨、文萊一直排在最后三位,三國的農產品進出口總額之和的占比都小于3%。
(一)產業內貿易指數——GL指數
GL指數,即Grubel-Lloyd指數,是研究產業內貿易使用最多的一個指標,表達式為:


1.產業層面

表2 四類農產品的GLi和GL指數
根據表2可得出相關主要結論:1992—2017年SITC0類的GLi指數都接近于1,表明該類農產品貿易主要表現為產業內貿易。SITC1類(飲料及煙類)的GLi指數逐漸增加,由最低0.012增加到2017年的0.6057,表明這類農產品貿易由產業間貿易逐步轉向產業內貿易。SITC2類的GLi指數,1992—2006年遞減趨勢,由最高的0.7482下降到2006年的0.1125,說明貿易方式由產業內貿易變化為產業間貿易。2006年以后有所提高,但仍表現為產業間貿易。SITC4類的GLi指數一直保持很低水平,最高0.15,且最近十年從未高于0.031,沒有明顯變化,因此這4類農產品是產業間貿易。GL指數在2014—2016年這3年間大于0.5,其他年份基本能夠保持在0.4左右,2003年至今,表現為逐漸增加的趨勢。因此中國—東盟之間農產品貿易總體上呈現產業間貿易特征,但有向產業內貿易轉化的趨勢。
根據GLi計算公式,應從貿易順差和逆差的視角對其變化規律進行解釋。中國與東盟0類產品的進出口數額差異不大,進出口均衡,產業內貿易相對繁榮。中國與東盟國家(泰國近5年除外)1類產品的出口遠大于進口,優勢明顯,但是貿易順差呈現遞減趨勢,說明產業內貿易特征日漸明顯。對2類農產品中國一直存在巨大貿易逆差,因此產業內貿易程度相對較弱。該類農產品多為東盟國家特產,特別是天然橡膠、毛皮原料、輪木等。對這4類農產品中國也存在明顯的貿易逆差,特別對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只有對新加坡、文萊有小量順差。相對東盟,中國動物油和植物油、油脂和蠟的生產制造和出口明顯處于劣勢。中國對整個東盟的農產品貿易額增長快速,但2013年開始至今都表現為逆差,并且有逐漸增大的趨勢,所以GL指數顯示為產業間貿易。
2.國家層面

表3 東盟各國GLi指數(1)

表4 東盟各國的GLi指數(2)
主要年份東盟各國的GLi指數的計算結果見表3和表4。根據最近10年GLi指數的平均值進行高低排序,主要結論如下:0類農產品的排序為越南、泰國、新加坡、柬埔寨、印尼、緬甸、菲律賓、馬來西亞、老撾、文萊。其中前七國表現為產業內貿易,其他國家均為產業間貿易。柬埔寨最近3年的GLi指數小于0.5,有向產業間貿易轉化的趨勢。1類農產品的排序為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老撾、越南、印尼、柬埔寨、菲律賓、緬甸、文萊。其中只有前三個國家表現為產業內貿易,其他國家為產業間貿易。2類農產品的排序為菲律賓、越南、新加坡、文萊、柬埔寨、馬來西亞、緬甸、印尼、泰國、老撾。除菲律賓和新加坡1998—2005年和2013—2015年這兩個時間段內表現為產業內貿易外,其他國家幾乎都表現為明顯的產業間貿易。4類農產品的排序為泰國、越南、新加坡、緬甸、菲律賓、馬來西亞、老撾、印尼。前三個國家表現為產業內貿易,產業內貿易程度有逐漸增強的趨勢,其他國家表現為明顯的產業間貿易。文萊、老撾、柬埔寨的GLi指數均為0,部分原因是統計數據的缺失,最主要原因是中國與這三國之間4類農產品缺少貿易往來,特別中國對文萊的該類農產品進口量為零。

圖1 產業內貿易程度較強五國的GL指數變化趨勢圖
如圖1,根據GL指數平均值進行排序結果為越南、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印尼、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老撾、文萊。各國GL指數變化規律性不明顯,總體呈現曲折迂回緩慢上升趨勢,說明東盟各國與中國所有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程度逐漸增強。總體來說中國與越南農產品貿易屬于產業內貿易,菲律賓、新加坡、泰國三國接近于產業內貿易,其他國家與中國的農產品貿易基本都屬于產業間的貿易。
解釋各國GLi指數變化的方法仍是根據中國對東盟各國的貿易順差和逆差的變化,由于國家和產業的眾多排列組合導致數據信息量很大,限于篇幅原因,本文只提供一個分析的視角,具體原因不再深入探討。
(二)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BI指數
BI指數衡量邊際產業內貿易程度,其計算方法與GL指數類似,區別在于使用的數據是貿易增量。BI指數可以衡量一國的貿易發展潛力,BI指數越大說明產業內貿易增長潛力越強。


1.產業層面

表5 各類農產品BIi和BI指數
根據表5,得出以下主要結論:SITC0類農產品BIi指數多數年份大于0.5的,說明0類農產品貿易增量主要表現為產業內貿易,該類農產品貿易發展潛力較強。BIi指數最大達到0.9953,但最小卻為0,其變化不甚規律。1999年至今的大多數年份,中國對東盟0類產品的進出口增量表現為同步增加趨勢,說明中國—東盟0類農產品的貿易關系比較穩定。1類和2類農產品的BIi指數變化更加不規律,最大時分別可以達到0.9664和0.9747,最小時都為0,但大多數年份都小于0.5,所以這兩類農產品貿易增量是由產業間貿易引起,說明發展潛力弱。4類農產品的BIi指數幾乎都小于0.5,并且接近于0,所以這類農產品的貿易增量是由產業間貿易引起的,發展潛力最弱。根據BI指數變化規律,有時大于0.5,但多數都小于0.5的,所以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增量是由產業間貿易引起,說明未來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潛力較弱。
影響貿易增量的因素主要從農產品生產相關特點和貿易環境變化兩個方面進行考慮。BIi指數變化不規律,源于農產品的貿易增量變化不穩定。部分是由于農業生產具有周期性和季節性,農產品產量并不能保證每年都有穩定增長量,特別是部分東盟國家農業發展仍很落后,農產品增產穩定性得不到保證;部分由于貿易環境和貿易政策并不是一成不變,而是不斷調整的。
2.國家層面

表6 各國的BI指數
根據表6,各國BI指數大多小于0.5,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邊際產業內貿易基本是由產業間貿易引起的,且其變化不規律,說明與東盟各國沒有形成穩定的貿易增長關系。根據最近三年BI指數,只有菲律賓、新加坡、文萊、越南四國在其中某一年是大于0.5的,其他國家均小于0.5。2007—2017年間,每年農產品貿易增量表現為產業內貿易引起的國家最多兩個。越南和新加坡出現的次數最多,說明二者與中國農產品貿易發展趨勢比較穩定。
(三)產業內貿易結構測度指數——TM指數


表7 各國的TM指數
表7中TM>0.5的情形用加黑字體表示。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部分國家農產品貿易增量并不會持續出產業內貿易或產業間貿易的特征,而是兩種特征交替出現。越南在2000—2005年間均表現為產業內貿易,持續時間最長為6年;馬來西亞在1998—2002年間均表現為產業內貿易,持續時間為5年。1993—2017年間24個年度中,表現為產業內貿易的,越南有16個年度,新加坡有14個年度,泰國有11年度,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文萊各出現9個年度,緬甸有7個年度,柬埔寨有6個年度、老撾有5個年度。總的來說,中國對越南、新加坡的農產品貿易增量更具產業內貿易的特征。導致TM指數變化的主要原因與BI類似,區別在于前者是由所有農產品總量增量的變化量導致的。
(四)貿易競爭力指數——TC指數


表8 四類農產品的TC指數
根據表8,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結論:我國SITC0類產品的TC指數大于0,說明具有較強的貿易競爭力;SITC1類產品的TC指數多數年份保持在0.6以上,說明具有極強貿易競爭力,但是最近六年有持續下降趨勢;SITC2類產品和4類農產品的TC指數都接近于-1,說明不具備貿易競爭力。
(五)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結構測度

表9 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結構測度指數
根據表9,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結論:中國對東盟的所有農產品貿易增量來說,其產業內貿易特征和產業間貿易特征交替出現沒有持續性。總產業內貿易指數最高值為0.9802,最低時僅為0.0215。產業內貿易指數平均值是大于0.5,總體來看,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總量體現為產業內貿易。水平型產業內貿易程度和垂直產業內貿易指數都很低,大部分年份維持在0.4以下,部分年份接近于0,基本保持在比較低的水平。
三、產業內貿易水平及增長潛力國別序
(一)產業內貿易水平
衡量產業內貿易發展狀態的指數眾多,各類指數含義不同,作用亦有所區別。各國的產業內貿易程度并不穩定,特別是邊際產業內貿易程度。最近十年綜合來看與我國產業內貿易程度最高的國家有哪些?能否找到兩個以內的綜合性指標,用以衡量產業內貿易的程度及未來發展潛力?基于這一考慮,本文增加以下內容。
根據指數的分布特征,有些指數雖然平均值很高,但有些年份指數值很大,有些年份指數值很小,數據之間差異較大,變化不穩定,說明平均值只能反應數據的平均水平,不能反應數據間的差異化,不能反應貿易的穩定性,因此不便用來衡量貿易的綜合水平。因子分析通過對變量關系的研究,找出能夠代表原始變量絕大部分信息的少數因子,并計算因子得分,因子得分多少反應了樣本點水平的高低,因此可以根據因子得分高低對樣本點進行排序[19]。因子分析具有綜合評價的功能,根據數據之間的相關性,兼顧數據的水平和差異,找出用于綜合評價的因子。根據GL指數的含義,GL指數越高,代表產業內貿易程度越高及產業內貿易程度越強。因此可以使用因子分析,根據GL指數計算結果對各國產業內貿易的綜合水平進行評價。
考慮到分析結果更具時效性,能體現當前貿易發展狀態,因此本文只對2008—2017年10年的產業內貿易綜合影響力進行分析。利用2008—2017年東盟十國GLi和GL計算結果,進行因子分析,根據因子得分進一步對東盟十國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綜合水平進行排序,見表10。

表10 基于因子分析的各國影響力分析結果
根據表10可知,產業層面:2008—2017年間,0類產品貿易中,越南的產業內貿易程度最高,其次是泰國;1類農產品最高的國家是新加坡、馬來西亞;2類農產品最高的國家是菲律賓、泰國;4類農產品最高的國家是泰國、越南;對于所有農產品來說,產業內貿易程度最高的國家是越南、新加坡、菲律賓和泰國,影響力最弱的國家是文萊和老撾。
國家層面:越南的0類農產品、2類農產品和4類農產品與我國產業內貿易繁榮,但是1類農產品對我國存在明顯貿易順差,產業內貿易綜合水平低;新加坡4類農產品的產業內貿易綜合水平都排在前四位,說明我國與新加坡的各類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程度均衡發展;泰國0類農產品、1類農產品和4類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程度高,但是2類農產品存在明顯貿易逆差,產業內貿易程度很低;菲律賓的2類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程度最強,其他類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程度低。
(二)產業內貿易增長潛力國別序
由于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的變化不規律,數據之間的相關性小,不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只能退而求其次,采用聚類分析的方法。聚類分析是把“對象”分成不同的類別,也具備評價和排序的功能[19]。聚類分析距離的計算過程表明,其評價過程既涉及到數據的水平和差異,也涉及到數據之間的距離關系。
本文根據邊際產業內貿易反應的國家貿易潛力進行分析,仍然使用2008—2017年10年的BIi和BI指數的計算結果進行聚類分析。鑒于要使用到聚類分析的排序功能,因此采用系統聚類方法,類間距離的定義方法采用Ward法,樣本點間距離計算方法采用SPSS中的“塊”方法。

圖2 國家間聚類分析結果(1)

圖3 國家間聚類分析結果(2)
產業層面:根據圖2—4,圖中線越長代表邊際產業內貿易程度越強,產業內貿易增長潛力越大。2008—2017年間,0類農產品中,新加坡、越南產業內貿易增長潛力最大;1類農產品中馬來西亞、新加坡產業內貿易增長潛力最大;2類農產品產業內貿易潛力高的是菲律賓、越南;4類農產品產業內貿易增長潛力高的是新加坡、緬甸。對于所有農產品來說,越南、新加坡、緬甸的產業內貿易增長潛力最強;馬來西亞、印尼、老撾貿易增長潛力最弱。
國家層面:第一,新加坡是東盟最發達國家,各類農產品都具有很強的產業內貿易潛力;第二,越南、菲律賓與中國貿易具有良好的區位優勢,除某一類農產品外,其他類農產品都具有很強發展潛力;第三,文萊、柬埔寨、緬甸、馬來西亞對我國貿易或缺少區位優勢,或經濟發展滯后,四國除某一類農產品具有增長潛力外,其他類增長潛力弱。

圖4 國家間聚類分析結果(3)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主要結論:(1)1992—2017年,我國與東盟國家的農產品貿易總額不斷增加,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后,農產品相互貿易得到更快發展。(2)不同類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程度有很大差異,0類農產品和1類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相對繁榮且貿易競爭力強,2類農產品和4類農產品由于我國不具備出口優勢和競爭力,表現為產業間貿易。不同國家的產業內貿易程度不同,越南、新加坡、泰國、菲律賓表現較好。邊際產業內貿易程度變化不規律,產業內和產業間貿易的特征交替出現。(3)2008—2017年間,不同國家不同類農產品的貿易增長潛力不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優勢產業和短板產業,整體來說,無論產業內貿易還是邊際產業內貿易,越南、新加坡、泰國這三國的綜合影響力都表現出最高水平。(4)越南不僅農產品貿易總量高,并且具有最強產業內貿易增長潛力;新加坡和緬甸的貿易總量較低,但是產業內貿易增長潛力很高,具有較大的貿易增長空間;文萊的貿易量最低,但是產業內貿易增長潛力較強;印尼和馬來西亞的農產品貿易量很高,但是產業內貿易增長潛力卻最低。
政策建議:(1)首先提升產業內貿易水平低的產業的貿易程度,特別是SITC2類產品和4類農產品。應有效利用國際市場,優化貿易結構,在積極加強0類農產品和1類農產品貿易的基礎上,加快發展2類農產品和4類農產品貿易。具體可以通過進一步加深農產品的專業化分工,提升農產品差異化,實現品牌化,提高在國際市場上的認可度。(2)充分利用和發展中國—東盟自貿區。東盟具有區位優勢、政策優勢,東盟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最重要組成部分,這決定了“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在此基礎上我國應充分利用多邊合作平臺,進一步在SCO平臺和WTO平臺上擴大并深化合作,開啟我國與東盟十國的新時代,為我國的貿易創造新機遇。(3)充分考慮各國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增強農產品在生產和貿易上的互補性和競爭性,進一步挖掘東盟國家的市場潛力,特別是一些經濟大國和農業大國。(4)在農產品貿易中,應注意預防各類風險。如農業生產的安全性及自然風險,農產品國際市場的價格風險和匯率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