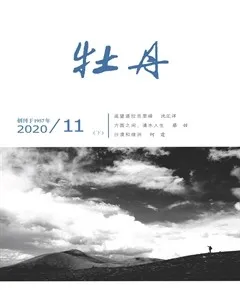對話與闡釋
明末清初,清言小品創作蔚然成風,張潮所作《幽夢影》一書以“幅短而神遙,墨稀而旨永”“所發者皆未發之論”而聞名。
張潮(1650-1709),字山來,號心齋居士,又號三在道人,清初文學家、出版家。張潮出身書香門第,自幼“穎異絕倫,好讀書,博通經史百家言,以文名大江南北”。少時勵志舉業,卻累試不第,以致“壯志雄心,消磨殆盡”。此后仕進之心日淡,遷居揚州,“杜門著書”。
一、文人交游網絡的形成
寓居揚州期間,張潮兼有商人、作家、選家和出版家多重身份,時人稱其文章巨手、風雅盟主。其間與他往來的文士有五百余人,在交往中,收集留存下來的尺牘就有一千五百通。在自著、選文和出版的過程中,他們逐漸結成了一個以張潮為中心的頗具規模文人交游網絡。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張潮刊刻《幽夢影》,書中收錄了格言、警句和隨感219則,參與點評者共113人,囊括當時各個階層的文人雅士。經過多年不斷積累,張潮征集到評語共699則,足可見其交游之廣。同時,這個交游網絡貫通東西南北、橫跨政商,關涉和反映了康熙年間文壇的諸多方面,頗具影響力。人言其“著作等身,名走四海,雖黔、滇、粵、蜀,僻處荒徼之地,皆知江南有心齋居士矣”。
這一文人交游網絡的形成亦與張潮個性沉靜、寡嗜欲、交游甚廣的性格密不可分。張潮善于交際,“惟愛客,客嘗滿座。淮南富商大賈惟尚豪華,驕縱自處,賢士大夫至,皆傲然拒不見。惟居士開門延客,四方士至者,必留飲酒賦詩,經年累月無倦色”。他的交游圈子既有王士禛、孔尚任、石濤、冒襄這樣的名士,也有孫默、黃周星、余懷、張竹坡這樣的同輩,更多的則是一些“無名之輩”。其為人慷慨,樂于資助文士,“近而井里,遠而關山,凡有告者,靡不周急之,且拳拳無倦意”。《幽夢影》中的評語皆多半出于張潮資助的受惠者,或是在受惠者的請托下寫出。相對其他的擁貲自厚者,張潮不同俗流,他以特殊身份和人格魅力從容游走在不同層次的文人之間,架構起一個龐大的文學交游網絡,給形形色色的文人提供了展現才華、交流切磋的舞臺。此外,這一交游網絡由相同階層或知識背景的文人雅士組建,又反映了這一特定圈層群體的苦樂悲歡、胸襟見地、待人接物、審美旨趣及人生體驗。
二、眾聲共鳴的對話體系
巴赫金認為“對話就是希望被聽到、希望被理解,得到從其他立場上做出的回答,這造就了一種雙方或多方的言說與傾聽的關系”,“這是語言的本質所在,是人的真實的生存狀態,也是一切偉大的藝術和審美活動的存在條件”。
雖自八股文占統治地位的明代起,文學評點之風日漸興隆,但能將友人、門生、學者等評語參錯其著作之中的少之又少,《幽夢影》不可不謂創新。清人楊復吉在《幽夢影》跋文中言:“昔人著書,間附評語。若以評語參錯書中,則《幽夢影》創格也。”
《幽夢影》突破了以作者為主體的寫作模式,而是以各色評語參錯其中,這些評語既有對張潮原著的贊譽,又有對上一輪評語的回應,形成了眾聲合奏、不斷闡釋的對話體系。從接受美學角度審視,這一體系既實現了作者、評者與讀者之間的交流,也構成了作者與參與評點的友人之間、友人與友人之間的對話關系,同時也從側面展現了作者文學交往活動的內容,實是其他清言作品所無的創新。其成書過程大致為作者首先亮出自己的論題,“懇請名家評語”,讓友人各抒己見,參與討論,做出評點。而這些評語無論是議論所發,還是傳抄時所附,都由張潮于后搜集整理,置于每則正文之下。《幽夢影》成書時間跨越二十多年,在不斷的傳抄評點過程中,不同的觀點角度、見解主張在這里匯集碰撞,交流生發。隨著參與者不斷增加,評點的數量越來越多,思想內涵也不斷深入,做到了“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下面以第208則進行說明。
“文人每好鄙薄富人,然于詩文之佳者,又往往以金玉、珠璣、錦繡譽之,則又何也?”
陳鶴山曰:“猶之富貴家張山臞野老、落木荒村之畫耳。”
江含征曰:“富人嫌其慳且俗耳,非嫌其珠玉文繡也。”
張竹坡曰:“不文,雖富可鄙;能文,雖窮可敬。”
陸云士曰:“竹坡之言是真公道話。”
在這樣的相互切磋中,眾人之言成為“綺語小言,而時多名理”。巴赫金指出:“真理不是產生和存在于某個人的頭腦里的,是在尋求真理的人們的對話交際過程中誕生的。”現實中,每個人的視閾都是有限的,而通過與他人的對話可以擴展和豐富自己的視閾,發現并不斷闡釋新的價值和意義。因而,《幽夢影》中友人間的交錯評點,相互拓展補充,闡釋生發,相對于一家之言,所涉內容更龐雜,參與者更多,傳播更廣,具有極大的開放性與交互性。其與時下的網絡媒體、微博、微信朋友圈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產生了“一葉百影,一人兼有眾妙”眾聲共鳴的效果。
三、極具個性化的審美創作
清言之風在明清之際盛行,并非偶然。正如魯迅談論魏晉清談,因時代政治黑暗,“名士不敢議論政事,而一變為專談玄理;清談而不談政事,就成了所謂的清談了”。此原因同樣適用于明清清言小品之盛行。避世揚州,張潮創作《幽夢影》,沒有選擇傳統儒家的經世致用、倫理教化之功,而更加貼近性靈派、公安派“獨抒己見,回歸性靈”的主張。第155則云:“立品須法乎宋人之道學,涉世須參以晉代之風流。”這兩句凝練概括了《幽夢影》一書整體的創作主張,也代表了作者的人生哲學和審美態度。
《幽夢影》更多地定位于個體本心,注重個體自由,自由地抒發個性,真實地展現日常生活和個體細微的感受。比如,第142則曰:“春風如酒,夏風如茗,秋風如煙如姜芥。”四時之風,帶給人不同的微妙感受,被張潮生動形象地進行了表現。再如,第28則云:“樓上看山,城頭看雪,燈前看花,舟上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境。”第40則曰:“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詩文。”活脫脫勾勒出一幅幅“英華發于外”的賢者、哲者、高者、達者、奇者、韻者的審美群像圖。
同時,作者還善用辯證思維考量世情風物,透過紛紜表象,發現深藏本質,悟出人生哲理。比如,第3則云:“無善無惡是圣人,善多惡少是賢者,善少惡多是庸人,有惡無善是小人,有善無惡是仙佛。”這一善惡標準超越了狹隘的種族觀、善惡觀,與佛家“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觀點相合。
從語言方面看,清鮮的生活氣息與雅潔的書卷色彩達到了完美統一,化平凡世俗為美與藝術,展現了生活情趣與詩情的結合。此外,《幽夢影》中還有相當多的讀書學問之論,如“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皆以閱歷之深淺,為所得之淺深耳”,將讀書與讀者的閱歷聯系起來,此三境界說被后世視作讀書的經典格言。
周作人說此書“是那樣的舊,又是這樣的新”。舊是指張潮學問的來源,新則是其強烈的個人意識與審美內涵。《幽夢影》之后亦有一些效仿之作,如清代朱錫綬的《幽夢續影》和近人鄭逸梅的《幽夢新影》,但它們都無法超越原作。
(陜西廣播電視大學)
作者簡介:李月媛(1981-),女,回族,陜西銅川人,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論、文學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