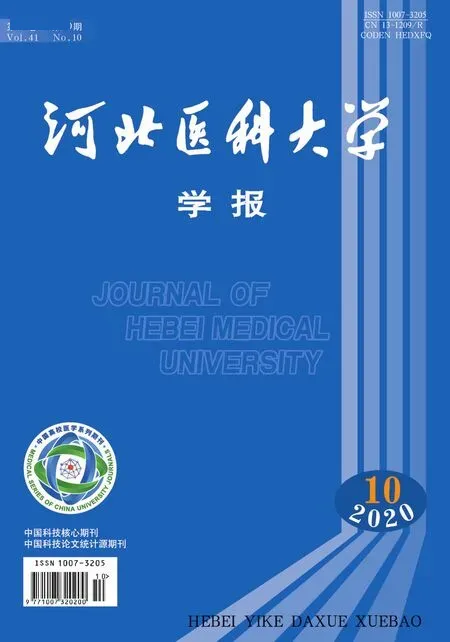醫學教育中理論與實踐關系的歷史考察及啟示
高 燕,翟海魂
(河北醫科大學醫教協同與醫學教育研究中心,河北 石家莊 050017)
縱覽我國醫學教育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反映了教育方法和手段的創新,鮮有關于醫學教育本質的討論,“重器輕道”的研究狀況難免會造成教育實踐的盲目性和局限性,尤其在討論醫學教育中理論與實踐關系問題上,從古至今就存在著“實踐第一”或“理論第一”的爭論。人們對醫學理論與實踐知識的來源、主次關系等問題所持有的觀念反映了教育者如何理解和構建醫學知識體系,直接影響著醫學教育的結果。本文基于西方醫學教育歷史的考察,對醫學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進行深入探討,為當今高等醫學教育改革提供思路。
1 醫學教育中理論與實踐相融合模式的演進過程
醫學理論包括了人類健康和疾病的系統化知識,其實踐是治療疾病和維護健康。從古希臘時期起,人們就已經意識到醫學既有著像法學和神學之類明顯的理論導向,智識色彩濃厚;又兼具大量的實踐性、經驗性的知識。在探索醫學理論與實踐相融合的過程中,西方醫學教育經歷了4個重要時期,從時間上大致可劃分為經驗主義模式(公元11世紀以前)、經院主義模式(11~15世紀)、實用主義模式(16~18世紀)和理性主義模式(18世紀中后期以后)。
1.1經驗主義模式(公元11世紀以前) 醫學知識源于經驗積累,自然哲學被引入醫學,醫學學習以實踐為主。
西方古代醫學一直被視為一門技藝(craft),治療疾病的經驗通過家傳師授的方式傳遞下來,積累成為一種普遍的經驗,憑借觀察病痛和治療之間的聯系形成的一般簡單而純粹的意識形式。因而,這種知識只是屬于一種本能與感覺,帶有很強的自發性和隨機性,缺乏科學的論證,還談不上是一種科學的知識。逐漸人們在實踐的過程中開始探索醫學的基本觀念和原則。起源于小亞細亞愛琴海岸的自然哲學賦予了希臘醫學更多的思考。“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是在融合希臘哲學的基礎上創立了四體液學說,他反對迷信和巫術,諷刺宗教行醫的欺騙性,認為疾病是一個自然的過程,癥狀是身體對疾病的反應,醫生應該從患者身上解釋疾病。因此,將觀察患者視為醫生的基本職責。至少有60篇源于公元前5世紀末到4世紀初的希波克拉底文獻流傳下來,這些文獻提供了早期反復和細心觀察的實例[1]。希波克拉底的實際觀察和哲學推理將希臘醫學從早期的經驗醫學推向了古代醫學的頂峰。
隨著醫學院校的出現,書籍開始成為醫生學習的資源,但是理論知識卻不受重視。亞里士多德認為,靠書本知識成不了醫生,蓋侖也認為對書本的依賴意味著醫學的倒退[2]。亞歷山大的經驗主義學派相信只有操作才能培養醫術,沒有理論也能行醫[3]。不過,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都提倡有教養的醫生。柏拉圖還區分了醫學理論和實踐,認為高級醫生的知識只能通過對自然或自然哲學的研究來獲得,而奴隸醫生缺乏這些知識,只有用觀察和經驗性實踐來學習醫學。總之,這一時期的醫學教育強調實踐,注重經驗,醫學停留于技術、手工藝和工匠的層面。醫學理論是在哲學家們長期自由觀察和思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使得醫學含有更多的經驗和批判的成分。
1.2經院主義模式(11~15世紀) 醫學知識源于對權威文本的注釋,自然哲學知識為醫學理論提供素材和方法,醫學學習以理論為主。
到了中世紀,這種寶貴的自由探索精神受到了限制。當指導醫學發展的核心價值觀是以服務于教會為目的時,醫學知識通常以經院注釋的方式被加以系統化,以保護其權威性不受破壞。這種方法需要應用自然哲學的內容和框架來解釋醫學經典。因此,中世紀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更偏重理論知識而忽視實踐,自由文理知識成為醫學的基礎學習,研讀權威文本成為學醫的主要方式。課程基本由文獻構成,希臘、阿拉伯的醫學以及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成為歐洲醫學的共同財產。
以中世紀最早的薩萊諾醫學校為例來進行考證。公元900年,薩萊諾成為醫學實踐的中心;10世紀末期,薩萊諾醫學還是以其實用技能而聞名,并非是醫學文獻和學術水平[1]。教學以傳統的經驗傳授為主,主要內容是一些常識性的醫藥習慣做法以及民間健康、飲食、衛生和藥物使用等[4]。11世紀中期,隨著醫學知識的復興,非洲人康斯坦丁諾斯(Constantinus Africanus)將大量的希臘和阿拉伯的醫學著作翻譯成拉丁語,促進了薩萊諾醫學校的發展。公元1080年左右,薩萊諾的學者開始將理論研究引入醫學教育[5]。通過經院的注釋方法創建了新的醫學知識體系,使得醫學成為大學的一門高級學科”[6]。
從薩萊諾醫學校的演變過程中,可以看到中世紀醫學教育從“實踐為主”轉向為“理論為主”的過程。當時意大利的醫學被分為2種不同的類型:實踐醫學(包括外科,歸入技術學科)與思辨醫學(被認為是文科的組成部分)[7]。直到15世紀以后,大學教師們才開始更加重視實踐教學。1543年,帕多瓦大學開設床邊教學,預示了醫學教育發展的新方向。
1.3實用主義模式(16~18世紀) 醫學知識源于臨床觀察,醫學學習以實用技能為主,醫學理論與實踐開始融合。
這一時期,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影響下,中世紀舊的醫學學習秩序和結構開始受到挑戰。16世紀后期,伽利略提出試驗和觀察是科學知識的源泉,極大地推動了包括醫學在內的整個自然科學的進步[2]。人們深信,自然科學的新發現可以建立一套新的醫學知識體系,這種觀念影響了17世紀的臨床醫學家布爾哈夫,他用機械原理解釋人體各種生理過程,把自然科學和解剖生理的學習納入醫學課程,并在荷蘭萊頓大學開設臨床教學,吸引了來自歐洲各地的學生。隨后,他的學生杰拉德·范·斯維登(Gerard van Swieten)在維也納設立臨床課程,臨床或醫院培訓開始被認為是醫生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18世紀,各國都在開展將傳統醫學教育與床邊實踐相結合的運動。這體現了一種希波克拉底潮流的復興,但是遠不同于原始的醫學觀察。這種觀察不是一種自發的實踐,而是建立了一種新的、系統的臨床教學體系。18世紀的德佐談到在主宮醫院講授臨床外科課程的經歷:“將最嚴重的患者帶到學生面前,對他們的疾病加以分類,分析疾病的特征,介紹采取的措施,進行必要的手術,解釋病情變化,展示病愈的過程;或者當治愈無效時,通過解剖來展示不起作用的原因”[8]。由此可見,這種學習已經不再滿足于對事物的籠統認識,而是側重于通過觀察、比較和分析大量收集的事實進行更加深入而具體的研究。醫學學習也不再局限于書本,各種實用技能變得重要起來,包括觀察機體各種生理現象,解剖人體結構,研究人體功能和檢查患者的身體等,醫學知識具有了更強的實用性,醫學理論與實踐開始走向融合。
到了18世紀末,醫院不再是中世紀意義的收容所。在新的醫院中,醫療和教學是核心,實用醫學受到重視。法國的主宮醫院和英國倫敦醫院的教學足以與巴黎、維也納和愛丁堡大學的醫學教學相媲美。事實上,這一時期醫學教學的主要場所都是在大學之外,這使得19世紀初的許多學生開始質疑大學醫學學習的必要性和實用性。
1.4理性主義模式(18世紀中后期以后) 醫學知識源于科學探究,實驗教學引入大學,醫學理論與實踐融合發展。
18世紀后期,理性主義的浪潮沖擊了德國的大學醫學,產生出一種獨特的醫學教學模式。醫學學習中,觀察、實驗、記錄事實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綜合眾多實驗結果,經理論思維形成學說,再通過學說指導科研沿著正確的方向進行[9]。“通過科學進行教育”的思想促使了學科的專門化發展,人們開始堅信醫學需要更精確、更可靠的科學研究,只能在大學里學習和傳授。在這種思潮的引導下,德國的實用醫學校相繼關閉,大學增加了醫學科學課程,建立了研究機構。到20世紀末,大學重新成為西方醫學培訓的主要場所。
德國以柏林大學為代表的現代大學是建立在理性主義基礎之上的。以威廉·馮·洪堡等人物為首的改革者認為,醫學是高深的學問,必須運用實證的方法來探索真理和教育從業者。到洪堡主導柏林大學的時候,基于教學與科研相統一原則確立起來了,大學開始定位于培養科學家的角色。從19世紀中葉起,德國大學引進醫學實驗教學,醫學知識不僅要在醫院通過患者來學習,新型的實驗醫學必須包括基礎科學知識,觀察、操作、實驗和其他類似方法引入了大學。臨床實踐和實驗室研究的結合推動了醫學基礎科學知識與專業實踐知識的良性互動,醫學理論與實踐進一步融合發展。
到1910年,幾乎沒有哪個西方國家的教育工作者或實踐者質疑醫學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需要認真的科學研究和嚴格的實驗室學習[10]。歐洲國家中的醫學生也不再只是從聽課與示教中獲得知識,而主要是從直接觀察實驗室的標本、開展試驗以及臨床病例中獲得醫學知識[11]。20世紀初,醫學生的學習已經遠不同以往,幾乎每門課程的學習都需要面對實踐、研究和技術問題。雖然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提出已經讓人們認識到醫學的社會屬性,但是迄今為止,自然科學的研究依然是醫學科學家們極力追趕的方向。
2 醫學教育中理論與實踐相融合模式的現代啟示
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始終是醫學教育中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早在10世紀,阿拉伯醫學圣人阿維森納就開始倡導“理論基礎結合相關治療的醫學實踐”[12]。但是如何達到理論與實踐的最佳結合,需要教育者不斷探索。醫學教學模式的演變本質上也是知識演進、理念更替和權力交迭的結果。知識、理念和權力等多種因素在不同國家的發展差異導致了大學醫學教育的不同樣態,也為現代醫學教育中思考理論與實踐的融合提供啟示。
其一,在尋求醫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途徑中,須考慮到醫學知識的生產方式,關注知識本身所具有的內在邏輯性。現代信息社會,醫學知識不再僅存在于書本之中,醫學知識來源的廣泛性促使了多元化知識生產的格局。基于信息技術和數字化環境的醫學教學模式成為醫學理論與實踐之間新的連接點,如建立多功能、多形式的虛擬學習平臺,開發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方式,使用遠程互動教室以及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等。未來醫學院校將更有創造性的運用現代科技來實現教育變革。同時,現代醫學知識生產的跨學科和跨組織性,對醫學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醫學理論與實踐需要吸收更多其他學科的知識。如美國早在40多年前就啟動了哈佛大學醫學院與麻省理工學院的聯合培養項目,支持優秀的哈佛醫學院學生在校期間同時攻讀工程學博士學位[13]。應用其他學科的理論框架和實踐途徑,可以為醫學教育提供新理論和新方法,從而培養具有多學科背景的復合型拔尖創新人才。
其二,醫學教育離不開其專業屬性,始終以服務于職業實踐為目的,為適應崗位需求而培養人才。因此,醫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邏輯起點還是在實踐,以實踐為基礎,在實踐中學習。長久以來,人們一直把醫學教育中的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分開進行,認為先要學習基礎的理論,才能到臨床實踐,理論先于實踐。直到現在,許多醫學院校還是沿用這種傳統的“割裂式”的教學模式,導致許多畢業生開始從業時不能適應崗位實踐的要求。事實上,并不總是先產生理論后有實踐的,醫學理論知識來源于實踐者的反思,實踐知識則來源于反思的實踐活動。還可以從畢業后醫生的學習方式獲得啟示,再如畢業后醫生的學習方式往往是在實踐中又重新尋找所需要的理論知識以適應醫療工作。可見,醫學生臨床階段的培養,絕不僅僅是臨床技能,而是包括臨床能力、臨床技能在內的醫學理論的升華[14]。因此,在醫學生的基礎學習階段,需要將理論知識及時地與實踐相聯系,使學生在情景中融入個體的意會能力,構建個體知識結構;同樣,在臨床學習階段,應在真實情景中去貫通理論,形成整合學習的意識,并將之內化成學習驅動力和知識生產力。
其三,在思考醫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目的時,要考慮到醫學知識的傳授不是簡單地賦予學習者的“教學產品”的過程。德科薩特(De Cosssart)等將專業領域的知識進行分析,發現了14個知識的要素,其中大部分包括了理論和實踐知識,還包括有經驗性知識、倫理知識、感覺性知識、自我知識、直覺知識、基于證據的知識和認知中的知識等[15]。這說明,醫學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遠非想象中的將理論放之于實踐那么簡單。醫學專業實踐行為實際上是各種知識-能力綜合體的表現,因此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無價力量應該是促進了學生這種知識-能力綜合體的形成和發展,而不是兩者的累加。自20世紀初,第三輪醫學教育改革提出以勝任力為導向的教育理念,注重教育結果,強調崗位能力,醫學教學中應更多關注的是如何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將單一的知識傳授和技能獲得轉化為學生評判性思維、溝通協調、自主學習和團隊合作等綜合能力的提升,以幫助學生更好地適應未來崗位的需求。
醫學教育關系公眾健康、國家強盛,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疫情的發生使人們更加認識到醫學教育在應對重大傳染病、實現全民健康等方面的重要性。對于兼具醫者和導師角色的教育者而言,需要深入思考醫學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不斷探索兩者的融合創新,才能在教育理念、教學模式、教學內容和方法手段上發生根本轉變,真正提高醫學人才培養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