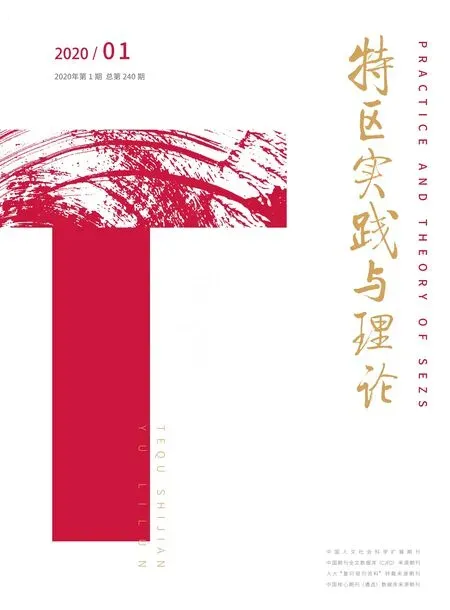真誠惻怛:良知的本然朝向
——良知之真誠惻怛與知是知非關系辨析
李健蕓
“良知”作為王陽明學說的核心概念,被陽明賦予了豐富的內涵,而其中“知是知非”顯得尤為重要,這層內涵在陽明晚年確定的“四句教”中得到了體現:“知善知惡是良知。”這里的善惡顯然就是“是非”。良知作為知是知非的“知”,在一念起處即能察知其善惡,而前提必然是知道是非的標準,那么,此是非標準為何?依陽明,此標準斷然不可能在良知自身之外,“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①(明)王陽明撰:《傳習錄注疏》,鄧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6頁。可見,良知只能以自身為標準對人的意識活動和行為進行是非判斷,與其自身同者則是之,異者則非之。然而,對此標準仍有進一步分疏的必要。筆者認為,良知之知是知非只有訴諸良知之真誠惻怛才能得到恰當理解,正是良知之真誠惻怛規定了知是知非的標準,本文欲通過以下三個方面論證這一點:首先,闡明良知之真誠惻怛的具體內涵;其次,闡明良知之真誠惻怛如何可能規定知是知非的標準;第三,分析在此良知之真誠惻怛規定下的是非判斷所具有的豐富而確定的秩序結構。
一、一體之貫通
對于是非判準如何得到規定,陽明在《答聶文蔚》里說:“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傳習錄》中)①(明)王陽明撰:《傳習錄注疏》,鄧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9頁。陽明把“知吾身之疾痛”與是非之心關聯起來,這種關聯在此至少可以理解為前提條件。但這里的知疾痛絕不僅是知個體的一身之疾痛,既然“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那么“知吾身之疾痛”就是在天地萬物本來一體的前提下,對此“一體”中不同于“我”的他者的困苦處境的醒覺,這種醒覺就像切于己身的疾痛感一樣真實。因而,這個意義下的“吾身”就不再是日常理解的封閉的個體性的肉身,而是一種在與他者貫通為一的前提下,對此貫通性的處境的整體醒覺。但是,為何知疾痛作為是非之心的前提?事實上,“知疾痛”在宋明儒者那里常被用來作為論“仁”的一條路徑,②對于以“知疾痛”論仁的相關討論,可以參考陳立勝:《“惻隱之心”、“他者之痛”與“疼痛鏡像神經元”——對儒家以“識痛癢”論仁思想一系的現代闡釋》,《社會科學》2016年第12期。也即以覺言仁的路徑。但知疾痛本應屬于惻隱之心,又如何作為是非之心的前提?
對此,不妨借助朱子的相關論述以期獲得一種理解的可能。朱子在論及惻隱之心與其他三心的聯系時說:“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卻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三),③(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297頁。朱子強調了惻隱之心“先動”的意義,如果說是非之心作為一種判斷是非的意識活動,那前提必然是意識先已活動,而惻隱之心“先動了”,強調的正是這種在先的活動性。這里正如陳立勝教授指出,此處的“先”不是時間上的在先,而是“‘惻隱之心’為其他三心的發生奠定了基礎”。④陳立勝:《惻隱之心:“同感”、“同情”與“在世基調”》,《哲學研究》2011年第12期。惻隱之心相對于其他三心的優先性正在于惻隱之心所指示出的心的醒覺能力是其他心的活動的基礎。借此可以對陽明以知疾痛為是非之心的前提有所理解。“知疾痛”不僅限于對他人困苦狀態的疼痛感知,而是以人在這種特殊處境下所體驗到的疼痛感,指示人心本有的指向他者、貫通他者的活動能力,而這種活動能力是人心進行是非判斷活動的基礎。
人心本有的貫通他者的活動能力又被陽明稱為“良知之真誠惻怛”。在《答聶文蔚(二)》中,陽明有如下論述:
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傳習錄》中)⑤(明)王陽明撰:《傳習錄注疏》,鄧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8頁。
“惻怛”一詞本于孟子“惻隱”,依朱子注:“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⑥(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39頁。如此,其義與上文討論的“知疾痛”相同,即以特殊處境下的疼痛感知指示良知貫通他者的活動能力。“真誠”強調實有之義,實有意味著這種能力不是外在影響的結果,而是良知內在本有,即良知內在本有這種貫通他者的活動能力。陽明在此明確以“本體”一詞指稱良知之真誠惻怛,這里的“本體”當為本來狀態的意思。這意味著真誠惻怛是良知本具,且良知的隨處發動都有真誠惻怛貫注其中。這一點也可以從陽明反復強調“只是一個”得到闡明。“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一個”強調良知的同一性,即在任何處境下都是同一個良知在發生作用,都有“真誠惻怛”在發生作用。因此,真誠惻怛作為良知本具的貫通他者的活動能力,具有普遍的貫通性,而此普遍的貫通性又必然具體呈現在某個個體所處的具體處境中,如事親、從兄和事君。
同時,陽明在此還為良知之真誠惻怛賦予了“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的內涵,對這個表達需要做進一步的細致分析。陽明在另一處將良知和天理的關系表達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答歐陽崇一》,《傳習錄》中)①(明)王陽明撰:《傳習錄注疏》,鄧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6頁。陳來教授認為:“以良知為天理之昭明靈覺并不是指天理能夠知覺……在‘昭明靈覺’前加一限制語,既表示這個靈覺不是指認知意義的能覺,又表示這個知覺自身具有規范意義。”②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62頁。這意味著良知是一種具有確定價值內涵的知覺。同時,這也進一步體現出良知和天理具有某種內在關聯,體現在“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這個表達中的“處”字。“處”字表明良知本質上是天理的一種呈現形式。天理必定會在現實層面以各種具體形式呈現,而當天理以“昭明靈覺”的形式內在于人并通過人而發生作用得到呈現時,就在人這里獲得了“良知”這種呈現形式,進而作為人的內在的道德原則主導人的意識活動和實踐活動。在“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這個表達中,“發見”二字更清楚地表明良知就是天理的呈現形式,以“自然”和“明覺”的形式得到呈現。“明覺”旨在強調良知作為“知”的一面,即一種明徹知覺的能力,而“自然”則表明良知的發動非主觀、非人為。非人為指良知的發動不是后天人力施加作用的產物;非主觀指良知的發動不是人主觀意愿選擇的結果。無論人愿意還是不愿意,良知都在發動,人的意愿所能做的只是:要么順循良知的發動而“致”良知,即順循良知所向而實實在在做“為善去惡”的功夫;要么違逆良知的發動而為惡。這種理解在陽明對弟子的如下教導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傳習錄》下)③(明)王陽明撰,《傳習錄注疏》,鄧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4頁。“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傳習錄》下)④(明)王陽明撰,《傳習錄注疏》,鄧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6頁。這里說“良知還是你的明師”,“爾只要實實落落依著他做”,乍看之下,似乎良知和行動主體“爾”分別為二,實際上,“爾”指的是人能夠做出主觀意愿選擇的層面,而“良知”則是人內在固有的不由主觀意愿選擇產生的道德原則。但另一方面,正是這內在固有的良知才被陽明視作“真吾”:“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從吾道人記》)⑤(明)王守仁撰:《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0頁。這里可以看出陽明對人的主體性的理解,人的真正的主體性的實現實則在于對不由人主觀選擇的內在固有良知的主動實現。
經由上述分析,“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的意涵已然清晰,進而也就對良知“只是一個真誠惻怛”的意涵獲得了進一步理解的空間。如上所論,“真誠惻怛”指的是良知固有的指向他者、貫通他者的活動能力。這種活動能力同時就是“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因而這種活動能力就是天理的一種呈現形式,這是一種不為人的主觀意愿所左右的根源上的活動性。進一步而言,作為天理的呈現形式的良知之真誠惻怛,也就同時提供了確定的價值內涵,而這一點正構成了是非判斷的起點。因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作為一種貫通他者的活動能力,從其在貫通他者中達到的一體之醒覺上看,構成了是非判斷活動的前提,而從其作為天理的一種呈現形式而言,則更進一步提供了是非判斷所依循的確定價值內涵。那么,由此良知之真誠惻怛獲得的確定價值內涵是什么?
二、一體之成全
依照上文的分析,良知之真誠惻怛指的是良知固有的貫通他者的活動能力,而這種貫通又不是在原本孤立的不同個體之間施加外在關聯,而是基于“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的前提,正是由于在根源上萬物本來一體,才有可能在現實中由一個具體的個體出發可以貫通另一個個體。依陽明,這種貫通性必有一種朝向對一體之仁的成全,即個體在良知之真誠惻怛的作用下,必有一種不容已地對此貫通關系下的他者之成全。陽明在論及孔子境界時說:
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答聶文蔚》,《傳習錄》中)①(明)王陽明撰:《傳習錄注疏》,鄧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1頁。
這里所言的“疾痛迫切”便是基于一體之仁的前提下對他者之痛的切己體驗,這種切己的痛感體驗讓自己“不容已”地想要有所行動。然而,這種想要有所行動的意愿出于何種動力?其目的為何?現代學者常將這種意愿理解為同情心的驅使。但是,一般理解的同情理論要求一種“設身處地”想象他人處境的思慮的能力,而這是與陽明的真誠惻怛不同之處。正如現象學家耿寧(Iso Kern)敏銳地指出,陽明所謂的“真誠惻怛”是“一種在情感上受到他者處境觸動的狀態和一種想要為它做些什么的傾向:在情感上關懷他者,在情感上參與它的處境”,并且,“這種情感的參與還不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意識,它不會試圖以想象的方式置身于其它生物的處境之中,并且不會試圖從它們的‘視角’出發……它更多是一種在對另一個行為生物身臨其境之感知中的前反思的、直接的被觸動或被感動狀態。”②[瑞士]耿寧(Iso Kern)著:《人生第一等事——王陽明及其后學論“致良知”》,倪梁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308-309頁。耿寧在此以“直接的被觸動狀態”理解真誠惻怛,而這種狀態會帶出一種為他者做些什么的傾向,以此區分了“一種深思熟慮的”,試圖以想象方式置身于他者處境的同情理論。這樣的區分對于理解良知之真誠惻怛和以盧梭為代表的古典的同情理論大有助益,③關于盧梭的同情理論的分析,可參看[法]弗朗索瓦·于連(Francois Jullien)著:《道德奠基:孟子與啟蒙哲人的對話》,宋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9頁。良知之真誠惻怛表現為一種當下性的、與他者貫通為一狀態下對他者之痛的同時感受。依照上文的分析,良知之真誠惻怛是良知本具的普遍的貫通他者的活動能力,這種活動能力是根源性的,而非有待于某種特定情境才會生起,陽明只是以某種特殊情境(“知疾痛”)提示出此根源上的活動性,但這并不意味著良知之真誠惻怛只有在身處他者之困苦狀態中才會發生。
由于良知本身的活動無息,“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傳習錄》下),④(明)王陽明撰:《傳習錄注疏》,鄧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0頁。故而,人的這種不容止息的活動一旦停止,必是私欲隔斷,而良知的活動又必有一種實現自身、恢復自身的動力,使得個體在此動力下能夠主動克除私欲,順循良知發用,而良知也由此恢復自身。陽明如是論及這個過程: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于圣人也,特其間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圣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答顧東橋書》,《傳習錄》中)⑤(明)王陽明撰:《傳習錄注疏》,鄧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3-114頁。
在這段文字中,陽明闡述了人心的三種狀態。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切行動的指向無非“遂其一體之念”;常人之心本來與圣人之心相同,但由于有我之私、物欲之蔽,于是失去了本有的以萬物為一體的狀態,而相互間隔、各有其心;圣人教化天下,使得常人能夠克除私欲、去除障蔽,恢復“心體之同然”,即所有人心本來相同的活動狀態,這種狀態就是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顯然,圣人教化,并非把一種人心本來沒有的東西施加于人心之中,而是喚起人心本有的狀態。在陽明看來,一切應該達到就是本來具有的狀態,萬物一體的目標本就是良知恢復自身活動的目標,它內在于良知的活動之中。圣人的教化與其說是圣人的施與,毋寧說是圣人喚起人人本有的良知,讓現實中已經被私欲隔斷的不同的個體,得以在內在本有良知的動力下克除己私,走向彼我貫通并將此貫通性落實為具體行動,實現在一體貫通關系下的整體成全,而最終無非恢復良知本有狀態。因而,良知在個體身上的活動無非是恢復自身本有的對萬物一體的醒覺和在此醒覺下的有所作為、有所成全。
陽明在《大學問》中明言:“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①(明)王守仁撰:《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8頁。陽明在此明確否定了萬物一體是“意之”的結果。所謂“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當中的“能”,不是抽象地在心之本然的意義上所講的潛能,而是在現實層面“大人”就已經把對天地萬物的責任擔負起來并已經切實為此“一體”有所行動。正是“大人”已經有所行動了,才能稱其“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大人”只有在徹底安頓了萬物之后才能稱其“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顯然,對于有限的個體人生而言,對無盡的萬物的安頓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現實中都不可能。不僅如此,一旦承認了這種可能,就意味著良知之用有完成之時,完成也就意味著止息,但良知之用本是自然生生不息,良知之用有完成之時對于陽明而言是不可接受的結果。其實,這里“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能”,對于真實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人而言,指的是良知本具的貫通他者的活動能力的暢通無阻,由于良知的活動在根源上可以普遍實現于天地萬物,故而在根源上良知“能以天萬物為一體”,不是停留在抽象的潛能上言說,而必然實現在大人身處的每一個具體處境之中。也就是說,對于大人而言,他可以在任何具體性中都讓良知本有的貫通活動得到暢通無阻的實現,這種實現必在具體行動中才得以可能真正實現,故此而稱其為“能”。
綜上,筆者借助對陽明論萬物一體的分析,闡釋了陽明所論的萬物一體并非抽象的靜止的一體,而是在良知自身活動下,達到的對天地萬物本來一體的完整醒覺。但是,就現實而言,良知必具體呈現于個體在具體處境中的活動,個體在自身內在本有良知的動力下,發而為一種指向他者、貫通他者的活動,而這種活動必在具體行動中才能得到真正實現,這樣的實現無非是“遂其一體之念”,而其終究指向則是恢復良知本有的活動狀態。通過對此過程的闡釋,良知的活動實有其確定不移的朝向:在對貫通活動的充實中,實現自身、恢復自身。
對良知活動本然的確定朝向的揭示,無疑有助于理解良知之真誠惻怛為良知之知是知非立定標準。其實,牟宗三已經注意到陽明論述的良知有其確定方向,牟宗三認為:“良知之照臨不只是空頭地一覺,而且即在其照臨的一覺中隱然自決一應當如何之方向,此即所謂良知之天理。”②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第151頁。但是,此說雖然認為良知有其確定的應當如何之方向,但仍然未能指出這個確定的方向就是良知貫通他者、成就他者,在此過程中朝向對自身本有活動狀態的恢復,而這就是體萬物為一。依上文的分析,良知之真誠惻怛正是良知根源上的活動性體現出的良知本然的活動方向,也是良知實現自身、恢復自身的動力所在。這樣,陽明將良知之知是知非歸結為“好惡”便能獲得深入的理解: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傳習錄》下)③(明)王陽明撰:《傳習錄注疏》,鄧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9頁。
這種表達將良知對是非的判斷歸結于好惡,如果良知的是非判斷不是一種任意的意見表達,而有其根源上的恒定性,那么這里的好惡顯然不同于人日常當中易變的感情,而是對良知活動本具的恒定朝向的揭示。良知隨其發動就必有其確定不移的朝向,這種朝向是根源性的、恒定的,而人的意識活動和行為如果與良知自身的朝向相合就會表現為喜好,與自身朝向不合就會表現為厭惡,唯有這種根源于良知的朝向的好惡才可能作為恒定的是非判斷的準則。故此,良知活動的恒定朝向為良知的知是知非活動確立了標準。對于個體的意識活動和行動而言,順循此朝向而實現良知,就是“是”、是“善”,阻礙這個過程的實現或與之相反,就是“非”、是“惡”。這就是從良知之真誠惻怛出發,為是非判斷立下的確定不移的標準。
三、一體之節次
經由上文的分析,良知之真誠惻怛與一體之仁所揭示出的良知活動的恒定的朝向,以及由此朝向所規定的確定不移的是非判斷活動的標準,已然得到闡明。然而,正如上文反復說明良知的活動必然從具體個體的具體處境出發才能得到落實,此確定不移的朝向和判準也必然落實在具體性當中。那么,由良知之真誠惻怛所揭示出來的良知活動的本然朝向,如何在千差萬別的具體性中得到展開?此展開過程是否能夠進一步為是非判斷活動提供標準?
依陽明,良知之真誠惻怛的發動自然有其固有的秩序,這被陽明稱作“天然自有之中”,陽明說:
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發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發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個。雖則只是一個,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發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答聶文蔚》,《傳習錄》中)①(明)王陽明撰:《傳習錄注疏》,鄧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8頁。
這里,陽明強調了良知在任何處境下的發動都只是“一個真誠惻怛”,這是在根源上確定良知的同一性。任何具體處境下的發動都是同一個根源的充分發動。但是,這種充分性本身卻又在不同處境下展開為具體的輕重厚薄,這里的“輕重厚薄”指的是良知主體在與他者的貫通關系中,為他者有所行動時所表現出來的差異和區分,但每一處的輕重厚薄又都是良知的充分發動。這是“天然自有之中”,所謂“中”即最恰當的分寸。陽明在《大學問》中同樣申說此義:
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于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于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②(明)王守仁撰:《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9頁。
這里同樣強調了良知之發見,有其不能用私意小智擬議增損的“輕重厚薄”“天然之中”,也就是在不同關系下的行動的恰當性。并且,這種恰當分寸在不同關系下都是確定的。良知在不同的貫通關系中,對他者投入的程度有輕重厚薄,且“毫發不容增減”,良知在何種關系下應當投入何種程度,有其不可改變的確定性,但這種確定性本就根源于良知之真誠惻怛自身的發動。一旦人在某種特定關系中的行動分寸沒有達到這種確定性,“可得增減”,就已經失去了良知本體,不再是良知本然的活動狀態,而是私意小智的運用。可見,良知依其自身的發動就為具體關系下的行動提供了確定不移的輕重厚薄的分寸,凡是失了這種分寸的行動,也就是“非”。
看起來,良知為人在具體關系處境下的行動確立了確定的分寸,這樣的“良知”更像某種外在于我的客觀標準。實則不然。良知之于有限的個體而言,固然有其超越性,這種超越性首先表現在良知為人所固有,“固有”二字就意味著良知本就不是人的主觀意愿的產物,良知的活動也不以人的意愿為轉移,而有其恒定不變的方向。在這個意義上,良知有其客觀性,而非主觀任意的師心自用。也正因如此,良知才能“公是非,同好惡”(《答聶文蔚》,《傳習錄》中)。③(明)王陽明撰:《傳習錄注疏》,鄧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9頁。但是,良知的客觀性絕不意味著良知是外在于人的尺度,良知為人的行動所確立的分寸本就內在于人自身,良知的活動必然在具體個體的具體處境下才能得到真正呈現和展開。對于良知固有的輕重厚薄,陽明還有如下說法: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此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逾越,此便謂之義。”(《傳習錄》下)①(明)王陽明撰:《傳習錄注疏》,鄧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1頁。
陽明在此同樣把厚薄的差異訴諸“良知上自然的條理”,這種不可改變的條理就是“義”。張學智教授認為這里的“義”指的是:“在萬物一體的境界中,如果需要分別對待,良知又自能作出分別。這種既分別又合于道德原則,即‘義’。”②張學智:《明代哲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06頁。此說甚是合當。不過,進一步的問題卻在于良知做出這種分別的依據是什么?應當如何理解這里所謂的“良知上自然的條理”?
從陽明整段話對厚薄的解釋看,所謂“條理”呈現出的厚薄是在“忍”與“不忍”的差異中呈現出的一種秩序,而這種秩序指向了良知之真誠惻怛在具體實現過程中所展開的差異結構。在這個差異結構中,陽明依次討論了用草木喂養禽獸、宰殺禽獸養親、祭祀、宴饗賓客,乃至在最特殊的情況下,當食物極其有限時,忍心于舍棄拯救非至親的人而選擇拯救至親。但是,再進一層觸及到吾身與至親的關系時,陽明堅決認為此處“不得分別彼此厚薄……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這其實根源于良知固有的指向他者、貫通他者的本然朝向,此處若是再分別吾身是厚、至親是薄,那就已經阻礙了良知根源上的活動朝向,而良知的這種根源上的活動正是“仁民愛物,皆從此出”。陳立勝教授認為:“‘自有厚薄’的說法乃是就具體的惻隱之心的發動者而言的,而不是一個泛泛的所指。盡管每個人都是某個(些)人的‘至親’,但每一個具體的人的‘至親’都不可能完全重合,所以每一個人‘忍’與‘不忍’亦表現出相應的情境性差異,所謂‘道理合該如此’即此之謂也。”③陳立勝:《王陽明“萬物一體”論——從“身—體”的立場看》,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00頁。然而,即便這樣的解釋,仍有不得不面對的困境。盡管不得不承認每一個具體的人都在其具體的倫理關系中有各種的親疏遠近,但如果由此確立良知發動的厚薄,那就意味著同一個人對一個人而言是“厚”,而對另一人而言是“薄”,那這是否意味著不同的人有各自不同的“良知”?這與陽明所說的“公是非、同好惡”豈非矛盾?
實則不然。良知自然的條理表現為良知之真誠惻怛在貫通他者的活動中,隨其貫通關系的遠近親疏而有厚薄之分,而良知的實現又必落實在具體的個體活動當中,其要求則是厚其所當厚、薄其所當薄,因而這樣的厚薄關系實則是在具體個體自身關系中展開的厚薄差異。“公是非、同好惡”意味著,任何一個人都應該在自身展開的關系中,厚其所當厚、薄其所當薄,而一個人不僅厚自己之當厚,且在看到任何另一個人厚其所當厚時,都會以之為“是”,看到他厚其所不當厚時,則會以之為“非”。簡言之,在良知的作用下,一個人不僅能夠落實自己的厚薄,還能夠理解他者應當落實的厚薄,并在一體關系中幫助他者落實他自己的厚薄。這一切又無非是良知自身的條理在具體個體身上的展開。正是由于良知只是一個,良知具有同一性、普遍性和客觀性,所以當良知在任何個體身上實現時,這個人都能同時理解普天下所有人依其良知所應當展開的厚薄關系。
由此可見良知自身本有的節次和秩序,這種秩序一旦在具體個體身上實現時,就表現為由此個體出發,依循其具體的厚薄關系而貫通他者的過程。因此,當良知在具體個體身上實現時,具體的是非就呈現為良知之真誠惻怛,在恒定的貫通他者、恢復自身一體之仁的實現過程中,依其具體的貫通關系而自然展開的厚薄與節次。此節次在現實的具體性中各自不同,但又都是同一個良知的發動,這種同一性表現在一個人只要依循其良知,就不僅能夠自知自己應當實現的節次,而且知道普天下所有人各自應當實現的節次,并在朝向一體之仁的“不容已”的動力下幫助他者實現其自己的節次。據此,良知之真誠惻怛所規定的是非標準不是抽象的和單一的,而是在每一個具體個體的具體處境的展開過程中呈現出豐富的差異性和層次性的秩序結構,而這個秩序結構又是同一個良知的展開,良知之真誠惻怛所指向的同一性因而內在包含了具體而豐富的是非的差異性。
四、結語
經由上述辨析,筆者已經依循陽明思想自身的展開邏輯和細致的文本分析,對良知之真誠惻怛與知是知非的關系進行了闡明。良知對是非的判斷根源于良知活動本具的固有的恒定的朝向,意識活動的發生或者與此本然的朝向相同、或者與之相異,而良知隨此意識活動發生的同時生起好惡、做出是非判斷,同則好之、是之,異則惡之、非之。因此,良知作為是非判斷的頭腦和主宰,其固有的恒定朝向先于一切意識活動而具有、始終作用于一切意識活動之中,并為一切意識活動和由之帶出的行為確定價值內涵,也即善惡是非的內容。這就是良知的本然朝向與良知之知是知非的關系。簡言之,良知在具體個體身上的實現以真誠惻怛為動力,指向復其萬物一體的本來狀態,由此真誠惻怛的具體實現展開為一個節次分明的差異結構,此差異結構為個體的行為確定了是非的標準,而良知的同一性和普遍性使個體同時知道他者應當實現的差異結構,這又為具體個體知道他者之是非確定了標準。具體個體在良知之真誠惻怛的動力下必然走向對他者的成全,而其自身也在此過程中實現對自身本來狀態的恢復。